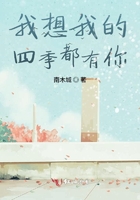他推开我,把毛巾狠狠砸在茶几上,“那也是我的孩子!我是父亲,我有资格、义务保护他!你若有什么想法大可直接告诉我,说好互不牵绊的,何必牺牲这无辜的生命!”他愤怒了,难过了,严厉中夹杂着心痛,他双手紧握,我都听到他骨节发出的啪啪声,可我一点也不惧怕,只是觉得好笑,为什么要等到失去才要珍惜、挽留呢?倘或平日多些许的留意,又怎会这样的痛心疾首。
门在我们的冰冷僵直对视中被撞开,一阵风过,身体便卷入紧紧地怀抱,李彬根本不给我挣扎的余地,双臂如钢筋,越争越往肉里陷,回顾见他双目赤红,满面颓败,口里不停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似害怕什么。
聂志翔反应过来,挥拳冲向他的面颊,李彬竟不闪不躲生生受住了,清晰听到骨骼断裂的声音,真切见到从他口鼻飞溅的血红,可他仍死死抱着我,口里呢呐着:“对不起,蓝韵。”
我觉出下身有热热的东西涌出,粘滑厚重,突然地眩晕竟带来从未有过的轻松,就这样消逝吧,没有不甘,没有牵绊,我无力地瘫软在两个男人的争夺中,其实,他们争自我,一个争自尊,根本与我无关。
就在我意识渐渐淡薄时,不知是谁发现了我的异样,于是我又重新回到医院,重新经受死亡线边缘的疼痛。刮宫时,作为女人的无助与绝望或许只有上帝才可理解。聂志翔紧紧握住我冰凉的手,倾身附在我的上半身,低低安慰:“不怕,就好了,坚持一下。”甚至不顾医生护士亲吻我汗湿的双鬓。我痛到极致张口咬住她的胳膊汗泪俱下,似乎五脏六腑都被人生生掏空了,他抱我下手术台时,我全身如筛糠,一句话也说不出。
医生打了针安定,我才算解脱。
当我再睁开眼,竟看到了垂泪的穗子!
我努力扯起嘴角,想给她个安慰的微笑,却扯断了如珠的泪,沿着眼角没入发中。她轻轻抚摸去消瘦的脸,带给我无限温暖,这是我从事发到现在唯一真诚的关爱。她轻轻抚摸我消瘦的脸,带给我无限温暖,这是我从事发到现在唯一真诚的关爱。
聂志翔起诉了李彬的母亲,除了民事赔偿、精神财赔偿,还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李彬的父亲来找我们,希望我看在李彬真实意的份上,放弃诉讼,转为庭下和解。
“可以,我可以放弃,但请转告李彬,今生今世永不相见,他给我的伤害足以抵过他给我的爱!”我不再想与任何人有情感上的牵连,上帝已然惩罚了我。聂志翔没有说话。
出院那天,医生来交待注意事项,临走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好容易才保住这个孩子,一折腾,日后能否再孕都难说了。好好爱惜自己,至少半年内不要考虑,等身体彻底痊愈再做计划吧。还有,月经期尽量控制情绪,不可大悲大怒。”我对这个当初脸色与手术台一般冰冷的医生本无好感,可此时,从她眼中我竟读出了真诚。
“谢谢,我会注意,以后有了孩子还会来找你的。”她点点头转身离开。
穗子把东西收拾好,扶我慢慢向电梯走去,她悄声在耳边提醒:“一会儿下楼,看到什么样千万别心软。”
我被穗子包裹得像个粽子,尽管天气还不算冷,但她坚持小产也如坐月子,刚到楼下,就打电话叫人,一个个头与穗子差不多,体态强壮肤色微黑的小伙子跑过来,冲我羞涩地一笑,大方介绍:“你好,我叫方子墨,你是蓝韵老师对吧,我是……”穗子抢着说:“我捡的男朋友。”我一时呆怔,好一会儿才消化这个惊喜。
他已快速利落地把东西放车上,又跑回来把我背起来,我惊呼一声,已伏在他宽厚的背上。曾几何时,我也曾憧憬着可以依靠在一个这样的背上安眠,齐明给我的是影子,聂志翔给的是云朵,李彬的是荆棘,女人一生何求,无非是累了时的依靠,寂寞时的拥抱,而我竟连这卑微的要求都得不到。
穗子打开车门,飞速将我塞进车里,我刚坐正,另一侧车门被野蛮地拉开,李彬硬挤进来。他生生将我锢在怀里,下颌抵住我的额头,任我怎么挣扎,他如雕塑般一动不动,任穗子在一旁又扯又拉。
他更憔悴了,俊秀的脸上写满疲惫,眼里盛着悲痛与绝望,看上去很是颓败,是他害了我,还是我害了他?一个意气风发、洒脱风流、活力四射的大男孩愣是沦落为心灰丧气、战战兢兢求人原谅的可怜虫,何其不幸又何其无辜,禁不住一声长叹,伸手轻轻抚摸他消瘦的脸颊,讷讷道:“瘦了,不帅了,看,我又毁了一个好男人!”
他将我的手固定在脸上,眼神中突然燃起亮光,宛若璀璨的烟花刹那间美轮美奂:“蓝韵,让我保护你吧,我再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我以生命起誓。”
“可你的爱对我就是伤害,你还不明白吗?”
他僵住了我,连同那没有散尽的笑容。我们没法生活在真空里,我的过去他的未来,彼此牵连的人际,都是我们肉身难以逾越的羁绊。他低垂了头,将我的手包在掌中,仍有不甘:“为什么爱一个人这么难,两情相悦不就好了吗?”
“因为你爱错了人。苍鹰一旦爱上水里的鱼,注定两败俱伤。放开吧,你的真爱还没出现。”
穗子扯着他的衣服将他拖出去,“90后的孩子很任性,你就是典范!”
车子在李彬凄楚的目光中离开,我同后视镜里那个孤独落魄的影子悄声告别:再见,李彬,好好经营你的人生,不要为了一处的惊讶错过所有的美景。
我没回家而是跟随穗子去了宾馆,我们定了第二天的机票,“放心,子墨是个老实人,自己经营一家小超市,我现在即是店员也是老板,打算元旦领证,反正是二婚,也不想大操大办,几个熟人、朋友吃顿饭了事。”她总能猜到我要问什么。
“你下定决心了?”
“嗯,人啊,得服命。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我把过去全抖给他了,他说他娶得是我的现在与未来,过去与他无关。”
“那就好,我们斩不断过去,只希望有个新的开始。”
“蓝韵,别想太多,一切都会过去的,像我,走在大街上,还有几人识得我是小三。你这么善良,上天总会眷顾你。”
我哭笑,还不是自找的,有道是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对聂志翔,我还欠一个交代,也该放手了,不用等他来交底儿。
我收拾完就去客房睡觉,在梦中忘了这些个烦恼。我睡的昏天黑地,是手机铃声将我唤醒,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你在哪儿?”是聂志翔生硬的声音。
“我在……这是哪儿?噢,是宾馆。”
“……那一家?”他猛然吼了一声。
“一客一家!”我被他的反常吓得反应迅速。过后清醒,他想干嘛,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有,我还没还他自由。
我从网上荡了一篇离婚协议,稍作修改打印出来,只等当事人签字。说实话,落笔时,心中实在不是滋味,那一刻记起的全是他的好,着实不舍。可三年婚姻怎敌得过人家青梅竹马、情真意切。
半个小时后,聂志翔赶过来,藏青色的西装外套皱巴巴的,显然这几天衣不解带,忙得无暇打理,他可是个整洁的人。
穗子犹豫地望着,怕他会冲动伤害到我,一时不知该走该留,方子墨悄悄扯了她的衣角,示意出去,朝聂志翔点点头。
他坐在沙发上,神情冷漠,目光暗沉,连一向温和的唇线也抿的紧紧的。他一言不发,就那么盯着我,直到我心虚坐不住了,才冷冷问:“什么意思?悄无声息的出院,还不回家?”
“家?没有爱,那里只是房子罢了。”
我幽幽地望着他,心中分不出是抱怨还是留恋:“你想好了吗?想好后,可以签字了。”我把离婚协议递给他。
他疑惑地接过去,只一眼就砸在地上。“蓝韵,你够狠!”
“哈!”我冷笑一声,嘴里苦苦的,“小兰恢复记忆了不是吗,你苦苦的等待就应还来美满结局,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是在成人之美,如何是心狠呢。”
他身体一僵,怔怔对着我好久。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放弃你吗?从未想过争取?这样大方地将丈夫送出去,一点也不难舍?”他语调平静,不杂情感。
“我拿什么争?你们有美好的过去,有坚不可摧的爱情,而我们真正在一起还不到半年;我怎么争?我没有她的温柔飘逸,没有她对你一点一滴的熟悉,跟没有她在你心中独一无二的位置,仅凭我肚子里的生命吗?聂志翔,你选她,是重情重义,还君明珠;你选我,是姑且从之,生活使然。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我们都是成年人,理智一些,对谁都好。”
他突然笑了,捡起地上的协议,轻轻敲打我的头:“你这女人,有时理智的可怕。”
我被他搞晕了,一时不知什么状况。
他伸手圈过我,拥入怀中,默默梳理我脏乱的头发,低声轻语:“真傻,我怎么会舍得你呢。我以为你可以感觉到我对你的情感。男人只会让最爱的女人为自己生儿育女,蓝韵,你才是我独一无二的。”
我惊喜过度,找不到北,难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在胡思乱想,无事生非?他捧着我的发昏的脑袋说:“真傻,为什么要与她比,一时的错过就永远错过了,她有爱她的丈夫,我有爱我的妻子。”
他亲吻我的脸颊,柔声说着对不起。
“我 彷徨过,犹豫过,但我肯定你才是这里的肋骨。”他把我的手放在他胸前,静静感受那强劲的心跳。
“蓝韵,如果有一天,齐明来找你,你会跟他走吗?”
“嗯?”我困惑,不是李彬吗,怎么扯上齐明了呢?
“李彬是一时冲动,我知道你对他有感动但没心动,你只是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我担心的是齐明,对他,你是否还有不舍?”
“没有不舍,可能还会有点不甘吧。正如你所说,错过就错过了,放开对谁都好。”
齐明已带着他所有的魅惑从我生活中远逝了,再不回来,美好早已成了玻璃杯中的标本,可远观而不可触碰。或许,他就应该是沉淀在生命里的一抹底色,回荡在耳畔的一缕绝响,招摇在地平线上的一带烟霞,美则美矣,只是太远太轻太飘,我靠不近,抓不住。既然不能在一起,爱又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