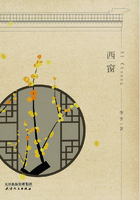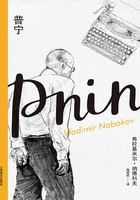停车场就在酒店右侧,但被酒店遮挡着。柳长锋迈着急促的步子走过去,举目远眺,暗淡迷离的灯光下,一袭黑影孤独地立在远处。那影子有点缥缈,有点朦胧,好像不忍碎去的一个梦,幽灵般挣扎在他内心的最痛处。柳长锋停下步子,他必须停下,必须思考那么一会儿。这影子曾经多么熟悉啊,他闭上眼,往事便一幕幕涌来,哗哗地,如同潮水,听得见响声,瞬间要把他淹没。他甚至已经闻到她的呼吸,嗅到她身上奇特的香味。是的,谢觉萍身上总是有股暗香,很奇怪,不是香水,也不是衣服留下的,柳长锋曾像探宝一样探寻过,后来相信了谢觉萍的话,生下来就那样。
那股暗香陪了他六年,六年啊。
柳长锋狠狠地吸了一口,仿佛空气中仍有那股香味似的,他抬腿往那边走去。
谢觉萍戴着墨镜,夜色没有裹住的东西,全让她藏在两片暗色镜片后。她像一个高高大大的陷阱,立在那里,等柳长锋去跳。
黑衣,迎风而飘的深色丝巾,还有被风吹乱的长发,整个人像恐怖片中的鬼魂。
柳长锋的腿有些软。自从两千亩土地大案曝光后,他就主动远离了这个女人,将过去的温柔还有激情全部葬掉,将山盟海誓还有甜言蜜语全都葬掉。谢觉萍定罪入狱,他没过问,谢觉萍在狱中怎么过,他没过问,谢觉萍出来后,他更是保持着警惕,怕毒蛇猛兽一样远远地躲着这个女人。现在,他居然乖乖地听从她的召唤,来到了她面前。
“你终于来了。”黑暗里响起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那声音是她的,哪怕再过一百年,柳长锋也不会听不出这声音。
“呵呵,呵呵,是你啊。”柳长锋干笑着,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你腿抖什么?”
“没,没啊,我抖什么,我有什么可抖的?”“不,你抖了,抖得厉害,怕了?”
“没,怎么会怕呢?”柳长锋强撑着又往前迈了半步,仅仅半步,他就不敢再往前了。说穿了他还是怕,自从事发,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老是做噩梦。有时梦见谢觉萍把跟他的一切都说了出去,有时梦见谢觉萍雇凶追杀他,最可怕的一次,竟梦见谢觉萍跟他做爱,做到一半,突然掏出一把锋利的刀,将他活活肢解……“我身上没带刀,也没带硫酸,你不必怕我。”谢觉萍说。
“看你说的,怎么这样说呢,觉萍啊我们之间有些误会,这样吧,找个机会,我们好好聊聊。”
“机会?你还在想机会?”谢觉萍口气冰冷,每个字都冒着寒气。“不要嘛,觉萍,毕竟我们……”
“我们怎么了,不就是让你白睡了六年吗,睡够了,睡烦了,一脚踹开。”“别说那么残酷,觉萍你知道的,我不是那种人。”柳长锋心虚地道。
“残酷,你说我残酷?”谢觉萍突然大笑起来,她的笑声被风吹起,阴森森地飘到空中,柳长锋忽然觉得周围的空气中都布满了恐怖。
柳长锋无言地垂下头,不敢再乱讲话了,怕再讲下去,惹出更坏的后果来。谢觉萍笑完,忽然摘下墨镜,柳长锋吓了一大跳,差点喊出声音来,半天,蚊子哼似的问:“觉萍,你,你……”
“怕了吧?”谢觉萍往他跟前走了一步,这样好让柳长锋看得更清楚些。“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是谁?”这话是柳长锋真心问出的,一点不带假,也不带造作。谢觉萍仿佛感受到了一点过去的东西,忽然就撑不住了,重新戴上墨镜说:“没啥事,是我自己毁的。”
“你自己?!”柳长锋越发震惊,一步跨过去,不由分说就捧住了谢觉萍的脸,“告诉我,怎么会这样,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急了,真急了。当一张美丽的脸突然以非常狰狞的面目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脑子里突然什么都不存在了,就一个念头,要报复毁这张脸的人!
谢觉萍痛苦地扭开脸,声音惨淡地说:“什么也不为,就为了出来。”“什么?!”柳长锋几乎要昏厥过去。
4
柳长锋他们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吐字不清。吐清能叫官场?不叫!官场中哪个有作为的官员能把话说清楚说明白了?没,只有那些糊涂蛋,以为必须讲明白,于是就奋力去讲,结果越讲越不明白。真正的明白就是不明白,越是吐字不清,你就越像官,越像大官。
谢觉萍并不是找柳长锋诉委屈,也不是让柳长锋看那张她在狱中毁去的脸,这些已是历史,对她一点不重要了。当初她能断然把玻璃碎片割到自己脸上,就没打算再用这张脸去赚取别人的同情,哪怕这人是她死心塌地爱过的柳长锋。
她是警告柳长锋!
柳长锋还处在巨大的惊恐中没有镇定下来,谢觉萍的声音就到了,她说:“已经在庆贺了啊,这酒喝得过瘾吧?”柳长锋啊啊了两声,避开她目光,讪讪道:“哪有,就几个朋友,随便喝点。”
“朋友?”谢觉萍怔怔地瞪住柳长锋,瞪住这个曾经让她疯让她狂让她迷失让她沉沦就是现在也仍然放不下的男人,一股陌生感涌上来,袭击了她。她感到一种恍惚,一种物是人非的飘离感,随后,就是彻底的悲凉了,是的,悲凉。她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太失败了,但之前她没感到过悲凉。这一刻,这种离奇的感觉攫住她,撕扯着她,让她想发出狼一般的长嗥。但她没发,只是定定地看了柳长锋一会,换一种语气道:“你柳大市长还有朋友啊,稀罕。”
柳长锋听出了这句话的不友好,忙讪笑道:“觉萍,我对不住你。”
“少说这种话!”谢觉萍突然像被毒蛇咬了一般喊出一声,随后,泪水就又模糊住她的脸。她忽然感觉到了自己的没出息,被判入狱那一天,她发誓再也不流泪,不为任何人流,更不为自己流。当她在狱中以色相引诱那位长得奇丑又极其猥琐的老狱警,以身体换得一个玻璃茶杯后,再次发誓,以后如果再流一滴泪,她就把自己的双眼挖掉。可是这阵,不争气的眼泪又出来了,挡都挡不住。这能怪谁呢,女人一旦掉进爱的陷阱,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地狱,再想出来,很难。她悲哀地叹了一声。
“柳长锋,你给我听好了,我为谁进去的,你们都明白。我为谁牺牲掉一切,你比其他人更明白。”
“明白,明白,觉萍我真的明白。”柳长锋几乎是蛤蟆一样连着啊啊了几声,腰连着弓了几下。他掏出纸巾想为谢觉萍抹泪,发现根本不需要,只好在自己细汗密布的额上擦了几下。
“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我今天来只想告诉你一件事!”谢觉萍几乎是吐血一般在往外吐了。
“我听,觉萍我在听,我一定听。”
“离胜利还早得很,就你这点智慧,想跟朱天运玩,做梦去吧。你们这帮蠢猪,让我羞愧,我谢觉萍不值啊——”
柳长锋打了几个哆嗦,忽然就发不出声来,目光傻傻地望向谢觉萍,这时候的谢觉萍像一座长满翠柏的山,他根本就无法一眼望透。
“好自为之吧柳市长,监狱的大门不是为我谢觉萍一人开的,你柳大市长还没我这点勇气,不敢拿玻璃割破自己的脸!”说完,她毅然转身,坚决地离去了。柳长锋傻愣片刻,赶忙追上去,追几步又停下,他没有勇气再追下去,可这女人说这些什么意思呢?
黑暗里突然又传来谢觉萍的声音:“让你老婆安稳点,最好让她滚到国外去!”
柳长锋在夜幕下站了足足两小时,极少抽烟的他这天突然想狠狠抽,可惜身上没烟,想打电话找阎三平要,号拨一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愤怒地迈开步子,去了停车场边上一个小卖部,扔出一张百元大钞,口气恶劣地说:“拿包烟!”店老板是位中年女人,盯着他看了一会,问:“要啥烟?”
“让你拿你就拿,问什么问?”
女店主没吭声,扔给他一包普通烟,柳长锋没好气地说:“换中华,软的!”
女店主沉默了一会,还他一句:“没有,那烟不是我这种小店卖的。”“好吧好吧,随便换一包。”
女店主没听他的话,而是拿起那张百元大钞对着灯光反复看,看完正面又看背面,最后扔给他一句话:“我的烟不卖!”
柳长锋简直要气死了,差点就咆哮,砸这家店的心都有。最后他还是拿起那张钞票,失落地离开了。看来,市长也不过如此,没了前呼后拥,没有身前身后那一大堆拍马屁的,他跟这街上任何一个老百姓一样。这么想着,忽然就又想到谢觉萍刚才警告他的话,内心涌上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最深的竟是内疚,他知道,他欠这个女人的太多了,怕是这辈子也还不完。
柳长锋最后在另一家小店买了烟,一抽就是假的,呛得他连声咳嗽,无奈,把那包花高价买来的软中华扔了。柳长锋苍凉地笑笑,他哪是市长啊,这夜的他,简直就是一条丧家犬。就在他徒自伤悲时,一个人影忽然晃过,眼一亮,这不是刚才酒桌上差点令他神魂颠倒的茹娟茹老板吗?遇着鬼了,柳长锋定定盯着茹娟的背影望了好久,顿然明白,这女人一直没离开过他,刚才跟谢觉萍那一幕,她定在暗处偷窥。
他问候了一声阎三平娘,重新回到跟谢觉萍说过话的地方,呆愣了片刻,毅然掉头,打车回了家。
贾丽刚洗完澡,脸上做了面膜,正躺沙发上按摩呢,边按摩边听歌,柳长锋记得这首吐字不清的歌,那是缘于他听这首歌时生出过的一种感觉。能以这样的唱腔唱歌,高,实在是高。柳长锋他们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吐字不清。吐清能叫官场?不叫!官场中哪个有作为的官员能把话说清楚说明白了?没,只有那些糊涂蛋,以为必须讲明白,于是就奋力去讲,结果越讲越不明白。真正地明白就是不明白,越是吐字不清,你就越像官,越像大官。
柳长锋一看贾丽鬼一样的一张脸,怒气顿然起来了。
“你不会做点正经事啊,净整些乱七八糟没用的!”柳长锋冲自己老婆吼。
贾丽没理他,继续听她的歌。
“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见老婆无动于衷,柳长锋火气更甚。
“吃错药了呀!”贾丽腾地从沙发上弹起来,一张森森然的脸对着柳长锋。柳长锋吓得往后缩几步,意识到贾丽是做了面膜,才镇定下来,板着黑黑的面孔说:“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做什么了,柳长锋,我做什么了?!”贾丽连着逼问几句,反把柳长锋问住了。是啊,她做什么了,好像什么也没做。是,什么也没做。柳长锋这么嘀咕着,不再理贾丽,往书房去。贾丽却扑上来,一把拽住他问:“柳长锋你跟我说清楚,023号那笔款子你是不是给了小妖精?!”
柳长锋跟贾丽的所有款项都是有代码的,这代码别人听不懂,他们懂。三位数,前面这个“0”代表一个人,比如罗玉笑或者骆建新,反正这笔款不是他们的,只是他们经手,中间拿一定费用。中间这个“2”也是代表一个人,这是给他们这笔款的人,比如阎三平什么的。后面这个“3”也是一个人,这款要通过谁转移出去。贾丽说的小妖精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儿媳妇方雨宏。
“你乱说什么,扯淡!”柳长锋回击一句,往书房走去。贾丽不让他去,扯住他:“你跟我讲清楚,柳长锋,别以为老娘傻,改天把老娘逼急了,我让你好看。”
“你敢!”柳长锋一把推开贾丽,面色骇然地进了书房。是要出事啊,摊上这么一个老婆,不出事才怪!
其实这笔款他根本就没转出去,不只这一笔,还有他自己的两笔,目前还都困在国内,就困在海州某个地下钱庄里。骆建新案发后,海州原来的地下钱庄不自觉地都收紧了,几条线上的头目都躲着不见人,就算见了,也都打哈哈,跟他说一句,最近玩不得啊,不好玩啊什么的,就应付了过去。而老婆和儿媳妇方雨宏都不理解他,较着劲儿跟他闹,一个怕他把钱给老婆,一个又怕他把钱给儿媳妇,简直到了争风吃醋的地步。她们哪里知道他柳长锋的难处!尤其贾丽,一直埋怨自己偏向儿媳妇。无稽之谈,他柳长锋分得清远近。他的苦衷在于,儿子不是正常人,不喜欢女人,偏要喜欢男人,这事万万不能说出去,所以当初他坚决把儿子送到国外,就是怕这事传扬开来。可儿子到了国外,这方面越发没有顾忌,玩得更过火。他能不迁就儿媳妇吗?
让她得不着人,至少能得着钱啊,要不凭什么人家为你独守空房,还要替你柳家保守秘密?
可怕的消息是三天后传来的。他这条线上的一个干部出了问题,这干部是柳长锋一手提拔起来的,目前在海州另一个区担任常务副区长,应该说前途一片大好,不出意外,一年内就能升到区长位子上。谁知就在这节骨眼上,他玩女人玩出了问题。背着老婆养了个小三,小三原来是海州艺术学院的学生,跟了他五年,越跟胃口越大,不只是要他明媒正娶,颠覆他老婆的地位,还公开要他将自己的弟弟、叔叔、叔叔的儿子等都安排到好岗位上。这下副区长不满了,认为她太贪。天下哪有不贪的女人,不贪的就只有老婆,小三小蜜什么的不贪人家能看上你?这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敢玩女人!副区长大约也是被这个女人逼急了,逼得没有退路了,竟铤而走险,想出一个谁也想不出的招来。他趁这个女人熟睡时将她活活勒死了,然后装进后备厢里,开了很远的车,扔到了远在两千里之外的江里。可他最后还是被查到了。天下的事都是如此,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出了这样的事,柳长锋哪还能消闲,天天擦屁股,谁让他用人失察呢。刚批阅完检察院呈过来的一份材料,门就被轻轻推开了,秘书安意林悄无声息走进来。柳长锋觉得奇怪,最近他看什么都觉得奇怪,安意林突然在他面前规矩起来,时时处处做得像个秘书,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当有人在你面前突然改变自己时,你就要警惕了,不是你出了问题就是此人出了问题,要么你们俩都出了问题。柳长锋抬起脸,亲热地唤了声安子,又问:“有事?”
安意林保持着秘书的低姿态,中规中矩地嗯了一声,往他面前跨了小半步,声音很诡异地说:“老板,出事了。”
“什么事?”柳长锋听出自己声音的变化,变化里包含着一种胆怯,那是不忍再受打击的一种怕,一种颤,尽管脸上仍装作若无其事。
“汤永康归案了。”
“什么?!”柳长锋腾地从老板椅上弹起,一双眼睛冒出两个巨大的问号,不,还有惊叹号。
“有人玩了声东击西计,表面好像把功夫用在了唐大姐身上,暗中却给汤老板放了线。”
“谁?!”柳长锋下意识地问出一句,问完,他就痛恨起自己来。还用得着问是谁吗,难道你柳长锋就弱智到这水平。
“好吧,我知道了。”柳长锋敛起脸上表情,淡淡地说了一句,将头又埋回已经批阅完的材料里。安意林默站一会,没再吭声,影子一般倒退了出去。
门刚合上,柳长锋就急不可待抓起电话,打给了肖庆和。半天,肖庆和的声音才到了,很礼貌地问了句:“市长有事?”
“没啥事,突然想起一道鱼汤来,就咱俩吃过的那道,处长有兴趣没?”肖庆和顿了顿,有点黯然地道:“那汤已让别人抢先一步喝了,市长换换口味吧。”说完,压了电话。
柳长锋再坐下时,内心几乎就要到崩溃的边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