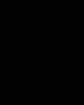临近中午,阳光有了几分热烈,天的蓝色也更纯净了。只有少许的云,也是静止的。收割的人大概是肚子饿了,纷纷停了打谷机,挑了稻子往回走。刚才还喧喧嚷嚷的田野眨眼静了下来。泥儿崽找了条漾满水的田沟,将鸭子拢到了田沟里。鸭子们入了水,嘎嘎叫开了,一边搅动翅膀,田沟里水花四溅。它们肯定是吃饱了,有了嬉戏的兴致。由着它们闹腾去。
可泥儿崽的肚子还空着。他挑了块干爽的地方,抱了些稻草垫着,之后就在稻草上坐下了。他从袋子里掏出饭团,在阳光下啃了起来。饭团冷了,就有了硬度,他啃得有些费力。而且忘记带水了,嘴唇干巴巴的,嗓子眼也有些干涩。胡乱吃了几口,饭团子只是去了小半边,他就收起来了。阳光有些炽烈,坐着不动,身上就热腾腾的,脸上也火辣辣的,晒得有些痛。他拖过来几把已经扎好的稻草,搭了一个小小的草棚。他将自己藏在了草棚下。
他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田螺,他的壳就是草棚,只是他不能像田螺一样背着壳儿行走。他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暗暗笑了。田螺躲到哪儿去了呢?脚下的泥土已经干透了,上面是一层白颜色,有了很多的裂缝。撬开一块裂缝,干结的泥土就翻转过来了。他捡起泥土放在鼻间嗅了嗅,干白的泥土不像稀泥那样满是腥味,而是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泥土的香气。他喜欢变白的泥土,又撬了几块,将它们铺展在阳光下。有了阳光的照耀,它们的颜色会更加白净。
泥儿崽的学名叫白泥。他刚出生时泥儿爹请算命先生算过,泥儿崽缺水又缺土,后来一直为他的名字犯愁。现在这名字是泥儿爹用两斤肉换来的。虽然不知道取名字的人是谁,但他的学问让泥儿崽佩服得五体投地。泥,有水也有土。白和泥连在一起就绝了,白色的泥土是干净的泥土,洁净,一尘不染,没有任何瑕疵。因为喜欢白泥,他因此喜欢上了秋天,只有秋天才有这样的泥土,也只有秋天才配有这样的泥土。冬天的泥土是白色的,可那是雪的颜色,夏天的泥土又是绿色的,那是叶子的颜色,而春天呢,完全是水的颜色。有时他会自己叫喊自己,白泥,白—泥,哦,白—泥——可令人气恼的是,村子里的人从不叫他白泥,只叫他泥儿崽。他讨厌别人这么叫他,可越讨厌别人叫得越欢,泥儿崽,泥儿崽哎。他知道他们是故意逗他的,并无恶意,也就默认了。
走了一会神,他就收住了自己的思绪,他记起了袋子里的那本书。他该看看书了,不能因为放鸭子而放弃了书本。正午的田野一片静寂,鸟雀又落到了附近的稻子上,趁着没人的短暂空隙它们来偷嘴了。他翻开课本大声朗读了起来,他的声音将鸟雀惊飞了,但它们很快就发现他的朗读声并不存在危险,三三两两又飞了回来。鸭子们早习惯了他的读书声,一点也不慌乱,依旧在田沟里嬉戏它们的。有的鸭子还在田沟边迷糊了起来。
他也有些困了,都打了好几个哈欠。他躺倒在稻草上,上身藏在草棚里,两只脚丫子伸出草棚外,任由阳光晒着。这样的天气是适宜睡眠的,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白泥,白泥,起来呀,白泥。他听见嘞嘞在叫他,村子里也只有她会这么叫。她的肚子里像是藏了一枚特大的鸭蛋,她就挺着肚子站在他面前。她告诉他,田沟里有枚蛋,它就在那儿,她指给他看。他一骨碌爬了起来,跑过去,在田沟里摸了个来回,最后在稻茬下摸到了那枚鸭蛋。他将蛋握在掌心,想要放到袋子里,不知从哪突然伸过来一只手,一掌拍在他的手臂上,蛋掉了,蛋清流了一地。
泥儿崽就是这时候醒过来的。他是被那只不知名的手拍醒的。鸭子们在田沟边嘎嘎叫个不休,像在争论着什么。不屑参与争论的就摇摇摆摆走到了田中间,继续觅食。背后的稻丛中像有什么声音,窸窸窣窣的,听得并不真切。他从草棚中探出脑袋,朝稻丛望了望,离他不远的地方有几蔸稻子在摇晃着,声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他以为有鸭子偷嘴了,赶快爬了起来,从田埂上跑了过去。快要接近地点的时候,泥儿崽听到了说话声,声音压得很低,但他还是听清楚了。
快点呀,他们就要来了。先是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她的声音是扭曲的,他听不出是谁的声音。
快了快了,我就要出来了。之后是一个男人喘着粗气在回答。
他弄不懂他们在干什么,反正不是鸭子在偷嘴。但他很好奇,想弄明白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他甚至以为他们在偷稻子。他收住了自己的脚步,立在了田埂上。田埂的位置比较高,只要踮踮足,就能看到稻丛中的景象。他真就踮起了身子,稻丛中的情景就一目了然了。一个男人光着身子抱着一个女人压在稻草上。他绝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幅图画。他怔住了,脑子里嗡的响了一声,之后耳边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他只朝他们看了一眼,他的呼吸立马就急促了,不由他自己控制。他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坚硬了。他的脸可能也红透了,只不过他自己看不到。他没看清楚那是谁和谁,女人只露出一张脸,是扭曲的,五官都错了位。男人呢,他只看到后脑勺,还有光着的脊背。
好半天,泥儿崽都没有醒过神来。他也不记得自己站了多久。那对男女仍在忘情地忙活着,根本没有察觉他的到来。他碰到了一起脏事,这是醒来后的第一感觉。呸,呸,呸。他朝田埂上吐了三口唾沫。这是嘞嘞告诉他的,撞见脏东西要吐三口唾沫,不然会走霉运的。唾液没有落在稻子上,他怕脏了稻子,也没有落在泥土上,他怕脏了泥土。唾液是挂在了田埂的杂草上,黏黏乎乎的一团,将草叶都坠弯了。
有—人—呢。可能听到了泥儿崽吐唾沫的声音,女人在提醒男人。
稻草上立刻响起了急促的慌乱声。泥儿崽转过身,沿着田埂往回跑了起来,可没跑出几步远,背后就传来一声男人的喝斥,你给我站住。泥儿崽背对着他们停住了脚步,他不想看他们第二眼,他怕他们弄脏了他的眼睛。可他们很快追了过来,而且站到了他的前面。他认出了那张男人的脸,油乎乎的,是村子里杀猪卖肉的屠夫。屠夫的裤子系了起来,上衣只是套了身上,扣子还没来得及扣上,他的胸部敞开着,上面歪歪扭扭排着三个圆圆的窝窝,肉红的,是扣子留下的印迹。
泥儿崽曾去屠夫的摊子上买过肉。那一次屠夫并不急着将肉卖给他,举着刀,就是不砍下去。我出个谜语给你们猜猜。屠夫说,山×山,是个么字?他的谜语里夹了个肮脏的字眼,泥儿崽没有吱声。是个出。屠夫有些得意,又说了个肮脏的字眼,土×土,是个么字?泥儿崽拿眼死瞪着他,他不容许有人将土同肮脏的东西扯在一块儿。是个圭。屠夫的脸上有了猥亵的笑,你的书是白读了,你爹×了你嘞嘞才生了你这个傻巴蛋。泥儿崽噙着泪跑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吃过从屠夫那儿割的肉了。
那女的比屠夫过来得慢一步,是朵儿娘,她的衣衫是齐整了,可她的头发上粘了不少的稻草屑。她红着脸站在屠夫的旁边。泥儿崽突然想到了那块麦芽糖,他彻底明白了嘞嘞为什么说那是脏东西。那的确是脏东西,她居然还红了脸。拿来。朵儿娘向屠夫伸去一只手。什么?屠夫满脸懵懂。你说什么?朵儿娘睁圆了眼。屠夫在裤袋里左掏右摸,摸出五块钱来。朵儿娘从屠夫手中扯过钱,要交到泥儿崽的手上。白泥,给你买糖吃。朵儿娘说。泥儿崽没接她的钱,而是将手藏到了背后。朵儿娘斜了屠夫一眼,屠夫又在裤袋里摸呵摸,摸出了一张十元的,交给了朵儿娘。泥儿崽干脆不看他们了,转眼望向了田野。田野上静悄悄的,什么人也没有。秋收的人还在吃饭,或者喝杯饭后茶,再稍微歇息一下。
朵儿娘见不得屠夫磨蹭的样子,自己动手去他的裤袋里掏开了,但最后她也只掏出一张二十元的。她将那十五元钱塞进了自己口袋,然后转到泥儿崽背后,想将二十元钱放到他的手里,他依旧不给她机会,他将手又放回胸前。后来朵儿娘就直接捉住了他的手,将钱按在了他的手心。白泥,你是个懂事的伢崽,这钱婶娘给你买糖吃的。可朵儿娘刚松手,他就将钱扔到了地上。朵儿娘傻眼了,她一屁股蹲坐在地上,双手捂住脸哭开了。他没理会她的哭泣,撒腿跑到了草棚边。他从地上拾起袋子,掉转身想去拢鸭子。他想离开这片田野,换过一个放鸭子的地方。
但他的出路被屠夫挡住了。屠夫横在那,就像一堵油腻腻的墙。如果想走,泥儿崽就必须翻越这堵墙。
你给我拿着。屠夫强行将钱塞到了他的掌心,泥儿崽还想扔出去,但屠夫后面的话将他吓住了。你要是将钱扔了,我就宰了你的鸭子。屠夫的话凶巴巴的,让他打了个寒颤,那么壮的一头猪屠夫都放倒了,对付二十几只鸭子那就是小菜一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