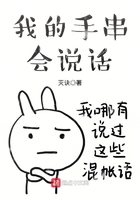是的,她嗅到了,的确嗅到了,而且不久之后,支那人用行动应验了她的嗅觉!一个叫李兆麟的支那将军率领支那军队在一天夜里攻入山谷。父亲、母亲带着她出逃的的时候,她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她生活了四年之久的山谷,山谷已经成了火海,平时沉默、温顺的支那人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不久之后,他们真的进了山海关内,很多支那人的土地变成了被父亲的同僚占据。父亲越来越忙,越来越忙,她见父亲的次数也变越来越少,一星期一次,一月一次,三月一次,半年一次,有时父亲一个口信或是电话,母亲必须带着她搬家,有时没有父亲的口信或是电话,在父亲下属的安排下,她和母亲也必须搬家。她最后一次见父亲的时候,弱弱的和父亲表达了想回北海道看樱花的念想。
“鬼束,战争快结束了,我们这就回去!”
那是她第一次从父亲的回答里读出恐惧、不甘、惋惜,也是最后一次!不久之后,苏联人来了,支那人开始反攻,父亲带着自己、母亲和两个在支那土地上出生的弟弟开始撤离,可是,可是父亲死了,死在撤离的前夜,一个支那士兵击穿了他的头盖骨。十几米之外,她平静的看着,就如同几年前同样看着罂粟园里的那个支那人的迸裂的脑浆一般。是的,所有的一切在,在她满是宿命的小小信仰中已经注定:生死、离别、漫山遍野的血红血红的罂粟、漫山遍野的焦土和焦土上恶臭的尸体、饥荒中争抢的饥民、月夜里见不得光的罪恶、激情岁月里因历史问题信仰问题的互相揭发与拆台,似乎在漂洋过海东来支那的那一年里早已注定!
她被沈世雄带进了山沟,然后嫁给了他的大儿子,有了自己的孩子:大女儿、二女儿、儿子、小女儿,四个孩子相继出生并健健康康的活了下来,他们日渐成长的时候,战争没了、饥荒也渐行渐远、即便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口号也被“改革啦”“开放啦”“经济建设啦”“家庭联产承包啦”等一系列新的名词所取代。可是偶然中,罂粟却出现了,小外甥拿着血红血红的罂粟花出现在他的面前,于是本以为或是真的以为忘却的过往、不为人知的过往就那么突入起来的从记忆的洞穴里窜了出来,拨开层层迷雾后,才发现,当年,记忆里的父亲并不如给女儿讲的那样,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商人。父亲是有罪的,不管大小总和报纸上、广播里公布的那些战犯一般,对中国人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但那又能怪父亲吗?他只是那个时代战争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总而言之,父亲或是和父亲一般的很多日本人,对战中国人犯下诸多罪行的日本人,他们只是那个年代特定状态下的怪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