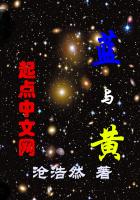于是,俩人隆隆的一阵脚步声,走到楼下。
走出舍楼,又是一片小小的树林,还有石座布满在其里。
无聊回首的道:“紧跟着我,若弄丢了,我可没空找你。”
“用不着吧?”柳条虽嘴如此说,可心还是有怕,脚步也跟紧。
穿过小林,又是一幢舍楼,之后的路似呈下山弯走之势。
曲径通幽,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犹如蜘蛛网般散布在此座山丘上,或是从山顶向山下故射性伸展,或是从山下向山盘环绕形般圈旋而上,路越是向下走,路口越是繁多,路口的景色各有不同,或是小林清幽,山石百态,或是溪水横流,瀑布轻垂,或是小湖荡漾,水鸟恩爱!虽有巧合之造,绝无雷同之嫌,可谓是幅干姿百态的山水画。
而且,在这凌乱美还夹有对称美,那就是路边的幢幢舍楼。
无聊走得过快,路的景色顿让柳条目不暇接。
柳条干脆不接,心想若熟路线,以后有的是机会游赏玩乐。
俩人从舍楼上走约二十分钟,才走出山丘舍楼区。
舍楼山丘前有一条江河,河上架有条拱桥,桥下河水稳媛奔流。
此江不甚宽阔,其宽度约是长度的一倍,几可容十几匹骏马齐奔掠过,而不有擦碰,因而拱桥的桥面也不甚拱凸。
拱桥的那边,就停放有流车四辆,却有三辆正在被人驾走。
“幸还剩有辆”无聊回笑道,与柳条走了过去。
忽然,不知那里爆出俩位学生来,大有争夺流车之意。
果真如此,四人猛跑到流车舱的两边,却谁也没快过谁。
学生俩一是穿黑T恤,一是着衬衫别样衫。
黑T恤俯身,俩手撑住流车道:“这辆流车是我们看到先的,麻烦让开。”
无聊见他们与咱们那样,是抡流车的,也不畏惧的道:“这辆流车是我们摸到先的,让开的应是你们。”
别样衫道:“笑话,摸到的就是你的,我摸过的汽车成千上万那我岂不是拥有成千上万辆汽车了。”
“你更笑话。”柳条见无聊也不怕惧的家伙,更是猖狂的道:“若见到的就是你的,我见过的美女超干过万,那我岂不是拥有一卡又一卡车车的美女?”
黑T恤无言,干脆打横的道:“哼,我说我的就是我的。”
无聊见其无理,于是要赖的道:“是你的么,你叫得它应你么?”
柳条亦帮腔的一挺身胸道:“我还说你的就是我的哩。”
黑T恤猛的一拳打在流车上,打得坪的声响道:“它应我了。”
无聊一听拳声的音量如此的高,不禁略有退怯之意。
“你也大声的叫一叫流车,让它大声的回应回应你。”柳条用手一撑顶无聊的腰脊,附在他的耳边轻声细语的道:“狭道相逢勇者胜,你要勇要猛。”
“你是我的,而不是他的,是不是。”无聊俯身对着流车吼道,猛的使尽浑身之力,一拳打车流车的持制钢板上。
流车也是坪的声响,铿锵有力,凹下小小的陷;而无聊却痛得鼻都酸了,浑身僵硬,高频律的震动,险些喊出声来,慌忙化疼痛为悲愤,紧紧咬住牙筋,睁着眼睛,慢慢的抬头道:“如何,你听见它在应我吗?”
黑T恤见无聊的气势,不禁有些退怯。
别样衫道:“多说无益,干脆就用江湖规矩解决。”
无聊仍在忽痛的扬头吐气道:“江湖规矩就江湖规矩。”
“好”别样衫道,随即挽卷衣袖,摆开架势。
“江湖规矩?”柳条事后有架打,不禁暗叫糟糕。但是,别样衫却早已出手了,一拳打来的道:“剪刀、石头、布”
“别打!君子动口!”柳条喊道,却见他们在划拳。
“哎哟!”无聊忽的痛叫,他出的是布,却忘了手肿的痛。
俩人同时暴出脆弱,露出马脚。
黑T恤顿的长了气势般道:“怕打就滚开!”
“谁怕”柳条死撑的道:“我不过有别的方法,能一见真章,解决这流车所有权的问题而已,你敢不敢与我们较量一番?”
“未怕过”别样衫道:“什么方法?”
柳条望了望流车,回首道:“你看这条校道。”
校道甚宽,而且甚长,中间有十字路口,此地距十字路口约有三百来米。
柳条用脚划了条无形的界线,蹲在界线前,俩手撑地后道:“此界线离那十字路口约有三百来米。我们四个在此起跑,较量较量谁更快跑到十字路口,若是一四与二三;就算平手;若是其他,就分胜负;那组胜出就得流车一辆,如何?”
别样衫笑道:“简直是自取其辱,我可是本校上季赛田径赛跑总决赛的候选人之一,就凭你也敢向我挑战赛跑?”
“还候选人”柳条不屑的道:“我可还是我校的田径赛的六连冠军哩。”
无聊听道却扶起他道:“你以前的学校怎能跟异武法幻校相比?别在此献丑了,你想奔跑,待会的路有得你跑,咱们走吧。”
黑T恤与别样衫不禁大笑的道:“让我们发笑的,是你的愚味无如。”
柳条却硬蹲下撑地道:“我就不信我刘翔第二代,跑不过你候选人。”
“好,我就给你献丑的机会。”别样衫说道蹲下撑地。
无聊仍想劝阻逃避道:“还是算吧,别浪费时间了。”
柳条道:“男人大丈夫输不起吗?逃走的才是乌龟。”
无聊听道不乐的蹲下俩脚,撑住了手。
黑T恤也跟着蹲脚撑手,四人排成一线。
“我叫三声,大家就一起跑。”柳条望望左右道:“预备”
“三”柳条喊道,屁股仿似被人踢了脚般,箭步飞奔。
“玩花招?”语声没到,柳条却忽的感到身边有两阵风吹过,别样衫与黑T恤已超越刘翔第二代的他渐拉开距离,而无聊也转眼跑到柳条身边。
柳条一扯无聊道:“不是说好一起跑的吗?”
别样衫与黑T恤岂会跟他一起跑?俩人的脚步密如天掉的雨般,身似离弦的长箭,穿破着空气,磨擦着风,三十多秒就是三百米,而别样衫还能气定神闲的边跑边问:“那俩家伙呢?”
黑T恤道:“当然被我们远远的甩在后面。”
别样衫道:“有多后?”
黑T恤回首而望道:“太约有三百多米吧。”
别样衫道:“那他们不是仍在原地?”
黑T恤笑笑的道:“是啊,两只乌龟,仍在流车的旁边。”
别样衫与黑T恤忽的惊愕,停止脚步,回首而望。
柳条一按红钮,一插入十指,一踩油门,喊道:“聊,撇啊!”
无聊听道,早已醒悟,幸跑不远,立即回跑。
别样衫与黑T恤见状,勃然大怒,竭尽平生之力,发足向回狂奔,快得犹如乘马御风,两脚不着地般似是车轮的高速滚转,倾而直追紧逼无聊。
流车已缓缓的流动,无聊敏捷的跳入车舱,柳条狠狠的踩下油闸,流车猛的一风飙。
黑T恤见无聊急欲跳入车舱,竟是猛的纵身一扑,犹如掷出的标枪般,扑过七八米之遥,俯身跌落,俩手一抓。
流车的一飙,刚让无聊逃过此劫。
黑T恤俯扑一抓不着,猛的跌在水泥混凝土上,疼痛不已。
流车飙一飙,吓得柳条脚停一停,头不禁回望一望。
他见状即道:“笨蛋,你们不是跑得很快的吗?来追啊?”
“追!”黑T恤虽痛但更气,拔腿就追。
柳条想不到他们竟会追来,吓得慌忙加速飞奔。
“快点啊,他们追到了。”无聊立即就在身后喊道。
流车的加速度虽甚快,别样衫与黑T恤的爆发力却更猛更速,转眼就追到,而且越逼越近,一八米,五米,三米,一米!
他们已触手可及能抓住无聊,却一时腾不出时间。
“还不快啊,追到了。”无聊急得虽后回首,却前倾身的道。
柳条年轻气刚,虽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却也一时不敢飙车,开着几十时速的流车也觉心惊胆寒,现在无聊如此惊呼急喊,更是调剂不了心绪,慌张得额汗飙冒的道:“还不使你的绝技如来神掌轰他?”
无聊正想开口道,他的神掌时灵时不灵。
忽然,一只犹如蒲扇的熊掌,猛的抓向他颈。
“如来神掌。”无聊吓得大喊一声,扭腰回身,俩掌推出。
黑T恤与别样衫见状,慌忙躲避
但是,掌心丝声过后,只是冒着缕缕青烟,仿似熄火般并没有掌劲打出。
不过,黑T恤与别样衫这样一躲,又离流车十多米。
“假的,又耍我们?”他们不禁又是一阵大怒,继续愤足疾追。
渐渐的,又是追到,十米,八米,五米,三米!“
阿条还不快啊,又杀到了。”无聊又喊道。
“怎么?你近视吗?这么近都轰不中他们?”柳条被惹急道。
“我的神掌不灵了,刚才是吓唬吓唬他们的。”无聊道。
“不行啊,杀到了,抓到了!”无聊接着急慌的道。
“我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样。”黑T恤说道一抓向他后衣。
在这危急关头,柳条却恢复了状态,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因为这一抓又不是抓他后衣,心一狠脚一踏,流车飙到了一百时速,拉了拉距离。
黑T恤与别样衬却也剧加脚速,并追流车两边。
柳条不禁大吓半跳,骂道:“乖乖的不得了,追到了,你俩傻蛋别追了,再追我告你们循环守旧,藐视现代最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黑T恤与别样衬无言不理,猛的左右挥手扬拳,但顾得脚速,却顾不得拳速,在百时速的运动里,柳条稍的一低头,无聊微的一仰首,轻易的躲开了。
体力的修炼终是难及脑力的结晶,黑T恤与别样衬坚持不了多久,脚步放慢,终是停下了倒坐在原地,仿似是高原反应,又像是哮喘般,有气出而没气入,汗如雨洒。
柳条见状,却也放慢时速,停了下来,甚是驾车后退。
车退在相距五米时,柳条调侃道:“俩位炮灰跟流车赛跑,简直是想让周星驰笑掉门牙。”
黑T恤与别样衬听道,猛的勃然大怒,没起身就扑身。
流车起速却也快,柳条一脚踩油,车就是一飙而去。
黑T恤与别样衬快啊快,流车却也快啊快。
黑T恤与别样衬慢啊慢,流车却也慢啊慢。
黑T恤与别样衬停下来加气,流车也停下来加水。
柳条就这样仿似诗青写几首俗诗挑逗材姑般,挑得他们气雷阵阵,追着流车跑啊跑,然后停啊停,流车挑拔黑T恤与别样衬停啊停,然后跑啊跑,可黑T恤与别样衬终是跑不动了。
柳条不禁让无聊驾车,从校道的树下,握起反扫帚,坐到车尾上,缚住俩脚,退车到黑T恤与别样衬十米处,把扫帚斜横在胸前,一手握住一端,一手的食拇俩指扫着扫帚杆,唱起两只乌龟道:“亲爱的,你慢慢跑,小心前面流车的扫帚!”
黑T恤与别样衬听那歌声,虽没有歇回足够的力气,却被补充了庞大的怒气,一鼓作气,猛的扑追过来道:“你这炮灰,我要宰了你。”
无聊却一脚踩油门,十指一翻,流车一飙、飙向朝阳,朝着饭堂奔驰而去。
柳条一摇身躯,若不是脚有缚住,险些掉跌流车,一扫扫帚杆唱道:“把一把一把我吓死,开始,坏的-坏的-婴儿,是乌龟就放弃!”
黑T恤与别样衬像是真的动了真格,仿似喷怒气式飞机般追得异常凶猛,却勃而不举,举而不硬,硬而不久,跑得快就不能久了,可他们虽慢,却真的坚韧不懈,不硬仍举,不举仍勃,不快仍跑,不跑仍行,可谓对流车穷追不舍,终是追上流车,一把抓住柳条。
别样衬掀着他的衣领,道:“小子!跑跑!呀,怎怎!不跑!了了,你你!欠!揍揍!得少!少啊。”
一副曾志伟的鸭公声,仿似被了般说道举手就打,却不手软弱无力,就连动作却十足十似太监了。
柳条轻轻的一挡,把他俩手放下,扶他坐在流车旁道:“花衫兄,对不起啊,我们其实不是想耍你的,而是在激发你们俩的潜力,你们俩不是想坐流车到饭堂的吗?现在无聊说到饭堂了,所以我就不跑了哦,虽然方式不一样,但结果不是一样吗?就好像我们的手法有些独特,但是结果一样是为激发你们的爆发力,忍耐力,脚力,腰力!”
别样衫又不禁有怒道:“真真!是!这样!你骗!”
柳条打断他,还扬扬拳头,奸奸的道:“是啊,你们不会追究我俩的用心良苦吧。”
别样衫现在已有气无力了,却仍死撑道:“既是!用心!良苦;就!不追究了。”
柳条站起一笑,与柳条步入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