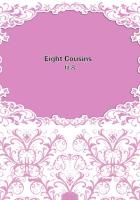此年5月,回国后的闻一多,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著名论文《诗的格律》。1927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深秋前往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此后一直在清华、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在革命烈士李公朴的追悼大会上,作为民盟成员的他作完“最后一次讲演”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潘光旦:对孔夫子“四体投地”
潘光旦,著名人文学者、社会学家、教育家、民主爱国人士。潘先生一生治学广泛,学识广博,中西贯通,文理融会,在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生物进化与遗传、性心理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儒家哲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英文翻译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毕生著译约600万言。
结缘清华,学有专长
潘光旦的学术生涯是从清华园开始的,他对清华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终其一生从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他怀着一腔振兴中华的热望,以身残志坚之躯,为清华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智慧与才华。
1913年,潘光旦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清华学校学习。每逢暑假,都用来苦读传统的经史典籍,有一年暑假还专门用来研读《说文》。如此坚持达8个暑假,对后来造就成博古通今的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2年潘先生毕业后,即赴美留学,先后获得达特默斯学院生物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遗传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多所大学任教。自1934年8月起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为止,潘光旦先生一直担任清华社会学系教授,曾讲授过6门课程,分别是家庭演化、家庭问题、优生学、人才论、西洋社会思想史、儒家之社会思想。此外还承担、参与了大量校务工作,先后兼任过社会学系主任、校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馆馆长、校务委员等职务。
潘光旦与清华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作为清华学校学生的时间是 9年,作为社会学系教授的时间是18年;如果再加上公费留学的4年,合计达到31年之久。1940年,梅贻琦与清华结缘31年之际,潘光旦曾评价说:“姑舍31年或25年的德业不论,此种关系所表示的一种真积力久的精神已自足惊人。”
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说:“大学聘请教授,有一个很普通的原则,便是一个‘专’字。凡是在某行学问上有专长的,便有被聘请当教授的资格。这个原则是不错的。但是在大学方面,待遇起教授来,也应当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也便是一个‘专’字。凡是能专诚待遇教授的大学,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们的信任和努力。”可见,用“学有专长”的原则聘请教授,以“专诚”的态度对待教授,是大学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在这篇文章中,潘光旦还谈到大学管理的另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使教授们得到精神上的谧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也在他的专门学问上继续用功夫,更求造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条件便是生活宁静”。这个意见不仅适于年长的教授,也适于年轻的教师。因为做学问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静下心来,排除杂念,钻研多年,才能有所收获。但是,官场的通则却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把这8个字用于学界,则是拿上课的时数、论文的篇数、得奖的次数等一系列数字来考核教师。各级教师整天被各种各样的表格和考核所困扰,自然不会有精神上的宁静。人不能被逼得太急,逼急了往往会出事。时下教师队伍里剽窃、造假的丑闻不少;除了当事人本身的原因之外,从客观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那些脱离实际的考核制度有关。
潘光旦说:对于教授来说,“所谓教导学生,并不专指在课堂上若干小时的知识传授;小之如教授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大之如持躬处世的日常生活,都有重大的教育价值;质言之,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极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这说明,能不能让教授过一种宁静的生活,至少是关系到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大事。
胜残补缺,客观毋我
1915年,当潘光旦还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有一次在体育锻炼时不慎摔伤右腿,随后由于结核菌侵入膝盖,故不得不截肢而致残。但潘光旦身残志不残,并不忌讳提到这一缺陷,反而给自己家里取名叫作“胜残补缺斋”;好友闻一多还专门为他篆刻了一方“胜残补阙(缺)斋藏”的印章。西南联大时期,潘光旦经常撑一个单拐打篮球。很多去看他打球的人,都被他那不屈的精神所感染。1949年新中国诞生,他欣喜非常,仅靠单腿和双拐坚持参加了开国大典的游行。
在朋友的眼里,潘光旦是个学问通透和性格豁达的人,徐志摩就曾戏称胡适和潘光旦为“胡圣”与“潘仙”。潘先生的讲课非常叫座,因为生动、形象。据说有一次他在谈到孔子时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五体投地的。”后一看自己的腿,发觉不对,又戏谑地说:“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
潘光旦在1947年为清华校庆所做的纪念文章中说,最值得纪念的是“客观与毋我”的精神。唯有客观的精神,才足以教我们毋我;而所谓毋我,就是去假我以成真我,去私我以成公我,去小我以成大我,去偏蔽之我以成通达之我,去愤恨、狠斗之我以成心气和平之我。他本人正是这方面的楷模。
笔走龙蛇,字如其人
潘光旦先生非常爱好书法。他自己所出版的著作,几乎都是他手题书封,也都是以楷书题之。在他的书房里,文房四宝长年不闲。他喜欢收藏砚台,家中大小、方圆不一的砚台比比皆是;据说最大的一方有圆凳之大。遇上有朋友索书求字,他总是乐此不疲。然后当写字时,大家都帮着磨墨抻纸,忙得不亦乐乎。清华大学前些年所建的“闻亭”,其横匾就是潘光旦先生于1947年所题,颜体楷书,中规中距。其书落字工稳、线条凝厚,观之有学者风骨、大家风范。
潘光旦的学生、同事兼好友费孝通评论说:“他的性格是俗言所谓牛皮筋,是屈不折、拉不断,柔中之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与他的性格一样,潘光旦先生的字写得也是非常的规矩而又放开的。他最擅楷书,兼长行书与隶书。他的隶书,如他题写并刻于自制的一个老竹根烟斗上,其几行铭文:“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光旦自题”。写的是一手标准“礼器碑体”,很见功底。
至于潘光旦先生的楷书风格,尽管他自己并未点明是学的哪家碑帖,但从他留下的诸多书封题签可以看出,他的书法受颜(唐朝颜真卿)体影响最大。他早年就读私塾,后在清华预科求学,写字日课可是一直都未断歇。看来,在打下唐碑坚实的底子后,受梁启超的影响,他于北魏诸碑也肯定略有所窥,所以他的楷书偶尔还兼有北魏书风。
强国优种,教育为本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忧患,有识之士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救国保种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周年时,费孝通曾说潘先生一生的学术,最基本的目的是“强国优种”,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国人的根本素质。
潘光旦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针对我们民族的弱点,潘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生育节制,生得少、生得优,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刚劲的成分等。
潘光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安排,而在教育。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将来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的。读洋书与去国外,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他主张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学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认识科学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此外,潘光旦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的观点。
潘光旦是“学行合一”的一个人。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他刻在自制烟斗斗腹上的十二字铭文,其实正是他本人最恰当的写照:“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
潘光旦先生的一生,是勤奋向上的一生、自强不息的一生、甘洒热血的一生。
【大师小传】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回国后至1952年,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馆长等职。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被平反。
老舍:“逸兴遄飞时,常有妙语脱出”
老舍是我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深受群众爱戴的“人民艺术家”。上世纪30年代,老舍先生曾先后两次受聘执教于齐鲁大学(校址在今山东大学西校区),在济南生活、工作了4年多的时间;又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执教近2年。在山东执教的经历,无论在老舍的个人生活还是创作生涯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第一次执教齐鲁大学
1930年初,老舍结束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职,返回祖国。当年7月,他接受在山东济南的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的聘书,任该校“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教授。
有人不禁要问:老舍为何不就近在北京找个大学任教,而要舍近求远,离开老母和北京,远去山东济南呢?通常的看法是:由于学历较低,老舍迈不进北京大学的高门槛,只能远赴山东。对此,老舍之子舒乙在回忆中写道:“当时,国内名牌大学里国学研究极其兴盛,尚古之风刮得很劲;而且,似乎研究得越古,越显得学问大。在这种气氛下,以擅长白话文小说为本事的老舍,自然很难在北平的名牌大学中找到立足之地。何况,他又没有大学学历。”
然而,山东齐鲁大学的门槛也并不低,它的前身是私立山东基督教会大学,是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开设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以前,系、所主任及教授,大部分是由外国传教士担任,其教学水平“接近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其国文系素重旧学。历届系主任和教员,多是擅长科举八股文的举人、拔贡一类老夫子,所开课程为文字、音韵、经学、诸子、尚书、文选等。这样的大学,何以便容得没有大学学历的老舍立足呢?
事情得从齐鲁大学的改制说起。1929年,在经历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要求所有民办大学一律立案纳入管辖(并冠以私立两字),校长必须由中国人充任,外国人任董事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于是,齐鲁大学的校长换成了中国人,系、所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时任齐大文理学院院长的林济青兼任校长后,亲自去北京延揽了6位专家、学者,分任文理学院各所主任,老舍便是其中之一。
齐大“国学研究所”的成立,是林济青任校长后的得意之作。此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想仿效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从美国查尔斯?霍尔基金会取得经济资助;二是顺应当时“国学”研究的热潮,以加快学校中国化的进程。
据说,老舍之所以得到邀请,推荐者正是“国学研究所”的筹备及主持人——墨学大师栾调甫。栾氏后人曾回忆道:“老舍来到齐大之年,正是该校‘国学研究所’成立之时。这所研究所是在栾调甫的积极倡议并在文学院林济青院长的大力支持下组建起来的。研究所的建立,了却了栾调甫多年想培养高级国学研究人才的夙愿。他在物色研究人员时,特地提出一个由名家、学者组成的名单,老舍先生就是在这个名单中,由林济青院长亲自出马聘请来的。”
老舍先生在齐大所开的课程,除了一年级的《文学概论》和《文艺批评》外,还有《小说与作法》、《但丁研究》与《莎士比亚研究》。《小说和作法》是给国文系二年级开的,《但丁研究》与《莎士比亚研究》是三年级的选修课。
老舍先生讲这两门课从不看讲义,也很少用手势,却能挥洒自如、纵横跌宕。虽然他带有浓重的北京口音,但经过了淘洗和净化,没有那种京片子的贫、虚、俗,没有哗众取宠的江湖气。老舍在课堂上举的例子多是外国的,课却讲得轻松动听、并不涩奥,颇有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味道。
此外,老舍先生对当时的军阀统治颇为不满,课堂上亦有言涉时政之辞。但多是反语、冷箭,含沙射影,藏而不露。
先生的《文学概论》与《文艺批评》课大受青年学子欢迎。除了国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之外,其他许多系的学生也跑来旁听,这在齐大实属罕见。
当年齐鲁大学的学生张昆河曾有过这样的回忆:“老舍先生讲课,是坐着的。后来知道,他有腿病。但讲着讲着,兴致上来,便也站起来讲得逸兴遄飞时,常有妙语脱出,冷丁袭来,引得哄堂大笑。但先生自己可不笑,始终板着脸,一本正经。”
老舍在第一次执教齐鲁大学期间,还主持和编辑了《齐大月刊》。《齐大月刊》是由齐鲁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合办的一份综合性刊物;除刊登学术论文外,也刊登部分文艺作品和一些反映学校动态、校际往来等内容的消息报道。编辑部由文、理、医三学院各派两名教师和两名学生任编辑委员,老舍先生就是文学院选派的两名教师之一;并被选派为编辑部主任,主持该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齐大月刊》创刊号于1930年10月10日正式出版,为大32开本,90余页。老舍为创刊号撰写了《编辑部的一两句》和《发刊词》,阐明了该刊的创办背景和内容及办刊宗旨。《齐大月刊》自创刊至1932年休刊,共出版了2卷,每卷8期。
在主持《齐大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的过程中,老舍在不违背《私立齐鲁大学印行月刊简章》中规定的原则“文艺作品不得过月刊页数四分之一”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加外国文艺理论与文艺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以及新文艺作品所占的比重,给当时死气沉沉的齐鲁大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