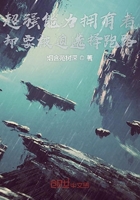全国解放的那年夏天,云南大学文史系特邀“国宝级教授”刘文典演讲。这一次,他讲的不再是《庄子》,也不再是《红楼梦》,而是《关于鲁迅》。这也是他首次公开谈鲁迅。此次演讲大约进行了2个小时,听者挤满了教室,欢声不断,笑语连天。当年,刘文典和鲁迅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同在北大文科教书,同为《新青年》写稿。最初“虽然常常见面,但是很少往来”。有一次,刘文典刚好经过鲁迅的教室,于是便好奇地走了进去,结果,一听是2个小时。他发现,鲁迅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刘文典说:“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佩服他,崇拜他。”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的云南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当地报纸先后发表了27篇“讨伐”刘文典的“战斗檄文”。后来,全国思想改造进入高潮,有人当面责问刘文典:“你为什么污辱鲁迅?”刘文典理直气壮地说:“绝无此事。”揭发者说:“二十多年前你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公然用小指比喻鲁迅,是何居心?”原来,刘文典有一次上课时,偶尔谈及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跟章太炎学《说文解字》,于是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他举手伸出了小指,纯属巧合。没想到,居然成了恶意挑事人的把柄。
对于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刘文典坦然一笑说:“用小指比鲁迅确有此事,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小指比老么,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我们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此话一出,揭发者无词置辩。
云南解放后,刘文典一直在云南大学执教,他是云南省唯一一名一级教授(文科),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我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更高兴的是以一个九三学社成员的身份来做一个共产党的助手。我愿意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化而奋斗!”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病逝于昆明。他毕生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为我国文化遗产的积累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为纪念刘文典诞辰110周年,安徽大学、云南大学联手整理出版了近千万字的四卷本《刘文典全集》。
【大师小传】
刘文典(1891—1958),字叔雅,原名文骢,笔名刘天民,安徽合肥人。人文大师,校勘学家。九三学社成员。自幼入教会学校学习英语。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受到老师陈独秀、刘师培的影响,积极参加反清活动。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其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随章太炎学习《说文》。1912年回国,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办《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1913年再度赴日,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并参加中华革命党,从事反对袁世凯复辟活动。1916年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发愤从事古籍校勘,经过数年努力,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好评,学术声誉由之大振。1919年五四前后,曾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在北京大学期间,讲授《淮南子》研究、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等课程。1927年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校长等职。1928年重回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兼任北大教授。1938年辗转至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1943年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直至退休。曾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第二届委员。1958年去世。
刘文典一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校勘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成就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过的课程有:《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杜甫研究》、《史通研究》、《校勘学》、《文选学》等,为培养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等。
汤用彤:打通古今中西,授课一泻千里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为数不多的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他精通中国文言文和英文、梵文、巴利文等多种外语,毕生致力于国学和印度哲学研究,教学和研究领域涉及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逻辑学、哲学概论等。他本着“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探求”的治学精神,精考事实,探本求源;通过研究民族文化发展、沿变的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总结规律,展示经验和教训,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问题,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论稿》、《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讲义》等。
听他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
汤用彤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和教育家,他对教学认真负责,课前准备充分,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凡是由他开设的课程,从头到尾,全盘计划,既广博又精专,范围兼容中、西、印三大文化体系,体现了当时国内甚至国际的最高研究水平。
1920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单独为吴宓讲授“印度哲学与佛教”;回国后,又一直在各大学主讲印度哲学。1929年编成讲义,增删后定名为《印度哲学史略》并出版,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重要著作。
王太庆教授回忆说:“他的讲授逻辑性强,语言平实。古代印度思想中,有很多成分在现代中国人看来非常可怪,他却能把它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比某些印度学者讲得还要明白。这是因为他严格掌握史料,善于发现问题,从梵文、巴利文原著中进行研究,用西方现代的逻辑方法整理,又顺着中国人固有的思路和语言来表达的缘故。汤用彤当时著有《印度哲学史略》一书,内容深邃而行文简明,读他的书、听他的讲确是一种精神享受。”
在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任教期间,汤先生先生几乎讲授过哲学系的所有课程。其中,“西洋哲学史”可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标志着“西哲东渐历史”的第一手文献原件。
据学生回忆,汤先生上课时,手里提一个布袋,穿着布鞋、布大褂,数十年如一日。他上课,从不带讲稿,也很少写板书;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然后一泻千里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的语言,语调也没有什么变化。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他经常是用英语。就这么一直讲到下课铃响起。听讲者稍一走神,听漏了一语半句,就别想再跟上他的进度。因此学生只能埋头记笔记,生怕漏记一字一句。在课堂上,除了汤教授的讲课声外,便是学生们记笔记的“沙沙”声。
1923年,汤用彤先生受欧阳渐之聘,兼任支那内学院研究部巴利文导师,讲授“金七十论”、“释迦时代之外道”两门课;讲义后来整理成文,刊于《内学》杂志。
南开的骄傲
1926年至1927年间,汤用彤曾在南开大学执教。那时,汤先生年方33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辰。当时南开大学刚成立数年,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正在海内外延揽人才。对于归国不久且小有成就的哈佛大学高材生汤用彤先生,理所当然在其收揽之列。1926年,汤先生正式接受聘请,担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朝气蓬勃的青年,遇上蒸蒸日上的学府,无疑是一个相得益彰的组合。未来的大师在南开成长,南开也因大师而辉煌。
汤先生刚来到南开,便被委以重任。在现存南开“文科课程纲要”中,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汤先生亲自讲授;其中包括逻辑学(形式伦理学)、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印度哲学史、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与此同时,汤用彤先生与日俱增的学术造诣和成就,也为其赢得了南开师生的推崇与尊重。
汤用彤先生用极其严谨的学术态度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他决不按照他人的转述来安排教学内容,而是严格地按照所讲哲学家本人的主要著作。因此,汤先生的讲课,更像是对哲学家原著的导读。在讲到哲学家的某个观点或问题时,汤先生都要指明出自某本著作的某章某节或某个命题,尽量做到有根有据、客观真实。汤先生讲课从不轻易下断论,而是适时引导学生思考问题,鼓励学生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准确理解前贤往哲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剖析解答问题。他十分注意因材施教,循循善诱。邓艾民教授回忆说:“他给我们全面、忠实地介绍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材料丰富而又不显得烦琐,分析清晰而又不流于空疏。即使自由主义习气很浓的同学,也舍不得缺课。”
虽然汤用彤讲课严格遵照原著,但绝不是“照本宣科”。他在通盘把握哲学家思想的基础上,以西方哲学分析、推论的精神和方法,再现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换言之,先生要求他所讲授的内容应有客观的真实性,不是那种表面的、细枝末节的或形式主义的真,而是运用科学方法所达到的本质的、整体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在汤先生看来,重分析、重逻辑、重方法是西方哲学传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而中国学术传统,不重分析也不从事分析。
在讲到任何一个哲学家时,不管他是理性派还是经验派,汤先生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方的“方法”。汤先生在进入笛卡尔哲学之前,就以题名为“心理学的分析”的一章,对笛卡尔所使用的思想、感性、想像等心理学的名称进行分析,一方面辨明它们在笛卡尔哲学中与现代的不同意义,另一方面揭示它们在其哲学中的多种用法和含义。
另外,汤先生对哲学家的某种根本的观点或原则,总要作一种客观的质疑。在《哲学概论》讲授大纲中,先生的这种客观质疑方法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频繁。如“真误”这一章,列举出了西方哲学史中关于真理标准的4种学说——相对说(即符合说)、自明说、实用说和贯通说。他对每一种学说都提出了质疑,而没有对其是非做出主观的最终判决。但是,这绝不是说先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张或观点。如在讲到“休谟哲学的两个解释”时,先生针对康蒲?斯密把休谟哲学解释为从洛克而来的一种“信仰一情感决定论”的观点,列出事实进行了反驳,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赞同康蒲对信仰的重视,但不同意他关于休谟把哲学放在新的情感基础上的观点。”
总之,汤先生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对象,即作为一门客观的学问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讨。这不仅是由于国人对西方哲学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而且是由于“我国几无哲学”,因而就更应采取虚心的客观态度,将其作为客观对象而认识之、研究之。在当时“西化”成为时髦、“中国文化本位”呼声四起的情况下,先生对西方哲学的这种态度真可谓特立独行、独树一帜,在这面旗帜上写下了“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这样一句掷地有声、颠扑不破、气势磅礴、意蕴精深的至理名言。
冯契先生回忆道:“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传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并且都是高质量的,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他讲课时视野宽广,从容不迫;资料翔实而又不烦琐,理论上又能融会贯通,时而作中外哲学的比较,毫无痕迹;在层层深入的讲解中,新颖的独到见解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并得到了论证。于是使你欣赏到理论的美,尝到了思辨的乐趣。所以,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的几位国学大师,凡是既能熔铸古今、又能会通中西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人之私言。”南开出此大师,实乃幸事!
1927年5月,汤用彤先生离开南开大学,赴中央大学哲学系任职。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汤用彤先生与南开的缘分并未因此而终结。在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时期,汤先生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又同南开师生走到了一起,对南开哲学系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半生执教北大
汤用彤先生的教学生涯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几部传世之作皆发表于北大期间,至今仍是哲学系和宗教学系的重要参考教材。由于他成就卓著和高风亮节,深得北大师生敬重与爱戴,因而“长期担任北大重要职务,起着文科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组织者和带头人的作用。因此,他的治学态度、方法和办学方针,对北大文科的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对北大之特殊精神的弘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汤先生治系、治校特别看重两件事:一是“聘教授”;二是学生选课——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根据他们的兴趣和才能来指导选课,然后亲笔签字。
20世纪30年代,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钱穆、梁漱溟、陈寅恪等常在一起聚会。熊、蒙二人常就佛学、理学争辩不休;梁、熊则常谈及政事,亦有争议。只有汤先生不喜欢争论,“每沉默不发一语”。朋友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汤菩萨”。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载,他在北平曾与汤用彤有过交往,并多次清谈。但每当两人之间发生学术上的争论时,汤用彤总是在一边沉默不语。
1931年汤先生到北京大学后,每学期开两门课,中外并授,讲有中国佛教史、笛卡儿及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概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研究等课程。1939年在西南联大时,汤用彤共开了7门课:印度佛学概论、汉唐佛学概论、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其中,印度哲学史是三、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此后隔年讲授一次。当时,必修课与选修课搭配合理,选修课的门类很多,学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汪子嵩曾感叹道:“一位教授能讲授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三种不同系统的哲学史课程的,大概只有汤先生一人。”冯契也回忆说:“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传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并且都是高质量,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
1936年,我国首次开设魏晋玄学课。汤先生为纪念这个特殊的年份,特意为其幼子取名为“一玄”,可见他对开玄学课的重视。季羡林先生1946年到北大后,整整听了一年这门课,一堂课也没有缺过,并记有详细的笔记。他回忆说:“我觉得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特殊的享受,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汤用彤先生研究魏晋玄学,是结合佛教思想并且比较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的思想)来考虑的。他既运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又以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玄学家们的著作,做出严谨、细致的解释和结论,从而“开创了魏晋玄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