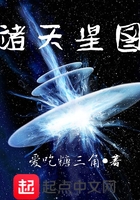一
门外站的不是别人,正是阎老太。她定定地立在那儿,月光之中形同一个鬼魅,两眼射出狠毒的光,两腮由于气急而变得鼓鼓的,就像两个毒气袋。
两个女人立时惊在那儿,吴妈发现只有阎老太一个人,狠狠心冲了过去。阎老太看见兰花手中攥着鹿角刀,不禁一怔,大叫着:“来人哪,来人哪!”那叫声非同小可,吴妈与兰花都大吃一惊。吴妈只觉额上一热,一股仇恨从心头涌起,她的全身不觉生出了一种力量,两眼直直地盯着阎老太撞过去。
阎老太的第二声喊还没有出口,就被重重地撞在地上。也该她命绝,脑后刚好磕在一块石头上,她这一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两个女人稍一迟疑,向着阎府东北角牛圈方向奔去。
阎大头和隋二正在前院正房里坐着,隐约听见后院响起喊声。隋二道:“东家,好像出事了。我听好像是老太太的声音。”阎大头急忙说:“把家丁们叫起来,都到后院去。”说完自己也披衣出屋。
家丁们慌乱地向阎家后院跑去,不久就听有人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李兰花跑了!李兰花跑了!老太太过世了!老太太过世了!”阎府大院里顿时鬼哭狼嚎。
阎大头到了后院,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倒在地上的已没有了一丝气息的阎老太,好久才缓过来。他气急败坏地指着那些家丁吼叫道:“都给我去追李兰花……都给我去追李兰花……追不回来,我一个个收拾你们……”
阎府的家丁分成四拨,向四面院墙而去。隋二带着几个家丁向牛圈的方向追去。
阎府大院的高墙是用垡子泥打成了。垡子泥是从草原上的盐碱地中运回来的。四马拉的犁杖在盐碱地上来来回回地犁过,最后盐碱地被分割为一块块五尺见方的泥块,那就是垡子泥。那些大户人家将垡子泥用马车拉回来,垒成高高的院墙,风干之后,不怕雨淋虫蛀,颇为坚固。
还是在上次巴山打狼时,兰花和吴妈看清了阎府的地势,两个女人撞翻了阎老太,直接奔向牛圈的方向。来到牛圈下,兰花猛跑几步上了墙。回头再看吴妈,她可没有兰花灵便,手搭在墙头上,努力地窜了两下,又落回到地面。
耽搁了片刻之后,只听有人大喊:“不好了,不好了,李兰花跑了!李兰花跑了!老太太过世了!老太太过世了!”兰花心头一紧,把鹿角刀向腰带上一插,对吴妈说:“我来拉你。”吴妈听说,慌急中把一只手递给了兰花,另一手去抓墙面。无奈吴妈太重,兰花费了半天劲儿,也没能将吴妈拽上墙来。
兰花跳下墙,说:“我先帮你上去。”,兰花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把吴妈弄上了墙。这时就听见阎府大院中发起喊来:“捉住李兰花,大当家的说了,捉住的有赏。”兰花翻身上了墙,心口已怦怦跳得厉害。“大婶,快跳。”兰花说。接着,自己纵身跳了下去。吴妈一闭眼,随即跟下去,可一到了墙下,她就重重地跌坐在地上。兰花拉了她两下,她才起来,一抬头,几名家丁已经从墙顶探出头来。
吴妈推了兰花一把说:“兰花,你快走,快走。不要两个都被捉住。”
兰花听见,眼泪簌簌地流下来,一转身,向村外的大草原上跑去。
一名家丁跳下来拉起坐在地上的吴妈,说道:“嘿嘿,捉住了一个。”
隋二在墙上说:“大家追前面的,前面的是李兰花。”其余的家丁又追了过去。
二
这一闹腾,大阎坨子村不再安宁了。这一回,阎府的行动变成了公开的,立时弄得全村狗咬吵吵的。兰花七拐八拐出了村口,借着月光朝大草原奔去。她跑得还真快!甚至都觉出耳边风声作作的。顷刻之间那些家丁便被甩到了后边。有人放起枪来,枪声在夜里听起来让人心慌。兰花咬着两只辫梢,脚下发了狠,一门心思地向前跑。
隋二带人追了一会儿,眼见着捉人无望,便带着家丁折了回去。刚进村口,就见村口上依稀之间人影一闪。隋二擦擦眼睛问:“兄弟们,你们看见人影了吗?”
“什么人影啊,鬼惊鬼诈的。”一个家丁小声叨叨着。隋二也以为看花了眼,遂不再说什么。这些人急忙进了村口,向阎大头报告去了。
其实,隋二的眼睛并没有看花。刚才村口上的确是有一个人。隋二他们走后,那个人影又出现了,疾步向村子里行去。
狗叫声与嘈杂的人喊声惊动了一个人,那就是二牛的父亲。二牛接连几天晚上都没有回家,二牛父亲知道他是在兰花家,可今夜狗叫吵吵的,到后来竟起了枪声。二牛的父亲预感不妙,便一个人起身,朝巴山家走去。
秋月的光辉下,李巴山家的院子里一片狼籍,门板被撞翻在地,纸糊的窗户也被捣烂。院子里丢着一根木棍,脚步杂沓的痕迹印满了整个院子。二牛的父亲心下一沉,心想:“坏了,莫非是二牛和兰花出了事?”他沿着纷乱的足迹出了院子,迎面猛然冲过一个人来,一把将他揪住,问:“老哥,发生了什么事?”二牛的父亲骇了一跳,这才看清原来那人正是李巴山。
“巴山,你可回来了。这两个孩子八成是出事了。”二牛父亲说。
李巴山看了二牛的父亲一眼,大步进了自己的院子。
二牛父亲跟在他身后说:“巴山,你咋才回来?”
“甭提了,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李巴山说
两天前,巴山打足了皮张就要返回来。那天临近中午时分,他正坐着吃前一天剩下的烤兔肉,忽见前面距离很远的一座大沙丘上转下两个人来。那两个人下了沙丘,聚在一块嘀咕了一会儿,一个转向了东北方向,一个直朝自己的方位行来。开始时,巴山并没有引起高度的警觉,只当他们是两个和自己一样的猎人。转瞬之间,那人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清他的那张歪歪扭扭的中风脸。巴山想:“这深秋时节,在草原上转的,大多是苦命人。”便直身站起来,向那人邀请道:“朋友,过来吧,我这还有半只兔肉。”那人稍稍一怔,放着大步,仿佛心急火燎地向他行来。巴山哪里知道,中风脸和青瘢脸已经议定:谁先发现李巴山便拿七成赏金。中风脸这样轻易发现了李巴山果然喜出望外。心下道:“老子发财的时候到了。”生怕巴山再无了踪影,就大踏步过来。
巴山只道那是关东人的豪爽,倒不介意那人的卤莽。等中风脸到了近前,十分友好地将那半只熟兔肉递过去说:“朋友,见面分一半。”
中风脸接过兔肉后,倒冷静了许多。“多谢了。”他嘴上道着谢,一双眼睛却打量起李巴山来。那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在秋日的阳光中,他叉腿立在那儿,高高大大的身量,带着一种凛然之气。青碴碴的短髭使整个面部显得粗犷豪爽。他那双热情而坦荡的眼睛由于经受着打量而略显不快,眉宇间微微泛出冷峻的神情。此刻,正站在那里,右手向他平举着那半只兔肉。相形之下,中风脸容貌伧俗。想到自己心怀鬼胎,不觉心竟突突乱跳起来。
他赶紧接过兔肉,装成笑脸说道:“草原上的路真难走啊!你莫不是李猎户吗?”
巴山一惊,问:“你怎么晓得?”
中风脸指了指铺在丘坡上的皮张说:“不是李巴山,谁能打得那么多皮张。”心下道:果然是他。
两人坐下来闲说了一会儿,中风脸一直伺机下手。他这一动心机,兔肉吃的也不那么爽快了,接连噎了几口。他忽然来了主意,问巴山道:“老弟,有水吗?”
“有,”巴山向矮丘后面一指说:“那有个湖泡,水倒是清亮。”
说着站起来向丘顶走去,中风脸跟在后头,暗暗地摸出一只短枪来。
“那不是……”就在巴山转身说话的瞬间,枪声响了,子弹擦着他的面颊飞过。巴山“哎呀”一声顺着丘坡滚下。中风脸举枪瞄了几瞄的当,巴山已滚落到他的脚下,乘势将他掀翻在地。中风脸的短枪也被甩落出去。两人滚打在一起,几个骨碌之后,中风脸的手中多了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巴山猛一翻身将他压在身下,两手一扭他的腕子,那把匕首就落在中风脸的身边。中风脸不动了,睁着两只惊恐的眼睛盯着巴山,气喘吁吁地哀求道:“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巴山问:“你为什么这样做?姓李的什么时候得罪过你?”
“是阎大头和马警尉让我们来的,全是他们,全是他们。”中风脸一迭连声地说。
这时就听见远处有人喊道:“中风脸,寻着了吗?”是青瘢脸循着枪声赶来了。
巴山抬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青瘢脸的叫声让中风脸又来了一股邪劲,他趁着巴山由于张望而松劲的瞬间,猛然发力,双手挣脱了巴山的腕子,右手飞快地摸起了地上的匕首,向巴山刺来。只听“呲”的一声响,巴山的袖子被刮开。巴山迅速地夺下匕首,耳朵中听见青瘢脸已经越来越近了,他一狠心将匕首用力地扎了下去。中风脸把脸向旁一歪,再也不动了。巴山一跃起来,抄起猎枪飞身上了沙丘。这时,青瘢脸的声音不见了,连人影也没了。巴山在丘上等了一刻,再也不见青瘢脸。他下了丘,脱下那件撕碎刮破的衣服扔在了中风脸的身边,换上了兰花给他带的另一件衣服,背起皮张绕了一个大弯,从另一个方向折回大阎坨子。
想到这,巴山对二牛的父亲说:“一定是阎大头干的,我去找他算账!”
“巴山,你一个人能行吗?我和你去。”二牛的父亲说。
“不用了,记住,我要是出了事,别忘给我收尸。”巴山说完这句话,把牙一咬,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两下,丢下二牛的父亲,直向阎家大院行去。
三
李巴山来到了阎府的高墙外,侧耳倾听,哭声隐隐从院中传出来。只不过那哭声有些怪怪的,就像精心布置的省时省力的接力唱,一声低下去,一声又高起来,各种腔调都有,时断时续,咿咿呀呀的,大多是男人的声音。巴山来不及细想,小心地将枪药下进了枪口。他背好了枪,飞跑了几步,翻身上墙。
吴妈被家丁们带回阎府后,阎大头命人将她吊在井台旁的那棵老树上。阎大头的眼睛都红了,他犹如一只发疯的野兽,让一名家丁把吴妈上身的衣服扒下来,扔在井台上。他手持一根皮鞭,劈头盖脑地朝吴妈身上抽打。
阎大头一边抽打,一边叫骂:“臭婆娘,反了天了。居然伙同李兰花杀了我亲妈。”他骂到这,忽然哭喊起来:“娘啊,我一定杀了这个女人给您陪葬。”
这时被隋二打发到草甸子上去的那两名家丁回来了。阎大头问:“李二牛死了?”那领头的家丁神色惶惶地说道:“回……回东家,姓李的……才被我们打死在甸子上。”阎大头见他的神色有些不对,又问:“废物,打死一个人咋吓成这样?”
领头的家丁说:“东家,草甸子上的狼嚎真是吓人,兄弟们差点遇上了狼群。”
阎大头回身对树上的吴妈甩了几鞭子,嘴上发狠道:“李兰花,让你逃,草甸子上的狼群也会把你咬死……”
他的三太太秋月也来凑热闹,接过鞭子说:“大头啊,你先歇会儿,这个女人让你费了多大的气力呀?吊在树上还怕飞了。我也替老太太打她几鞭子。”
吴妈当然明白,秋月为什么打她。
阎大头对那些家丁发话道:“都到老太太的屋中守灵去,要像发丧你们亲妈那样哭,都给我去。”
家丁们本来就怕阎大头把一肚子邪火发泄到自己身上来,听到这句话,如同得到赦免一样,排着队一路小跑奔阎老太的房间去了。
阎大头在树下站了一会儿,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独自一人回正房了。秋月本想多打几下,过足手瘾。无奈,阎大头走了,那些男人们乱蝇般的哭声,让她感觉有些害怕。她赶紧打出最后一鞭子,扔下鞭子,扭着屁股去追阎大头。
巴山进院时,院子中已空无一人。陡然瞧见井台旁的高树上似挂着一个人,他便飞步过去。
吴妈只听见脚步声,心想,一定是阎大头又来了,遂闭上眼睛将头歪向一边。
脚步声在她面前停下来,接着便是死一样的沉寂。
吴妈睁眼一看,自己身前站着一个人。她仔细一看,蓦然辨清了那人,吴妈叫道:“你,你不是李巴山吗?”
巴山早已认出那个女人是吴妈,他不明白吴妈为什么会被吊在树上。
“告诉我,阎府出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被吊在树上?”巴山急切地问。
吴妈说:“是我放走了你的女儿。”
巴山惊喜地说:“你是说你放走了兰花,那么说兰花没事了?”他早就断定兰花一定是被阎大头掳了去。现在,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我现在就放你走。”巴山说着,解开绳子,把吴妈放下来,那女人瘫软在地上。
吴妈说:“先前阎家人把二牛装进了一条袋子,抬到草甸子上去了,兰花晕了过去,我好不容易才弄醒她。”
李巴山心下一沉:“咱们赶紧去救二牛。”
“晚了,阎家那几个家丁刚从草甸子上回来,他们对阎大头说,二牛被他们打死了。”吴妈忽然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李巴山,你要是一条汉子,就不要放过阎大头,是他害死了你的女人,一定要替你的女人报仇啊!”
李巴山登时像遭了雷击一样木在那里。好久,他才说:“你怎么知道?”
“是阎大头亲口说的。”吴妈平静的声音中淤积着一种仇恨。耻辱和毒打让这个女人生出一种报仇的欲望。
李巴山只觉得心窝一酸,他黯然地呆立了一会儿,随即一股愤恨之火在他心底窜腾而起,一种早就隐藏在他身体里的力量迅速被唤醒,并且就要爆发出去。他对吴妈说:“你先在这儿等着。”说完,直奔阎家正房而去。
吴妈捡起地上的衣服披在身上,将扣子一颗一颗系上。抬头一望,李巴山已经走远了。
阎府正房中的灯正亮着,两个身影清晰地映射在窗子上。一个大头鼓脸,身材肥大,一个小脑细脖,瘦骨伶仃,正商议着阎老太明天发丧的事呢。秋月已经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这女人尝了心愿,对这场变故的结果倒有些庆幸。回到房中她哼了一段做妓女时常在嘴边的小曲,就躺下了。恍惚间入了梦,见一个男人向她走来,她高喊着:“九子,是你回来了,你可回来了。”就迎了上去……
李巴山这时已窜到阎府正房前,躲在了窗下。只听阎大头说:“都是孽呀!都是孽呀!早知道这样,当初我怎么敢碰李巴山的女人。”又听隋二说:“跑了一个丫头,成不了什么气候。前几天,您雇人杀了李巴山,今晚上又结果了李二牛,等九子买了枪回来,大阎坨子就太平了。”
李巴山听了,再也按耐不住,他呼地站起身,迫不及待地把枪口撞进了窗户,对准阎大头,扣动了扳机,阎大头应声倒了下去。巴山从窗口中拔出枪来,一脚踢破窗户,飞身进屋。屋子中隋二已不知去向。只见阎大头躺在地上捂着流血的胸口惊恐地望着他:“李……李巴山,你……你咋没死?”李巴山毒毒地瞪着他,突然抄起一张凳子,对准那颗大头砸了下去,他断定阎大头再也活不成了,才提着枪,从窗口飞身跳出去。
那时阎府后院中男男女女鬼哭狼嚎似地喊叫起来。那些家丁们具在后院给阎老太守灵,听见枪声,也喊叫着向前院跑来。他钻进马棚,牵出一匹马来,飞身上马来到大柳树下。吴妈正在那儿等着他。他将吴妈拽上马,两腿一夹,冲向阎府大门。恰巧阎府那几个后从草甸子上回来的家丁,忘了给大门上锁,巴山打马出了院子。
他骑着马一口气奔到了大阎坨子下,发现后面并无人追,他停了下来。回过头来看了看夜色中那熟悉的村子,又将目光投向了长长的大阎坨子。那蜿蜒蠕动的脊背,就像一条土龙,将人居的村庄和兽踞的荒野区分开来。作为一位猎人,死在他枪下的狼不计其数,但他还从未将枪口对准过人,除非那人已是失去了人性的畜生。
当他回想起阎大头倒在血泊中的那一刻,他并没有感到丝毫惧怕,只感有一种血性的东西快意地撞击他的四肢百骸。关东汉子,恩可以在心坎上涌泉,仇可以在刀尖上沥血。
那一夜,他在大草原上开始了另外的一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