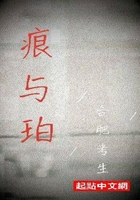5一说到变瘦,楼主的肚子饿了,开始手撕包菜。饭店愿意用刀切,没情调。可能您会问,为何要撕包菜,而不是切猪肉呢?因为这是《都灵之马》,你得找个耐干的活来做。马夫的女儿用来装衣物的木箱子蛮有范儿的,有机会也要入手一个。父女俩的搬家以失败而告终,瞧他们狼狈地装货卸货的样子,可见搬家公司的重要性,再次让人质疑生命的意义。
6全片只有30个镜头却拍了很久,因为动物很麻烦,尽管贝拉·塔尔曾在《撒旦探戈》中执导过鸡、狗和猪,说服奶牛演床戏,并在《鲸鱼马戏团》里让一头鲸鱼保持不动,但这次的马儿却让他伤透脑筋。以这个推上去的特写为例,马儿一看到摄影机盯着自己就会羞涩地转过头去,导致镜头报废,这对长镜头电影影响更坏。之前拍她拒绝进食的一段戏,她也总是不争气地大嚼特嚼。导演多次发飙,后来发现这并不是一匹母马,而是被阉了的公马,立刻抱着TA大哭。
7没看过贝拉·塔尔的是普通青年,佯装要看的是文艺青年,真的看完的是二逼青年——除非是为了爱,他的片子可以用来测试爱人的忠贞度,如果TA愿意为了你把这片子看完,才说明真的爱你;如果愿意为了你把《撒旦探戈》看完,那就是爱到海枯石烂,其他的都是扯淡。
8小屋进入黑暗,黑暗象征着虚无,虚无比地狱恐怖,所以要有全黑的环境相配合。这消极的世界观来自片中人的处境:没有马(步兵)的羡慕有马(骑兵)的;有马的羡慕有两匹马的;有马的马不吃草(汽油贵);有两匹马的四处流浪(房价贵);年轻女子没对象;她老爹又不像小津老爹那么热心。难怪贝拉·塔尔说,“我年轻时也渴望改变世界,到老才发现这很复杂。”
9蛀虫不吃木头,马儿不吃草,最后连人都不吃土豆了。贝拉·塔尔准确地抓住了生命存在于世的最大意义,即对美食的渴望,口舌之欲的破灭就成为万物必将走向末世的隐喻。这也解释了为何是黑白片,以及为何土豆不切丝不放油——想想看油锅发出的嗞嗞声,还有黄得透明的嫩土豆丝,看到这么美好的东西,您是不会相信上帝已死的。
感后记:楼主将攻略送给了因为看不懂《都灵之马》而自惭形秽的朋友。他依葫芦画瓢地创造全黑的环境,但是在拉好窗帘、走回沙发的过程中不小心磕到了茶几,撞断了一根小腿骨。显然他没搞明白手电是用来干吗的,就好像我始终不知道该如何标句号。
丑人多作怪
最近有主流媒体开始讨论是否需要影评人的问题,我猜他们是找不到凑版的东西了,因为答案是如此的显而易见——我们不需要影评人,就像我们不需要历史教授、哲学教授、文学教授、艺术史教授一样,像文史哲这种小儿科的东西,没有门槛,让发烧友利用业余时间搞一搞就够了。其实大部分跟文科有关的行业都没有门槛而且没有意义,但是笨人也得生活啊。至于影评,你把片都看完了,还得靠别人的评论才知道好看还是难看,也许你根本不该看片,而应该去医院拍个片。当然,现实中不但存在文史哲教授,还有人给他们发工资,所以影评人的存在也没有特别碍眼,更何况国外早就有了。
接下来,我是很想严肃地讨论一下关于影评人的事情,但是总有一些不相干的外来因素在干扰我这么做,比如他们长得太丑了,丑到你无法斜视,丑到你觉得必须要讨论一下。有的时候,我看娱乐频道的花边新闻,满眼的俊男美女,冷不丁会出现个接受采访的影评人,本来就无一例外地丑到爆,对比之下丑得更加出挑。要说写影评会让人变丑,这个就有点唯心了,因为其他写字的人也很丑。我在《看电影》编辑部工作过,多少是有点发言权的——你走进编辑部,就好像走进了一部费里尼的电影,通俗点说,就是进了《生活大爆炸》剧组。
来面试的时候有个小考,要求写一篇影评,给我放的片是塔可夫斯基的《轧路机和小提琴》,我此前既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没听过塔可夫斯基,我只有过开轧路机和垃圾车的理想,但是你也知道,人一上岁数,就不再浪漫了。我胡写一通,竟然被录用,而且老编辑对我还不错。很多年来都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丑了,才明白他们是以貌取人,觉得丑到我这种程度的,肯定是文字方面的可造之材。编辑部的人事安排也跟丑的程度成正比,新编辑还能看,老编辑看不能,主编就只能待在自己的小屋里,跟象人似的不见人,开策划会的时候大家都盯着地面,他还以为我们是在思考问题。众多办公室恋情也因此水到渠成,“既然咱俩都这么丑,那就在一起吧。”
丑人爱文字是种必然,因为脸太难看,只有字见得了人。推而广之,丑人也可以藏在画布、镜头或者五线谱后面,画画的人比他的模特丑,拍片的比演片的丑,写歌的比唱歌的丑,这都不是偶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写字的、画画的人都是在死后才走红的,因为最妨碍他出名的脸没有了。更丑一些的,我们就不让他跟人,而是跟宇宙打交道,我所见过的人类历史中最丑的两个人,爱因斯坦和霍金,恰恰是最聪明的两个。最近一个证明我的判断的是《神探亨特张》,你用写字的人当演员,就只可能拍现实主义题材——为什么我们管意大利战后的很多片子叫现实主义?因为片里的人一个比一个难看。
按照才华跟长相成反比定律,难看的人弄出来的片子一般都还不错。直到二楼的阿姨突然伸出脑袋,主动捐款十万——写意地就跟捐款十块一样——之前,亨特张还挺有意思的。顺便,谁能把这阿姨的地址发给我,我现的工作15分钟才能挣五千,没脸见人。
导演的丑也不甘示弱,我觉得《帝国》应该搞个最丑导演TOP100的评选。为防被批肤浅,可美其名曰“展示大师们的另外一面”,再说说长相跟风格的关联。比如伍迪·艾伦,他是我最喜欢的导演没错,但也是丑得最放肆的一个,也许仅次于年轻时候的特里·吉列姆。伍迪曾在《傻瓜大闹科学城》里留过长发,就像《蓝精灵》里的格格巫,他们的鼻子也一样大,这是经过白人丑化的经典犹太奸商形象。即便伍迪的脸窄得跟红海似的,鼻子却如同喜马拉雅山一样纵贯其中。他戴眼镜就是为了让鼻子显得小些,有一次他去麦迪逊花园广场看尼克斯的比赛,林书豪晃过防守队员,三步上篮把球放到了伍迪的鼻孔里。
反倒是年纪大了以后,无论是伍迪还是特里看起来都比以前好多了,让特里变帅的是他的胡子,现在你知道为啥艺术家都爱留胡子了吧。马丁·西科塞斯是留胡子遮丑的代表人物,跟细长的伍迪不同,马丁整个人都是方的,尤其是他的脑袋。据说他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忘带三角板了,就用马丁的脑袋画直角。还有昆汀,我们之所以叫他怪才,主要是因为脸长得怪,那个遮天蔽日的大脑门跟外星人差不多,他的整张脸都是实验失败的结果,很有性变态的潜质,所以有人爆料说他喜欢****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惊讶。昆汀虽丑,却跟帅哥导演罗伯特·罗德里格兹厮混,不过你看看罗伯特的那些片子,《特工神童》四部曲什么的,就知道帅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人家泡到了罗丝·麦高恩。
往前数,最厉害的导演希区柯克算一个吧,他的脑袋就像是气球灌多了水,脸蛋子跟晾衣竿上的湿秋裤一样耷拉着,层层叠叠,让人想起沙皮狗。库布里克也靠胡子维系脸面,你应该去看看他年轻时候的一寸照,留了个中国干部式的一九分发型,一双死鱼眼。伯格曼可以成为相貌堂堂的导演,如果他始终笑不漏齿的话——他的牙不用任何特效处理就能在《指环王》里演个半兽人什么的,据说《生化危机》这款游戏就是以伯格曼的口腔为原型。
但是,现在的人什么都敢说,连自己床上那点事都能写成日记,就是没有人讨论丑。有美学,没有丑学,有选美,没有选丑,女人之间的客套话永远不会是“你穿这条裙子真是丑死了!”为什么人们敢于面对所有可怕的真相——有些虚无主义者会告诉你,无论你活着的时候做了什么,到头来一切都没有意义。就是没有人讨论丑,我们难道不应该敞开心扉,真诚交谈,告诉对方他有多丑吗?如果大家觉得当面说人家丑是不礼貌的,那就在背后说好了,但这也很少见。只在这一个问题上,人类做到了表里如一的虚伪。
就连弗洛伊德这种深入人类灵魂的大师,探讨了生死与性爱,就是不说丑。其实长相也是影响历史的一部分,为啥总有人闹革命、策划政变,因为想当老大。老大可以随便选女人,各地进贡,都是开封小姐、长安小姐的级别。剩下的都是歪瓜裂枣,大家就不乐意了。
你说有趣不,丑鬼喜欢的也是漂亮的人。那长得丑的人怎么办?他们研究天文地理、人文经济、历史哲学,他们用科技改变世界,做出没屁用的iPhone,他们孜孜不倦地创作,开创了印象派和蛋黄派,他们发明了“心灵美更重要”的雷人之论,他们做各种奇怪的事情吸引别人注意,奇怪的程度跟难看的程度成正比,比如用15秒变好魔方的理工男,难道你要靠这个找对象?负责这篇文的编辑老师每天上班都要在地铁里拿着Kindel看书,你以为他真的对《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1感兴趣吗,怎么会有正常人对罗兰·巴尔特感兴趣,怎么会有正常人知道罗兰·巴尔特是干吗的,知道巴特尔就不错了。
所以,丑鬼们都活得很累,做各种事情让别人忘记自己那张丑脸。只有男男女女都帅气美丽,这个世界才能变成美好的人间。想象一下,几十亿的皮特和朱莉聚在一块,全世界都变成了奥运村,除了fuck eacho ther,根本不会想到干别的。在那样的世界里,没有战争,因为没有仇恨;没有饥饿,因为愿意分享;也没有病痛和衰老,因为上帝看着他完美的造物,根本下不了狠手;更不会有一群丑鬼,闲着没事干,到处打听另一群丑鬼收红包的事儿。
本文不代表作者观点。
1.罗兰·巴尔特(1876—1928),著名的意大利恶棍,后移民美国纽约。原名罗德里格兹·保尔·柯察金·瓦西里里尼,绰号“独眼迈克”、“单耳鲍勃”、“口臭喀秋莎”、“龅牙思密达”,在大禁酒时期死于酒精中毒。他的传记《罗兰·巴尔特的最后日子》被改编为HBO热播剧《大西洋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