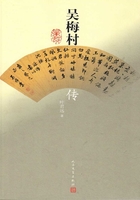有些事就是这样。中央提出一个东西,大家都说拥护,但是你并没有弄清楚就里。而反对的人反而很明晰,他们是有的放矢地在那里反对着的,于是,随大流拥护的人从而得到了启示,知道为什么要拥护啦。
此前出现过多么危言耸听的说法:除了作家煽动……之外,还有更大发的说法,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文联作协之类组织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某部某某局,某报某某部。其实真正靠得住的是三个代表。我从参考消息上读到,曾任哈佛大学亚洲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义教授在香港讲,有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质疑,目前,如果中共能够做到,一不断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二有条不紊地进行政治改革推动社会进步,三有效地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它的执政就是合法的。他用的语言当然与中共不同,然而其思路与三个代表思想一致。把作家说成主要危险的同行,显然不妥。
这是扩大开去,对于背景与有关话题的我的一些想法。下面回到九六年的五次作代会前后。一些告状者的穷斗不舍,使我积累了新的经验。无欲则刚,无私则平,无争则莫能与之争,无妒则莫能妒。我得到的已经太多太多,我不埋怨什么人。我的心情平和。
至于小贤弟们,自己慢慢消停了下来。人文精神失落了半天,现在也不像已经复归的样儿,也不见激愤的呼喊了。我早就说过,调子太高,一个是难以为继,一个是容易自我重复。祝他们有新的思考,新的作为,新的进展。
五次作代会后,察颜观色,感觉掂量,还是两便的好。我告诉作协同志,我已经年逾花甲,视力明显减退,(我后来还做过一次眼睛的小手术,太好了,我更有理由对某些活动请请假了。)写作未有穷期,我只参加作协的类似春节联欢之类的活动,外事则是参加有外宾提出要求要见王某的活动,只参加宴请,不参加会见。简单概括就是吃与玩的活动可以考虑,其他则请假,以求皆大欢喜,请他们谅解。
在老翟主持工作期间,在五次作代会结束后,我对所有主席团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都请了假。一次几位老作家在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暂住,老翟邀集座谈。我亦请假。
此次是谈艺术规律问题。李?说你们搞的什么什么评奖就不符合艺术规律嘛。陆文夫说,艺术规律是不能搞得太清的,搞不清的人还能写作的,一搞清楚了,再也写不出来了。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徐俊西说,艺术规律谈不清,倒不妨谈谈过去我们违反艺术规律的经验教训。
后来老翟抱怨我不出席该座谈会,我说,两便就好,如果加上我,也是那样谈意见,一定好吗?
其时我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同身份的人会说不同的话,最好的情况是做到和而不同。又和又同难以坚持,反而谁也念不好自己那份“经”。同而不和,如孔子说的“小人”们那样,是恶劣的,表面上亲如兄弟,实际上心怀鬼胎,一个个乌眼鸡似的。又不同又不和,则是危险的啦。
后来二零零零年,金炳华同志前来作协主持日常工作,有领导同志对我家访,要我支持老金。我稍稍改变了不参加作协正式会议的做法,前后五年,我参加过少量会议。其中翟金交接时的一次会议有个插曲。
针对一时有人认为解放后缺少大作家的说法,前后已经有领导同志引用周总理的话,说明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还有人列了一个名单,说明中国古代,几千年著名作家不过那么百十个,而解放后已经出现了著名作家某某某某某,一大批了。相信这是某个局处级单位为领导准备的名单,古代作家中提出了萨都剌,不像是领导同志自己列的。但这个比较法略显牵强,因为几千年淘洗后的留名著名,与现当下的留名著名没有可比性。不必妄自菲薄,我则是赞同的。至少,在文学问题上,是需要更长的时间考验与时间淘洗的,何必急着说东道西。责备一个当代诗人不是李白,一个当代小说家不是曹雪芹,或一个作家不是鲁迅,与责备一个英国作家不是莎士比亚,一个美国总统不是林肯,一个中国将军不是成吉思汗一样的不可思议。但同时,改善我们的人才生长环境,进一步学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能也不完全是多余。
后来在作协全委会上再一次谈起这个话题,宣读了一回一直延伸到当前来的作家名单,这回可有了事,一些曾在或正在作协担任工作的确系作家的同志未上名单,议论起来了。包括老翟,都很不平,怎么能够没有某某某呢?他是非常仗义的。
需要做一些弥补工作,于是由作协自身的领导出来说明,本来另有一张“纸头”的。后来讲话时临时没有找到……
列名单的事是最麻烦的,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切切不可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