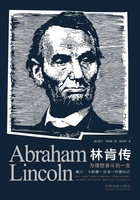如此这般,我的这些观点并无新奇,也非多么谬误,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弄清谈人文精神的来龙去脉。在我的心目中,左倾空谈主义的分量太重太重。而另一些文友,他们在看到警惕着左倾空谈主义的同时,他们在各地,包括在比北京要商业化得多的上海,他们感到了另一种类型的压迫,即拜金主义的压迫,物质主义的压迫,在改革开放开发的名义下巧取豪夺、多吃多占、把超经济的与经济的不公正结合起来的压迫。当然,这里同样有惹不起锅惹笊篱的问题,他们看不清或惹不起这些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前现代性权力掌控性的原因,却去大骂市场、拜金与通俗文艺去了。
我不能忘记那位定居香港的年轻学人,所谓新左派之一的人士甘阳先生的意见,他说,在美国,百姓真傻,精英真精。在中国,百姓不傻,精英真傻。天机不可泄露,此话咱们先撂到这儿。师傅领进门,理解在个人。
我还说到: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停滞与挫折,使左翼文人们集中批评资本主义的软腹部精神空虚、道德堕落、吸毒、卖淫、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等 。而强大的执政党、强大的人民政权、强有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似乎确实能够扫除或基本扫除或一度扫除人类面临的永无解除之日的精神危机。
这样的信息并非人人都能提供,也并非我们的文友我们的读者个个都明白的,相反,他们的青春“文革”背景,他们的一知半解的新趸入的理论,加上中国的社会环境,使他们特别容易倾向于新左派的高蹈。
我的单打一与我的轻率,朋友们的天真与自我良好感觉,使我们一下子碰撞了一个不亦乐乎。
这回我一下子得罪了一大批人,恰恰是我最看好、最欣赏、最喜爱的一批创作人与评论人。这就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供养作家问题我已经讨嫌一回了,斯事并未过去,如今又为人文精神问题得罪了那么多优秀的、有影响有威信的、自我感觉极佳的可畏的后生们,而且,直到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到了上海领奖与参加“面向新世纪的文学”的座谈会,我竟然对自己的失误与不妙处境浑然无觉。王某是够浑然的了。
上海又给我发奖了,我多高兴。获奖小说是《棋乡轶闻》,是一篇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胡扯淡”的小说。郭德纲式的信口开河中写了一个爱下象棋的省区,棋人后裔,即小说的主人公名胡聚旗,我写到了他的祖上三辈都因下棋与大形势的风云变幻而遭横祸。聚旗明白了以争输赢为核心的棋艺,应主大凶。他下死了决心再不下棋,结果为了小而又小的原因局长女儿的姿色与谁输谁喝凉水的规则,终于下得兴起,下得上火,下得投入,下棋下得进入了最佳境也是最险境界了,下得主人公再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字里行间,信手拈来,大故事里套着小故事,大幽默里套着小讽刺,大夸张大荒诞里套着小叹息。主题是啥,一句话说不清楚,但是含有一种哲理,关于放得下与放不下的悖论,关于超得过与超不过的两难,关于较真与洒脱的弯弯绕。人生就是这样,你一天活着,一天就摆脱不开入世与出世,无争与有争,计较与不计较,投入与撒手的麻烦之中。
有些作品我是拼命往荒诞里写,以至一些眼光短浅之人只看见了我的调侃与抡砍,直到封我为网络文学的始作俑者并断言“戏言是王某的唯一语言”。真令人喟然长叹,令人怆然泪下。如果你读过《青春万岁》,如果你读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如果你读过《蝴蝶》、《风筝飘带》、《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济南》、《春堤六桥》、《秋之雾》、《晚钟剑桥》、《靛蓝的耶稣》、《我又梦见了你》和一批新诗……
可你又怎么能埋怨读者读你的书读得太少呢?到处都是文学刊物,到处都是作家,全国有正部级的中国作家协会,每个省都有一个正厅局级的省作协。人民供养着那么多好作家,一级作家,特殊津贴获得者,写呀写呀写,歌呀歌呀歌,讴呀讴呀讴,有那么多人知道有个你,知道你会写幽默小说(其时广东原文化厅长唐瑜同志在文联主持工作,他一次邀我为他们的杂志写“肉末小说”,我大惊,后来才闹明白他的客家话“幽默小说”),你应该知足,应该感谢了。
而我原本是多情的,敏锐的,梦幻的,有时是偏激的,被长者爱护与深情地说成“神经末梢过于敏感”的……曾几何时?曾几何时?浅眼儿们只看得出王某的聪明与调侃,戏弄和豁达了。
其实我的荒诞含有不得已,我必须荒诞得使任何深文周纳者无迹可寻……除了胡扯还是胡扯,如马三立的名段子:逗你玩儿!再不让它发生稀粥事件或者宰牛事件。后一个事件本卷暂时从略。
我甚至觉得,马三立的逗你玩儿也有泪存焉。马三立五十年代居然闹成了右派,“文革”后他改正、入党,他很快被评成了天津的优秀党员,这叫啥呢?反正不叫“逗你玩儿”,反正只能算是“逗你玩儿”。
事物也有另一面,从无奈的荒诞,会发展成收不拢的荒诞,过分的荒诞,不无失控的荒诞。信手拈来成妙趣,随心舒卷含真谛,如我在一九七六年所填《满江红》一词中所写的。那么,我会沉醉于荒诞,玩荒诞而丧志???文章得失,端的是寸心难知也。
我高高兴兴地到上海开会,发言,与为养不养问题与我争论的陈村老贤弟握手言欢。公开争论而且真名字发出来的都是好人好友。例如山西的韩石山,至今宣称他在三个关键时期都批评过王蒙,这为他增添了光彩。我当然乐于作出这方面的微薄贡献。
然而我不识相,这也是标准的上海话。我的关于人文精神的文字已经激怒了不止一位上海的老中青精英,我还跑到上海来说什么保护作家呀,不要文化专制主义呀,不要极左呀……什么什么的。而一些文艺人,早已经对左呀右呀活活地烦死啦……如果你能够感觉到、理解到,并不会老有人对于周扬与丁玲争,或者夏衍、张光年与某某、某某某争论感兴趣,那么王蒙与某某争,人家就会更加不感兴趣。一位著名年轻一点的作家兄就说过,王蒙还是某某某当领导,能有什么原则区别?他的话一针见血,他的话能令“臣脑冷如冰”,他的话消除了多少自作多情,他的话让你静静地低下头来。我希望,我完全相信,他不会因为我写到了他的名言而介意。
还有一件蠢事,我在会议的发言中不点名地反驳了南京一位青年评论家的言论。我感到了他的矛头对准当代作家们,过于聪明啦,轻视散文啦,乱开玩笑啦(如说一位年轻女作家在会议上不发言,说是“我家先生说了,不要在人多的地方乱讲话……”),不像活鲁迅啦……
我相当反感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中烈士出得太少的各类暗示。左联五烈士,雨花台的枪声,郁达夫的被害,王实味掉了脑袋,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丁陈集团,成千上百的作家划成右派,“文革”中《红岩》作者之一的坠楼,傅雷的全家自杀,郭小川在黎明到来时死去……你为什么那样嗜血?你的记录何在?至少这些聪明的作家还留下过杜鹃泣血、以身殉文的记录,你呢?
鲁迅只有一个,废话,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与曹雪芹也都是只有一个,作家当然是不二的,能够克隆的作家一定不是好作家。鲁迅有鲁迅的伟大,我们有我们的环境与特点,让学习咱们就学习,向鲁迅致敬!而您用鲁迅、更不要说用诺贝尔奖了,压当代作家,岂不笑话?如果说人人可以成佛,人人可以成圣人,那么人人可以学习鲁迅。与其责备别人不像鲁迅,您先生自己就像一回嘛!鲁迅才活了五十挂零,不是说要等到花甲以后才能学习的。一个正当年四十多岁的人,责备六十多的人不像鲁迅,不有点找乐吗?
问题是日子有那么点安定了,肚子越来越吃得饱了,口袋有发凸的趋势,稿费版税看涨,教授与作家都有各种名目的奖金津贴称号职位,是的,平凡有可能取代高潮,日子有可能取代爆炸,轻喜剧与反讽有可能代替一部分指天画地,短信小品是不是正在取代一部分悲情的诗朗诵?于是从小已经习惯了大喊大叫与声泪俱下的朋友们愤青儿们愤中儿们失望了!
而且不仅在中国,美国的那位俄克拉荷马的炸市府大楼的愤青儿,也是激昂于美国人的堕落、世俗化,他怀念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冷战的高峰,中国的“文革”,全世界都在发疯,谁也做不到面向世俗,世俗化,日子化。这个愤青儿被美国政法机构招待了死刑。
中国总是这么绝门。查阅资料,外国讲人文精神,是讲脱离神学的钳制,承认世俗与人,而中国讲的是脱离物欲的引诱,走向伟大的理想精神,有时否定形而下,否定世俗与经济,甚至视世俗为罪恶。同样叫人文精神,外国强调的是人,人的而不是神的。我国强调的恰恰相反,我们强调的是原文中并不存在的文与精神,而不甚在意于人。绝了。刘心武说了一句“面向世俗”,就被视为背叛了知识分子的道统,我也说了两句世俗化的不可避免的话,也遭到了我所最最尊敬的一位长者学问家的反感,真是无地自容啊。同样的嘲笑媚俗,外国原文嘲笑的是装腔作势,是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矫情媚雅,如王小波与王蒙都著文谈过的,而到了中国,人们望(中)文生义地认为,要反对的是世俗性,是市场化与玩物丧志的日常化、非理想化、形而下化。天乎天乎!
对不起,我有这些想法,我并没有改变这些想法,但是我仍然后悔于我的轻忽,我本来应该更加理解,本来不应该有什么人比我更能理解青春的理想主义与愤懑心理,我本来应该更加理解所谓人文知识分子的求真理精神献身精神,我本来应该完全懂得中国一旦放开了市场经济,在解放了生产力的同时也“解放”出了多少罪恶与黑暗。我本来应该明白,人怎么生活便怎样思想,生活在外省的刚刚出炉的雄心勃勃的文艺文学青年一代,是怎样地对当今的文学当今的作家当今的小说诗歌不满意不过瘾,对电视剧、歌星、卡拉OK、咖啡馆等酸葡萄就更愤怒与轻蔑。本来,你也不是满意一切,包括同行,本来你可以跟着骂一骂,你也可以高尚一番决绝一番高屋建瓴一番,没有比骂文艺骂同行更安全更拔份儿更看好的了,旱涝保收,一本万利,零风险,高回报。我们的社会时兴集体表现自己的道德义愤,表现自己的神勇无畏与生猛,例如站在一个已经跪下的铁人前吐口水,证明自己绝不会做卖国贼。至少在口头上我们绝对不能在道德的制高点前退后……而你要为同行们说话!你算老几?你替谁说话?你在护着谁?你已经早就不是文化部长,不是中央委员,没有任何人觉得你能保护他们她们,你既没有慷慨就义,也没有东山再起,你不代表作家,作家不需要你的代表。
上海话就是说得好,你太不“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