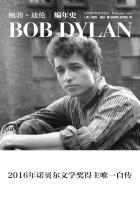还要怅卧,还要寥落,还要相望冷,独自归,还要飘灯,还要梦依稀……全是一个方向,一个平面,一个悲哀无望的模式!至于吗?当不成官,至于吗?爱妻死了,至于吗?男人啊,总要有点承当,有点骨头架子!
更不要说“先期寥落更愁人”“忍剪凌云一寸心”“羁泊欲穷年”……幸亏还有咏史诗与政治诗。史与政入诗,有助于开阔气象,那些但求遗老遗少风格,但求莫谈国事的小家子气的同行们不可不察。
然而,他写得又是这样的美丽。哪怕悲情像砒霜一样的剧毒,哪怕绝望像小儿麻痹病毒一样地传遍全身,在李商隐这里,在他的诗里,一切都审美化了,无害化了,去(毒害)功能化了。
美了也更哀婉更动人刺人迷人移人心绪了。我有点后悔,也许,九一年我本来不应该读那么多琢磨那么多李义山的诗的,本来没有李诗,我不会咀嚼那么多悲凉与颓丧。颓丧一词,出自《红楼梦》中贾政二老爷对于宝玉二爷的训斥。
消极情绪的审美化与少害无害化,是我在李义山诗歌讨论上提出的一个论点。我还提出了“无端”说。我认为执著于寻找诗的本事是侧重于诗的非诗化解读,是把诗变成时与史与事的注脚。李诗的特色恰在于抒情,有一类情的特色恰在于它的深刻性弥漫性自成性长远性,并非一时一事一史而来。曰悼亡,曰怀旧,曰感遇,曰思乡,曰冤屈,曰牢骚,曰痛惜,曰自恋,曰空虚……他什么情绪都有,什么原因都有,什么悲哀都有。大病无因,大情无端,大难无兆。大幸运与大晦气都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都不是一个掌故一个细节一个本事能够解释清楚的。唐诗特别是李诗专家刘学锴教授在他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一书中指出:“王蒙的‘无端’说,显示了在更高的层面上兼容众说的趋势。”
我希望的是不要忽略以诗心问诗,情心解情,文心通文。我们已经过于习惯于以治学心、史心、训诂心、考证心、侦探破案心来对待文学作品特别是诗作了。当然,以治学诸心诠解古典作品,也会长学问,长见地,破疑团,添知识,也会结出奇葩,放出异彩,如钱钟书的以触类旁通、美轮美奂的治学方法治诗(而非读诗吟诗赏诗),各种高见,各种常识,尽数大家气象,夺人耳目。只是不要反而忘记诗心情心文心就是了。
温州李诗专家黄世中教授撰文指出,王某的李商隐研究有六个方面的原创性观点,大概包括了爱情失意与政治失意内心体验同构说(诗可以是写失意的,但并非实指哪一事一时的失意,而是写一方面的失意,也带出了表达了甚至更巧妙地抒发了另几方面的失意。其实这个意思我早在六十年代谈鲁迅的散文诗《雪》的时候就讲过了)。混沌的心灵场说。政治诗增加分量与气象,李的政治抒情诗见识绝伦,清醒峻急,但急切有余而从容不足说。无题诗结构的无主线、无序非矢量说。尤其是关于对这些诗的解读的多层次包括字面的、背景与本事的、学问的、情绪与心灵的、触类旁通的等等说。也不还有什么什么,说是近年来我所讲的李诗之能受到重视与更高的评价反映了当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与提出了新挑战云云,也算新观点。黄教授并且说,有些观点已被权威的文学史家所采纳。
黄教授并且夸奖说,王的李商隐研究做到了什么历史与逻辑、宏观与微观、传统与当代、语言与意蕴什么什么的贯通,叫人偷偷高兴一场。
德高望重而又平易亲和的张中行老师著文说,王蒙以小说见长而评《锦瑟》,属于反串,他反串得不差。
这一段时间写得比较用功的是《雨在义山》,专门探讨李对于雨的描写处理特色。最带有顽童恶作剧色彩的是《锦瑟的野狐禅》,我竟然把《锦瑟》五十六个字打乱重组,出现了情调接近而结构不同的别样韵文作品。
其一:
锦瑟蝴蝶已惘然,无端珠玉成华弦。庄生追忆春心泪,望帝迷托晓梦烟。日有一弦生一柱,当时沧海五十年。月明可待蓝田暖,只是此情思杜鹃。
其二:
杜鹃、明月、蝴蝶,成无端惘然追忆。日暖蓝田晓梦,春心迷,沧海生烟玉。托此情,思锦瑟,可待庄生望帝。当时一弦一柱,五十弦,只是有珠泪,华年已。
其三,尽量使之成为对联风格:
此情无端,只是晓梦庄生望帝,月明日暖,生成玉烟珠泪,思一弦一柱已。
春心惘然,追忆当时蝴蝶锦瑟,沧海蓝田,可待有五十弦,托华年杜鹃迷。
冯宗璞读后心有不甘,声称要淘气一番。她把《锦瑟》五十六字重组成了“曲”的形式:
沧海月明
无端珠泪
悬
玉生烟
蓝田日暖
庄生梦迷
望帝心托
是蝴蝶还是杜鹃?
惘然一弦一柱
追忆锦瑟华年
可待
是五十弦
这里不仅有淘气,也有汉字的独立性、情绪与色彩性、可组合性、诗性,还有诗的语言性与超语言性。诗,可诗,非常诗。句,可句,非常句。无句,诗之始,有句,诗之母,易句,诗之诗。他年回忆,其乐何如?义山有知,罪我乎,笑我乎,感我乎?
一九九二年秋,我应邀到广西桂林附近的平乐县参加第一届李商隐研究会。李曾在这里短期做官。我被推选为李商隐研究会的名誉会长。
过了这个村,未必再有这个店,评红,谈李,翻译约翰契佛,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有点酸溜溜,有点书生气,有点雕虫之乐乐也无穷,有点从翻筋斗的变成了看戏的的轻松从容舒展……红、李、契佛这些事还让我欣喜地发现,王蒙仍然是王蒙,当了部长也罢,不当部长也罢,委员也罢,不委员也罢,出入中南海也罢,出入胡同市井村镇也罢,被称赞肯定也罢,被绝非善意地送上了“等身”的“材料”也罢,被赶车人罗织了一堆罪名也罢……咱们从来没有认生过文学,认生过生活,认生过平民,认生过书桌前的功夫!王蒙仍然能够规规矩矩地做活儿,兴会空前地读书,云蒸霞蔚地写作,一定之规地做人,其乐无穷,其味隽永,人莫予毒,别有天地。
王蒙最喜爱最天真地为之得意的一个词就叫做“活儿”。说到底,咱们也是个手艺人,是练活儿的,你得能拿出一手活儿来。拿不出活儿来,您靠边吧,您。练出活儿,比掌了大权发了大财受了大恩德都更高兴,因为咱们靠的不是运气,不是关系,不是背景,不是手段,而是手上的、手里出来的活儿!我间接听说,张艺谋的名言:咱们是卖力气吃饭的。张艺谋配说这句话。王某也当仁不让,能练心情善,有活儿道路宽!
我可瞧不起鲁迅所说的那种拿文学当敲门砖的人,以文学的名义混上一官半职,把文学祸祸了一个够,然后连一个沾文学味儿的词儿都说不出来了。呜呼,哀哉,嘛呀,您老!
按,“祸祸”一词,为我的家乡沧州南皮一带的人喜用、天津话中也有的一个生动的词儿。我小时候常听家人用这个词儿。后来用得少了。零六年听冯骥才说起此词,还给我讲了马三立的相声里的名句“你嫂子让人给祸祸了……”祸祸二字,不知这样写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