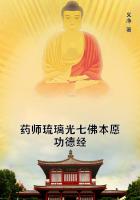又能怎么样呢?心事尽成灰也罢,匆匆归去悲也罢,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知止而后有定,想一想身前身后,祸福通蹇,也许人能稍稍踏实一点?
对夏衍、陈荒煤、冯牧、张光年、铁衣甫江、克里木霍加……我都写了专文追思。
摘胆囊后三年,终于实现了率友好代表团访日的愿望。我准备了在大型招待会上用日语发表演说的稿子。其实我小学期间学过日语,可惜我只学会了片假名,不会像草书的平假名。确实是由于民间的抗日心理,我们那些孩子没有谁愿意认真学习日语,到四五年日本一投降,孩子们都把日语书丢到了九霄云外,对日语是忘之犹恐不及。但毕竟有儿时的基础,我在文化部外联局日语专家老赖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终于可以讲出日语来了。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欢迎会上,我讲了话。我说到对日中文交协已故的领导人,中岛健藏、千山是野、东山魁夷、井上靖、团伊久磨等的怀念。我说今天的集会上他们好像仍然活在我们中间。
是电影演员栗原小卷主持的欢迎会,曾任议长的日本社会党领导人土井多贺子出席了欢迎会。
我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总部去的经验令人十分感动。一间大房间,就是此会的全部办公室。据说周扬曾经到过这里,开初,他还以为整个楼属于此会。他们的资深工作人员白土吾夫、佐藤淳子,横川健,都是真正的服务者,一切出头露面的事,全部依靠本会的文化界头面人物,一切风光与利益也是先文化人物,很少轮到自身。他们这样的群众团体里没有号称的服务者变成了官员,而号称的被服务者变成了下属的有趣现象。
对于日本作家水上勉的访问令人感动。水上勉刚刚做过手术,身体很弱。他坐着轮椅对我说:“真想再去一趟杭州,再游一次西湖啊,哪怕是坐着轮椅转一圈啊……”日本有些友好人士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的热情,催人泪下。
水上勉把他画的西湖风景给我看,他是天才的写家,也是画家。
他年轻时由于穷困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他人。他的儿子最后找到了他。他的儿子也是很好的作家。
他住的山头上有一个纪念馆,是纪念当年的一个艺术学校的学生的。二战中,学生们从军,差不多全送了命。纪念馆里有他们的照片和年龄,小的才十几岁。
二零零三年我访问了毛里求斯、南非、喀麦隆与突尼斯。缘由起于零一年喀麦隆的第三号人物、文化部长费迪南利奥波德奥约诺访华,他本人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在法国出版。我出面请他午餐,与他交谈文学。当晚是他回请中方东道主,由于是晚孙家正部长要陪中央领导同志去听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便要我代表他去出席“费部长”的宴请。其实我原来也打算去听演唱的,为了工作,只好放弃。两次活动,与费部长相识相谈甚欢,回国以后,费部长立即发来了邀请我偕夫人访问喀麦隆的信件。然后结合了其他国家,加上维吾尔族舞蹈艺术家阿依吐拉,我们以文化人士代表团的名义走访了一趟非洲。
非洲是多么可爱,毛里求斯是印度洋里的一颗名珠,到处都显出质朴与自然,大海与蓝天,白色的珊瑚礁受到国家的保护,现代化的旅馆里用的是茅草屋顶与原木建筑。时值当地的初春,我清晨下海游泳,水相当凉,同游的法语译员王杨游完了不停地吸抽着鼻孔,我连忙给了他一包维C银翘解毒药片。他与崔建飞从新加坡转机飞毛里求斯的时候,由于自认不懂英语,使他们失去了原来得到的宽敞的靠近飞机安全门的座位。我教给他,你不懂英语要什么紧,谁来跟你英格力士,你就跟他弗朗西呀,法语绝对不比英语少一点权威与国际化的气概。他学了就用,立竿见影。他背着一件乐器在巴黎转飞机,一个工作人员对他携带的物品表示有疑问,向他讲英语时,他的漂亮的法语竟然收获了肃然的敬意。而后一切顺利。
在南非,我们攀登好望角的灯塔时,注意到身前身后都是同胞游客,而在毛里求斯的维多利亚旅馆,也正碰到世界华商大会在那里召开。头几年,我看到在柏林墙那边留影的说的也都是大陆味道的普通话。我想起八零年首次访美时,台湾背景的诗人秦松曾经在晚餐会上幻想若干年后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中国游客的情景,曾几何时,早已成为事实。而秦诗人不幸于零七年春去世了。愿这个孩子一样天真的诗人安息。
去好望角的路上看到大洋里的鲸群,巨大,所以从容,平稳。令人惊喜赞叹。
南非的有色人种摆脱种族歧视还不久,与同行们的座谈,仍然洋溢着反帝反殖的热烈气氛。同时,可以分明地感到他们对于毛泽东的崇敬。他们甚至于事先私下询问我们,如果他们在谈话中表达对于毛的崇敬,我们是否能够接受。看来中国的事件,中国的改革,也并不是一句话能够向世界说清楚的。
一位参加过抵抗种族主义政权的老战士向我们朗诵他的诗作,大意是,你要面包吗/好的,这里有面包/你要喝水吗/好的,我帮你挖一口井/什么?你还要民主和平等/滚开,贱货/你面对的是枪口。这很令人震惊。
然而翻了身的南非社会治安极差。我早就听海外一位学者说过,说是曼德拉经过多年的囚禁,心灵完全升华了,他出狱后没有仇恨,只有慈爱。他主政后废除了死刑,但是社会秩序有了问题。我驻南非文化参赞车兆和嘱咐我们一行人注意看护好自己的财物,正说着,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公文包不见了,内有相机和一些财物。这一切发生在五星级大宾馆的餐厅里。
喀麦隆的黑非洲风貌实在难忘。它的河流如大水漫漫,几乎没有河岸,却有河马在波涛中出没。这里有更多的大自然,更多的纯朴。我吃到了菜蕉(一种作主食用的无甜味香蕉)、木薯等食品,我与一些部落的王室人员会见。他们穿着宽大的长袍,仪态威严。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国两制,却不知道如喀麦隆这样的一国数制。它是共和国,但对原来的各部落王室不采取取缔消灭的态度,而是取消其行政权力,承认其作为民俗的特殊身份。一切礼仪,一仍其旧,但已不管社会政治事务,有点像当年辛亥革命后头几年溥仪的处境。
至于白色的突尼斯,本是欧洲人的度假圣地。什么迦太基呀,什么罗马帝国呀,到处都是历史。
最最可爱是非洲,我写过一系列文字。我写过她的野马奔腾的河流,她的蓝灰色的鲸鱼、水中的犀牛与河马、陆上的大象与驼鸟……美丽强壮的非洲男人与女人。每个人都是一尊雕像。每个角落都是一幅油画。我相信上帝是护佑非洲的。
带着游戏的友好的孩子气的心情到处讲当地语言,也算我的一项乐趣,除在日本讲了日语外,我还在二零零四年在莫斯科讲了俄语,在阿拉木图讲了哈萨克语,加上几句维吾尔语,而且是俚语,全场轰动。我曾在一九八八年对土耳其进行官方访问时用土耳其语祝酒。而二零零六年在德黑兰伊朗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的欢迎会上我讲了七分钟波斯语。讲得最好的还是哈萨克语,我国的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帮我起草了哈语讲稿,我在伊犁期间也没有少与哈族同胞接触,加上维吾尔语与哈萨克语的“亲戚”关系,我讲得得心应手。波斯文里的词汇有许多与维吾尔语相同相通,其小舌音与卷舌音也与维吾尔语相仿,我没有少费劲,最后讲的效果还不错。
后来,李肇星部长也说,出去讲英语法语不稀奇,能到伊朗讲波斯文,就不容易了。
我有一些小趣味,有对雕虫小技的爱好与沉迷,我认为这是我的可爱之处,是我对于“异化”与“VIP化”的抗御。读者你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