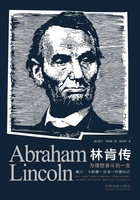有趣,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而又什么都没有透露的词儿。英美人,当他对你的讲演、主张、作品不想作什么评论,并非那么感兴趣,却又要表现出礼貌与友好来的时候,他就会说:“Very intresting很有趣。”
就在“吾兄”(白话文就是我大哥)的一些人提高了批王的分贝以后,似乎头一项效果是一些大学加快了聘请王某做他们的教授、兼职教授、名誉教授、名誉院长的步伐。有的就是针对吾兄的那些动作的,如《……其人其事》的发表,使得南京大学立即决定聘王。但当时我不能及时去宁,结果我得到的头一个名誉教授的头衔来自解放军艺术学院。是我们的“最可爱的人”的艺术学院。这期间,我数次到军艺讲课,讲过小说创作,也讲过《红楼梦》。
此后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南大学、鲁东师范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温州大学可能还有别的高等学校,都聘请我担任了他们的教授,有的加上了文学院名誉院长,有的是学校顾问或高级顾问。我还担任了国家图书馆顾问、上海东方讲坛顾问。此外去讲过课的就更多,包括国防大学、装甲兵学院、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邮电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我被聘为他们的诗学中心顾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大学、延安大学、社会主义学院、鲁迅文学院、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上海图书馆、上海东方讲坛、南京图书馆、光明讲坛、宁波讲坛、现代文学馆、301医院研究生班、青年政治学院、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香港作家联合会、香港作家协会、香港图书馆、澳门基金会、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
这个发展确实“有趣”。
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不是隐士,不是酒仙,不是所谓闲云野鹤,不是甘于寂寞的小草或者沙砾或者泥巴,不是一个完全省油的灯。我不会长期让那些不学无术、装腔作势、拉帮结派、与人为恶的猛人们太如入无人之境的。同时我又绝对不是一个钻营者,一个官迷或者级别迷,或者一个市侩。很简单,如果中国的市侩能急流勇退辞官不受,如果中国的市侩能坚守自己的做人的底线而不惜付出代价,如果中国的市侩能研究李商隐与《红楼梦》,如果中国的市侩能够写诗写小说写《夜的眼》与《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写《活动变人形》与《青狐》,如果中国的市侩能够讲遍国内外境内外大学研究院,不仅用中文而且用别的文,中国就一定是最清高最伟大最神奇最有智商最有激情的赛过柏拉图与黑格尔的设想的理想国了!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学术讲演已经逐渐成为我的生活的又一个组成部分,每年都要讲个十几二十次(不包括境外),除大学外近年各级党委宣传部门与政府部门也很注意组织人文讲座。演讲的内容也在逐年开拓新“产品”。这些年我讲得较多的有“文学的悖论”、“文学的挑战与和解”、“小说的可能性”、“语言的功能与陷阱”、“《红楼梦》中的政治”、“《红楼梦》的文化情怀”、“放谈《红楼梦》诸公案”、“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华文化”、“门外谈诗”、“说无端(讲李商隐的无题诗)”、“当代文学语言的资源”、“中华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关于大国风度”等。
我越来越多地对每次讲演作好准备,包括幻灯投影教学片。但是我的习惯仍然是即席发挥,同一个题目,但每次讲的和过去都有不同。讲话和写文章感觉不太一样,有更多的直接交流,听众的每一个表情、声息、动作都直接地感染着与启发着我,激励引导或制约着我的话语。我始终感觉得到与受众是息息相通、亲密关系、及时交流、立即反应,哪一点讲得成功,哪一点讲得生涩,哪一点不妨乘胜拓展,扩大战果,哪一点需要即刻换一个说法,以免人家听不明白对我都起作用。写作的过程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当然,我写过一篇文章:“作家是用笔思考的”,讲话的过程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你边说边寻觅,边整理边发挥,边造句边反问,边注意反应边调整,一个问题你讲过三遍,就比只讲一次的时候体会深刻得多,再讲十遍,你自己也被自己说服了,感动了,觉得一个思想,一种论说,一番道理正在往完美方面发展。
最初,我一讲话就沾点激动,讲到近两个小时,心跳有点加速。慢慢我也练出来了,掌握好节奏,调整好呼吸,一泻千里中有停顿也有反刍,有充电也有瞬间的节能保护待机“睡眠”。如此,讲话便不成为伤气耗神的单纯消耗,而是变成一项有氧运动,讲两个小时,出点汗,脉搏趋于有力,能消化食物,排除废料,心情愉快,也如跳了三十分钟绳或游了七百米泳。
最早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讲演集《王蒙说》,然后是上海连续出版了我的《王蒙讲稿》、《王蒙新世纪讲稿》。我收到过读者反映,说是愿意看讲稿,因为讲稿通俗,好接受。
当然不是全部根据,但至少占有一小部分,《中流》、《文艺理论与批评》上的那些批王文字,促进了我在高校的影响,帮助我获得了太多的教授头衔。
我更重视的是二零零四年,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委员会授给我的荣誉博士头衔。在莫斯科,举行了正规的仪式给我授学衔。年轻时候我一直为自己没有受高等正规教育而遗憾,后来(六十年代)我到高等学校执教,而如今我也忝列教授与博士之列了,我得到了相当的安慰。
也是此年,夏天我应邀到荷兰莱顿大学讲演,我国驻荷兰女大使与该校校长参加了我的演讲会,并在会后举行了招待会。此次的荷兰行我与芳还有助手崔建飞先生顺便参加了女儿王伊欢在瓦格宁根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在一个德国、一个美国、一个墨西哥和两个本地的教授的主持下,她获得了成功,得到了博士学位。她的先生和七岁儿子也自费前来参加这一盛典。没有穿博士服装,使我的外孙刘铜河有些失望。但开始时有号角吹奏,和举校旗入场的仪式,差强人意。此前我的弟弟王知,不久前从民航局计划司长的职务上退下来,和他的孩子们正计划前来欧洲旅行,说是也要参加伊欢的博士化手续,我开玩笑说,要不咱们干脆包一架飞机来吧,让欧洲人看看现在中国的发展和实力!虽然只是说笑话,也反映了那么多沧桑、感慨和欣慰!
在答辩委员会主任宣布伊欢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我想起了父亲,他一辈子那么向往欧洲,向往学位,尤其向往欧洲的学位,他的在天之灵应该会怎样地为伊欢而高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