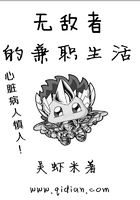李世荣被女人的猝死击倒在了炕上,根明根亮傻了眼只知哀号流泪,家里缺少主事的人。众人见此,推举高全德来主持根亮妈的丧事。高全德安排两人看定李世荣,防止李世荣想不通去寻短见,一面安排人分头去请安阴阳、请娘舅以及置办丧葬用品。安阴阳听到消息后,皱了皱眉头。说声:“天要命是不能成着,人又何必自寻死路呢!”言罢,收拾了家当,跟着去请的人来了。去请娘舅的人话刚说完,根亮的两个舅舅立马吊下脸。发起了脾气,破口大骂起来。去请的人脸上挂不住,只一味地说我们是跑路的,不关我们的事,你要骂到李世荣家骂去。娘舅听后仍喋喋不休地骂着。
根亮妈的坟冢安先生勘定在了喇嘛梁顶的一块根亮家的自留地里。全村人停下了春耕的所有田间作业,打坟的打坟,跟集的跟集,跑零碎的跑零碎,在安先生定的出殡的日子到来时一切事情准备就绪,只等出殡送葬了。根亮妈的安葬日期定在了本月初九。李世荣在乡亲抬起女人的灵柩起身时,抚棺大恸,哭着不许乡亲抬走。几个年迈的乡邻好言上前劝慰李世荣,李世荣犹然不听,哀叫着女人,爬在棺盖上哭得泪人一般。李世荣后经乡邻解劝拉扯,哭叫着被搀扶到屋里去了。正当起身炮连放了三响,乡老抱着引魂鸡鸣锣走出院门,将要朝墓地行进时,请后一直没有露面的两个娘舅突然哭喊着“姐呀!你死得冤枉”,跪在当路。拦住了去路。无论高全德等乡里头面人物怎样劝说,娘舅就是不让开道路,沉着脸非要把姐的冤伸了再走。高全德等乡里头面人物许愿保证,并好言劝慰了好长时间,都没有结果。这时,安先生闻讯走了过来,安先生冷眼不动声色地用目光逼视着跪在灵柩前面的两个娘舅,一句话也不说。安先生是附近人尊人敬的神灵。在安先生声色俱厉的威严目光下,两个娘舅不自觉矮了一截,先还理直气壮的口气,变得嗫嚅结巴了。这时,安先生才淡淡地说:“让死者入土为安吧!莫要耽搁了时辰!”两个娘舅听完连忙抹把泪,站起来,退在一边,用哀伤、愤怒的目光看着送葬的队伍过去。送葬的队伍过去后,一个娘舅用手暗暗拽了一把另一个娘舅,另一个会意,走在那一位娘舅的后面,朝着坟地,绕着山道,攀缓而去。
送葬回来,安先生草草收拾了行装,不顾庄里人留劝吃饭,看了眼黑着脸坐在一边的娘舅走了。两个娘舅一回来,高声大嗓地嚷喊着要惩治逼死母亲的不孝子孙根亮。庄亲纷纷劝抚,说闹得够乱的了,你们就不要再添乱了。两个娘舅变了脸,说你们庄里出了这种事,你们还迁就;假若这事遇到你的头上,你咋做?我没有他那样的外甥,他也没我这样的舅舅,翻脸就翻脸,不给逼死的姐姐出口气,自己就不走。庄亲拿娘舅没有办法,回头目光征询李世荣意见。李世荣瘫成了一堆,瑟缩着蜷偎在炕角,只顾流泪,木头人一般,不言不语。庄亲和娘舅争辩了好几个时辰,都无法让对方屈服,末了,年长的一位娘舅气忿忿扭头出了院门,过了一锅烟的时分,复又转来。这次,娘舅搀扶着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老人须发皆白,后脑勺留着个满头,梳理得光滑净亮。老人脸上肌肤疏皮松垮,但面色白净,额头浮有紫斑,一双眼睛,眼睑低垂,下眶翻突出来。形同红色的瓜瓤,阳光下水光莹莹。那老人身穿饰有万字花纹黑绸宽袖对襟,足蹬方口条绒平底便鞋;瘦若鸡爪的手握拄着一根褐色龙头拐杖。众人认识这位老人。众人见老人走了进来,齐闭了嘴站着看。大娘舅请来的正是族里尊寿双全的李世荣的三太爷。三太爷弓着背、颠着遽趋的步履,一进门,就呻唤着连呼:“世荣——世荣——世荣啦!”众人见三太爷走来,纷纷刹住话,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请三太爷到屋里去。三太爷进到屋里,李世荣方才意识到三太爷来了。李世荣惊慌失措地溜下炕,垂手站在三太爷面前,神情甚是颓唐。三太爷看了一眼泪流盈腮的李世荣,蹙了蹙额,一句宽慰的话不说,却大失所望地责备道:“你看看,你看看,从我的话上来了么没有?给你当初怎样说的?——你当耳边风!现在好了,闹得逼死了生母这下你该舒服了!冤愆啊!冤愆啊……”三太爷头摇得风铃一般,一条拐拐棍不住地敲打着李世荣脚前的地面。李世荣大气不敢出,任凭三太爷数落,泪水雨一样洒。三太爷将李世荣数落了一阵后,说:“到死人的地步了,你还护他,不让教训,难道非得到杀人放火变为强盗,朝廷株连九族时才知悔吗?”三太爷用目光刺了李世荣一下,突然愤慨得全身战栗,大声吼道:“小畜生哪里去了?”李世荣一脸茫然,周围站着的人忙替李世荣答道:“在香桌前跪着呢!”
“给我绑在屋檐上!”三太爷目眦尽裂。
众人知道三太爷要动用祖规典章了,一听三太爷的呼喊,抢上前将根亮用绳子反剪着绑束在了李世荣上房的屋檐上。吊挂着的根亮像颗粽子。三太爷率领全族人众香桌前给祖先重新上了炷香。跪拜祭奠已毕,三太爷当院一张竹椅上威严地坐了,两个娘舅威仪地站在后面。满脸激动。三太爷的大儿子——一位和三太爷年纪仿佛,齿牙松动的老者——虔诚地从神龛中拿出族谱,抖抖索索翻到祖规律典部分。熟悉地遴选着相关的祖规,念道:
第八规十九款:桀骜不驯,恶习流患乡里者,杖笞二十,训诫之;
第八规廿八款:不赡养双亲者,族人唾训之,杖笞三十;
第九规十款:不孝,丧人伦者,割一耳,杖笞五十;
第九规十六款:虐杀至亲,失秉性者,革其姓,割一耳,杖笞一百,逐之:
第十规第七款:杀人放火,为非作歹,淫匪为盗,身负人命官司者,革其姓,游其街,报之官,听官裁处;
按照八百年前的族谱规定,根亮应割掉双耳受一百杖笞,然后除消李氏姓名,逐出村子,或者报官处理。三太爷坚持执行祖法。族人议论纷纷,认为如此处理有些过分,会给悲痛不堪的李世荣更重的打击,并说社会到现在了,就不要割耳了,至于报官,就更加不必,咱们能处理多少处理多少,别打浆子把事情弄黏,再说好歹根亮也是自家子弟。三太爷在族人的请求央告下,不再坚持割耳报官了,但他执意要革除李根亮的姓氏,并要将其逐出村子,说若不把这个祸根贼胎清除出本门,逐到外面去,一旦野性狂放,不知要闯下什么祸来,到那时,全村不得安宁不说,株连全族的罪愆可是要掉头的。众人再劝三太爷,统统遭了三太爷的斥训。不敢再说什么,任凭三太爷处理安排。
三太爷觉得规矩不能废。不成规矩,无以成方圆,也是为后代子孙起见。若饶恕了根亮一人,会弃了祖先的心意,后辈儿孙前树立了坏榜样。如果争相效仿,一族人就没有了希望。今日惩治根亮一人,能给日渐惫懒狂荡的子孙讲个样子,不使后辈儿孙走上歧途,牺牲一人也不为过。三太爷有了如此的想法后,更加坚定了心意,觉得肩上担着千钧重任。他谢绝了众人的圆当请求,派人叫来木瓜面各家各户的年轻子女,一溜烟排站在周围,然后,找来两条皮鞭,挨次派人抽打屋檐上悬着的根亮。屋檐上悬着的根亮双目紧闭,他在回忆着母亲的生前事迹。母亲生前对自己的恩义使准备在三太爷毒打时硬充好汉的根亮泪水簌簌洒落。情绪哀凄,深陷在追悔的意识中不能自拔。皮鞭在眼前飞舞着。根亮浑然不觉得疼痛,许是吊挂得麻木了,而更为恰切的原因是他内心的疼痛已经超过了肌肤的疼痛,使他超越于皮鞭毒打之外了。他觉得即使一死也无法洗尽罪愆,他为自己的过失致使母亲心灰意冷地离开了自己感到懊悔,他在默默地忏悔着,这种心灵深处的忏悔使他泪水交流,浑身瑟抖。
其实,在皮鞭的抽打中,每抽一鞭,根亮的身体就得一次寒战似的战栗,几十鞭后,随着鞭梢的起落,根亮的喉咙相应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呻吟。这声声惨叫使围观的人众生汗直流,心惊肉跳,似乎每一皮鞭同时也抽到了自己的身上,众人纷纷捂起了双眼,一百皮鞭过后,根亮浑身皮开肉绽,鲜血染红了衣衫,神志模糊不清,软兮兮似卸了骨架的一条刮了鳞甲的鱼。痛打之后,三太爷慷慨激昂地宣布:“从今之后。根亮革除李姓,不再是本村子民,并逐出村子,永远不许回来。”宣布完毕,三太爷鸡爪似的枯手一挥,四条壮汉如狼似虎般扑上前,架起根亮。朝村外快速拖去。侧面站着的以泪洗面的李世荣一见此景,一口痰涌上来卡在喉头,双腿一软,再次昏厥过去。根明顾不得父亲,哭号着从院门里追出去,撵兄弟去了。高全德一直觉得三太爷做得过火,但碍于李氏家族内的事,不好插手,故一直冷着眼站在一旁静观,今见三太爷除了根亮姓氏,根亮被逐出了村子,李世荣又昏过去,终于沉不住气,上前劝三太爷道:“三爷,做事莫要触犯国家政策!”三太爷不满意地盯着高全德看了一会,鼻孔里“嗤”一声,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懂不懂?”三太爷说完,不屑地摇着头,慢条斯理地在两个孙子的搀扶下回了。高全德在家族势力庞大的三太爷面前不敢做大,目送三太爷出去后,唤来了儿子怀文,耳畔低语了几句。怀文听后,放开脚步跑了。
四条大汉将血肉模糊的根亮架出村子,丢在了村子对面的沟底小道上,然后,扬长去了。追赶前来的根明抱住奄奄一息的根亮。放声大哭。悲恸的哀声使神志模糊的根亮清醒过来。根亮感到浑身剔骨一样疼,他强忍着酸疼爬起来,准备安慰哥哥,不料未语泪先下来。愁不能言,兄弟俩瘫坐在尘头,抱头悲号连天。这时,在父亲的嘱咐下。怀文赶了前来,他劝解住放声痛哭的根明根亮,说:“热天伤口容易感染。到我舅舅家去给你用药洗洗。”根亮想起是因怀文妈制造的诸多矛盾,致使他前来不得后去,不孝不忠,遗留骂名,便把心中的怒火迁到怀文身上,骂怀文少假惺惺,自己即使死,也不要别人怜悯,你妈把我家搅成了这样,你还来领人情。怀文知道根亮心中有气,不想解释,上前来背根亮。根明见故也来帮扶。根亮欲要反抗,怎奈浑身乏力,一堆泥一样软。怀文背着根亮,委蛇上山路,来到他舅舅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