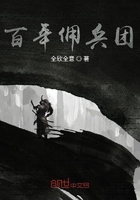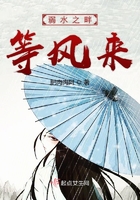欧阳妙弋捧起他的脸,替他轻轻揩去额头的血,既心疼,又是责备:“傻小子,为什么这么待自己,你不知道有个我,会比你更疼吗,你疼的是肉,我疼的是心!”
傅夕歌渐渐恢复了平静,用手把妙弋的手包在手心:“妙弋,我们要出去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如若可以,我打算一辈子不出此谷,永远和你厮守在一起,相伴到老,白头雪发,看那黄昏夕阳。”欧阳妙弋流下了泪,她明白心中的念想,是如何的虚无飘渺。
傅夕歌心中那份感动自然是刻骨铭心的,他暂时忘记了刚才的心痛,把这世间绝美的女子拥入怀中,看着她那沾满泪水的脸庞,犹如那美玉沾露般晶莹,他心中那千仇万恨一瞬间荡然无存,只有心爱女孩那温柔的爱,把他紧紧包围着。
要走了,要一起面对未来的风风雨雨冰刀雪剑了。
亲爱的,就让我们忘情一吻吧,吻去你那眼角的泪花,吻去你那心间的伤痕,吻去彼此的隔阂和疑惑,让这一吻,定下我们终生不变的情誓吧。
那少女和那少年,紧紧拥吻在了一起……
最后看了一眼这谷底的所有景致,那深潭,那小溪和那石洞矮树。
傅夕歌手拥着欧阳妙弋和青木棒子,肩头趴着那只叫闪电的豹子,豹子口里叼着丐帮圣物打狗棒。
傅夕歌仰头望着这插入云霄的绝壁,问怀中的人儿:“妙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这一去,将生死难料,前途莫测。”
“嗯,就算是去送死,我也陪在你身边,世间的任何苦痛,也阻挡不了我和你。”妙弋依在他宽广的怀里。
傅夕歌深提了一口气,尝试着用张无忌传授的心诀,把真气在周身运转了两遍,待畅通无阻之时,真气一聚,整个顿如出弦利箭,携着那一人一豹,贴着绝壁,飞身而去,一时间地心引力对他们已无作用,随着体内源源真气的摧动,他们如那身轻无比的的燕子,一步千里,拔云直上九霄,两人身轻如燕,穿过倒挂于崖间的青松和飘浮在壁侧的薄云,半刻不到,便已飞身腾上那崖顶。
登顶之时,眼见豁然开朗,清风徐徐细雨飞飞,人间烟火,瞬间让两人的心胸似回归到了家乡一般。
脚才踏地,欧阳妙弋不由得纤臂一舒,在前面狂奔了起来:“啊,人间,我欧阳妙弋又回来了,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我的傻小子。”
她这活蹦乱跳的样子,引得身旁走过的游人纷纷侧目,感到像遇到奇怪的人般,更奇怪的是那后面走着的年轻男子,肩膀上扛着一只大豹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不奇怪就是惊悚了。
傅夕歌因身上多了一股强劲的内力,走路顿觉轻松愉快毫无累感,拿着那二百余斤的木棒和肩扛那三百余斤的豹子,却若无物般,轻松得很;妙弋却没有那么厉害了,但见她小跑一下子,已累出了细汗,等着傅夕歌走近,叉着腰在那里喘气,鼻头香汗津津,一脸娇气,撅着嘴唇问傅夕歌:“傻小子,你家妙弋走不动路了,怎么办啊。”
傅夕歌指了指肩膀上的豹子:“像它一样,坐我肩膀。”
“那不行,你不是我的青龙,我才舍不得骑你呢。”欧阳妙弋迈着碎步后退走着,手却拉着傅夕歌的手臂,傅夕歌伸手替她揩去鼻子尖上的汗珠:“没事的,就把我当成你的青龙吧。”他用眼神示意她爬上自己肩头。
妙弋听得心中暖洋洋的,但是她还是舍不得骑在自己心爱人的身上,突然,她眼睛一亮,瞄着傅夕歌肩头打盹的豹子,坏笑开了:“你瞧它那享受的样子,凭什么?不如让它下来,我把它当我的青龙马儿可好。”
“你想骑豹子?”傅夕歌哭笑不得,这么奇葩的想法,只有她才想得出来我。
欧阳妙弋兴高采烈:“当然啊,早就想骑了。”她开心得快要跳起来,像是真正骑到豹子身上了似的。
傅夕歌肩头的豹子,顿时无了睡意,它一脸鄙视加憎恶的表情对着欧阳妙弋,脸孔上写着三个字:“想得美”。
有这么一对活宝陪在身边,傅夕歌的生活想不精彩都难。
二人出了那绝谷,见时逢深秋,来秦岭游玩的游客比肩接踵,络愈不绝,他们也不想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招摇过市,故寻了个茶肆,要了些填肚子的吃食,正准备吃喝一番,却不知如何围过来一群人,把而人围在那茶馆里面,两人抬目扫了扫,但见这些人个个粗布破衣蓬头垢面,手拿竹棍,全是那丐帮中人。
一个中年乞丐直步走到二人桌前,眼睛死死盯着他们桌子下面趴着的豹子,豹子口中叼着他们的圣物打狗棒,在那桌下养神。
傅夕歌放下筷子,看看桌子面前的中年乞丐,笑问:“你好,有事吗?”
“我认识你。”那人的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盯着傅夕歌的脸,尔后又看了一眼欧阳妙弋,说:“敝帮大会上你二人可是大出了风头,害得敝帮圣物丢失,到现在还没立出帮主来!没想到二位盗走了敝帮打狗棒竟还敢在我秦岭分舵地盘上大摇大摆的吃喝,在下佩服。”
“如何不能吃喝了,难道你们秦岭还不允许别人吃东西?”傅夕歌倒不理会他话的意思,只是顾左右而言他,那欧阳妙弋却嚼着一块牛肉,含糊不清地指着那桌下豹子嘴里的打狗棒问那人:“你说的圣物,就是它么?”
那人冷笑道;“姑娘不必在在下面前装疯卖傻。”
“如果是,那就拿去呗。”欧阳妙弋倒很大方似,她弯腰一拍那豹子的脑袋,只见豹子抬起头莫名其妙的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傅夕歌,突然伸了个懒腰,从桌下起身钻了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竟嗖地一声跃上了十几余尺高的棚梁,随后迅速蹿上屋顶,跳到棚外的树桠上,外面是一片相连着的树林,那豹子黄影一闪钻进林地,消失不见了。
见豹子一下溜得没了踪影,傅夕歌哭笑不得:“人家来要东西还了便是,这下倒好,打狗棒没了,豹子也溜了,打发不了人了。”他一脸无辜。
那丐帮分舵的领头人显然不相信傅夕歌二人会还打狗棒,怒到:“少跟我在这里唱戏,跑得了豹子跑不了人,两位还是跟在下回丐帮解释解释一下吧。”
傅夕歌冷笑:“看来阁下是想强请了?”
“你们夺走我丐帮圣物时既然是那般嚣张,我今天强请一次又何妨?来人,祭打狗阵。”
“打狗阵是什么东西?”傅夕歌皱眉问欧阳妙弋。
妙弋想了一下,眨眼回他:“打狗阵不是东西,是他们乞丐去讨饭如果人家不给,便要结伙强夺。”
“要饭都要得这么嚣张?”傅夕歌提声说。
妙弋嘻嘻笑着:“谁有你傅夕歌嚣张啊,万人大典独身闯,傲视无用乞丐帮,飞鸢捻走圣物去,羡杀人间少年郎。”
他俩你一言我一句在那打情骂俏,气的那桌前的叫化子脸都绿了,他被华丽丽的无视了,他一时老羞成怒,吼道:“出阵。”随着那乞丐的怒喝声响过,四周的乞丐应声而动,他们手中棍子一齐在地板上发力狂捶起来,击起了阵阵黄烟,众丐一下子把此茶肆围了个水泄不通,口中念念有词,脚步哗哗踏着,却是愈压愈紧,全全朝傅夕歌与妙弋包饺子般包了过去,看起来似乎一只苍蝇都难飞出去。
一下子如黑云压顶,杀气腾腾而来。
傅夕歌微笑着站起身来,右手拿起青木棒子,叫上欧阳妙弋,一脸无谓大步流星走出茶肆,迎那围来的乞丐喝道:“尔等是要以多欺少么?”
那围着他们摆阵的丐帮人士,你来我往,犬牙交错,攻守皆备,棒风呼呼,已把这围得像铜墙铁壁也似。
募然之间傅夕歌两足轻点,在众人面前长身一提,飞身腾入空中,众丐一声惊呼,眼睁睁的看着二人身影急急拔高,几刻间已飞出去十几丈远,一时望尘莫及,众丐打狗阵乱做一团,他们没想到防住了地面却没堵住天空,让傅夕歌那小子抓了个空隙,堂而皇之的逃身而去。
又如那日在万人大会上,他又嚣张的飘身而去,空留所有人在原地长叹。
“蓬”地一声凌空炸响,那堂主手中的响箭在空中盛开出了绚丽的花朵,花朵是一个信号,只有丐帮人士明白,这是全帮上下的规定,一旦发现圣物打狗棒的踪迹,便无论是谁,必须以响箭报信,以变好引众附近帮众前来驰援,一起夺回打狗棒。
秋风瑟瑟,红叶翻飞,深秋之中,一架马车由北往南,匆匆驰去,在那官道之上卷起了一阵飞扬的黄尘,眼看天欲近黑,赶马车的中年汉子把皮鞭挥得呼拉拉直响,想尽早把马车里的客人送到三十里以外的城镇,因前面有座叫鬼见愁的山口,山上强人盗贼颇多,若夜过此山定凶多吉少,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在天黑之前翻过山口为妙。
此处已是成都境内,乃富庶之地,位于神州之西南,面积宽广人口众多,川北剑门关有如一道天然屏障,将那北方强人拒之秦岭以外,自古欲进成都必经剑门关,过得剑门关才能踏足天府大地,而这剑门关又锯二山悬崖中间,地势险要之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为川北的一重要门户。
剑门关脚下方圆百里荒无人烟,唯有这条官道孤独的延伸进了那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若是有行此路常识者,断不会在快黑之时有这条路的,因为此路的茂林间藏着一个神秘组织,专干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们手段毒辣,在此道上令人闻风丧胆,不欲敢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