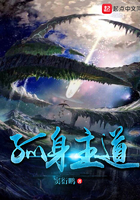老高和杜老头从外边进来:“三位小伙子都是有识之士,我们有事相讨,还望见谅。”我听完这恶心人的话,都不知道该怎么接好,我说欢迎吧,张不开嘴,我说不欢迎吧,我也不能把你们俩哄走。
“今日晚饭时候,多有得罪,还望路先生见谅。得知老高已经把日记的事给路先生讲过了,杜某人就不再赘述,实不相瞒,我今日来就是向路先生请教日记中的字。”
“拿来吧。”路直连个“不敢不敢,哪里哪里”之类的词都没说直接伸手要了。
杜老头从怀里拿出几页纸来交在路直手里,路直接过来,看着那些字眨了眨眼睛,先是把那几页纸大概看了一下,然后重新排了顺序。显然杜老头的这几页日记不是按顺序给他的,有可能是故意考他一下,也有可能是看来看去看乱了,随手一放。但是我感觉试探路直的可能性比较大。
路直看了半天没说话,老高有点忍不住了,咳了一声问:“小路,这个是锡伯文么?”
我伸过脖子看了一眼,感觉像是把维吾尔族烤羊肉串的招片上那些文字,竖过来一样,画得满纸的蜈蚣爬。
“不是。”路直抬起头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就这么淡淡地说。
“不是锡伯文?”老高一愣,“那是蒙文?”
杜老头忍了半天了,插嘴问:“他们长得很像么?”
“像。也不是很像。”老高低声说,“我觉得这不是蒙文,也不是达斡尔文。”
“满文。”路直低头看着说到,“这是用新满文记的笔记,不过能看出来是出自洋人的手笔。”
“你看得懂?”老杜问到,“你当真看得懂么?”
路直皱了皱眉:“有什么问题?”
“不瞒你说,事实上,我找人翻译过。但是没有译出。”老杜叹了口气,“我找的是锡伯人。没想到是满文。怪不得那个人没有译出来,说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老杜这么一说,老高的脸色突然之间变了,他小声说了句:“满文和锡伯文的差别,恐怕小得都可以忽略不讲了。如果真是满文,那锡伯人没道理翻译不出来。”
老杜眼睛一转:“噢?”
路直笑了笑:“老高说得对,满文和锡伯文大同小异,甚至可以说差不多是一种语言。不过是满文有的地方出个头儿,锡伯文不出头儿而已,我只说这是满文,但是后边我也说了,这是出自洋人的手笔。”
路直这番话说得我心里都痒痒的,明明是满文,难道是洋人写得不标准才导致别人翻译不出来的么?
“你先说说,你读得懂么?”
“当然,很简单。”路直点头,“里边记述了他临摹壁画的经过,和壁画的所在地。”
“在什么地方?”老高问。
“察布查尔。”路直回答。
“这不是废话……”老高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路直给截住了,“靖远寺。”
一下子屋子里的人都安静了。老高和杜老头交换了一个眼神后,说:“靖远寺是我那天开车时,没对你说过的。看来,你当真看得懂这篇东西。”
“是个什么道理,还望贤弟不吝赐教。”杜老头问。
“这实际上是通篇的英语,用满文拼的,明白?满文用的是女真人改良的蒙古文字母,也分元音辅音,这个作者是用满文字母,拼了一篇英文出来,有的地方虽然拼得很别扭,因为毕竟两种语言的字母的数量是有差异的,不能完全一一对应,但是只要是这个人精通英满两种语言文字,读懂它就非常容易。”
“那这就不是文字了。”杜老头一笑,“是密码。”
“可以这么说。”
“路先生厉害厉害。”
“你们就不想知道这几张纸上这么多的字讲的是什么?”路直问。
“路先生指教。”杜老头说到,“我们当真要是找到了宝镜,必然少不了路先生的一份。”
路直一笑:“希望你说到做到。别等我翻完了,就取我的小命。”
“那是不敢,路先生只要多多少少,说错了两三个字,可能我们一群人的命就全被取了。”杜老头虽然是对路直笑着说的,但两只眼却紧紧地盯着路直的眼睛。
我在这里观望着他们的博弈,我是有点笨了,到现在好像才明白路直和他们每个人说的话都是有含义的,或者说都是有目的的,而他们可能和路直说的所有的话也都有着很多层的意思,不过这也可能是他们说话太动心眼了,我才没听明白,不过接下来江虎说的这句话,却让我一下子就全糊涂了,不光是我,就连杜老头和老高也彻底输给了这句话,气氛又一下子更加紧张了起来。
“也许他只要你们其中一个人的命。”
路直并没抬头,只是一心一意地看着这几张纸上的内容,而老高却和杜老头面面相觑,杜老头给老高使了个眼镜。
“聋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高问。
江虎不再说话,当真就摆出了个聋人架式,往床上一躺,一言不发。杜老头看看老高又看了看面前的路直,老高想问路直,可路字还没说完,就又被杜老头拦下了。
“不要惊扰路先生的翻译工作。”杜老头说到。
我的脑子也混乱了,路直想杀他们中的一个人?哪个人?他和哪个人也该不认识啊,首先路直和江虎好像老早就认识一样,他们俩原来在我家里说话就都是话里有话的味道,看着像是结过什么梁子,但又相处得很融洽,没发生过什么争执。但是江虎总是说一些个离奇古怪的话好像是知道路直很多的事情一般,虽然那个不爱说话的江虎有一股二劲,但他总这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也够人呛的。
再说杜老头这群人,他们明显是和路直不认识的,如果说,他们话里话外透着和我家里有过什么瓜葛,和我爸有过什么生意上的往来,我是认同,因为那幅画毕竟是在我家找着的。但他们找上门来绑我到这儿,完全是一种被动,路直也是因为我才和他们认识,虽然他们不够友好,但路直没理由想杀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而且路直据我的分析应该是个警察,他和我承认了啊,他是个警察,那么他现在的目标不应该是破案么,难道是公报私仇?这也不是没可能,毕竟他和江虎明显很想来这里,那这么说,江虎有可能也是个警察。他们都有任务,可是又不像啊。
我越想越混乱,脑子里的东西都要打起结了。而在我想的时候,他们四个人也都很配合我,始终一言不发,路直在翻译我是知道的,江虎已经睡着了,但是老高和杜老头他们心里肯定在想着什么,而且应该不比我想得少。
路直的话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安静:“看完了,大体的意思我都清楚了,壁画在靖远寺不远的山中,不过是在地下。”
“地下?”
“对,据这几张纸上所说的,靖远寺地下,有一条暗道,顺着暗道一直走能到山里,壁画就在暗道之中,这是一个叫扎勒齐的锡伯人发现的,他当时带这本日记的作者去过。”
“我们到哪去找暗道?”老高问。
“他这上边写的挺神的,我照着意思念出来,你们听听,兴许你们能听懂。”
“你说,你快说。”老高已经按耐不住激动的情绪了,一个劲儿地催路直。
“这座庙有着它的生命,你要找到和他对话的方式,他才会将大门为你打开。扎勒齐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经历,他小的时候,调皮地发现了与这座寺庙对话的方式,就是注意‘Morihey’。”路直皱了一下眉头,“这好像是个什么佛的名字。”
“你再说一次?”老高推了一下自己的眼镜,“什么?”
“Morihey。”
“没有这尊佛啊。没听说过哪座佛是叫这个的。”
“后边还有,先听我念完吧。”路直接着说,“就是注意‘Morihey’手里的剑,当然还有‘Moriching,MorihongandMoribuy’他们各自……”
“啊!我明白了!”路直的话再一次被老高打断,他显得特别兴奋,用一种极富成就感的姿态和我们说,“他描述的,是四大天王,分别是东方天王魔礼青,南方天王魔礼黑,西方天王魔礼红和北方天王魔礼白。魔礼黑的形象中手中就是执着一把宝剑,后边呢,还有什么?是不是魔礼青手里有把琵琶,魔里红手里有条龙,魔里白手里是把雨伞?”
“是的。”路直核对了一下纸上的东西,“一把东方的弦乐器,一条中国龙和一把伞。”
“那就是天王殿了。寺里有一座天王殿。然后呢?”
“注意将他们手中的东西,以同样大小的力度同时向下拉,位于三世佛殿后边的地道门就会一下子打开。顺阶梯下去,只有一条路,往前走几百米就能到一个巨大的空间,这里,上方是山谷中的光亮,很微弱,但那光射到地下,能看到周围丰富的锡伯壁画。”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老高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急急地问杜老头。
杜老头并没有理会他这句话,而是思考了一会问:“他有没有提到过壁画和镜子的关系。”
“有。”路直点头,“我还没有说完,老高你先安静地听完吧。”
“行。”
“扎勒齐发现了壁画,但是我发现了壁画的秘密,每一幅壁画边上都有它们来历的介绍,有一幅叫做‘被阉割……’《宦官映照》的壁画的下面,有一串很古老的满洲文,他说明这幅画的来历,与锡伯人向西方迁徒途中的经历有关,并且,那个、宦官手中所捧的镜子,也是确有其物,被安放在那样一个神奇的地方。”路直抬起头,“没了。”
“这么说,只有找到那幅壁画,才能知道镜子的位置了?”老高问。
“看样子是的。”路直将纸交还给杜老头,“你们要去?”
“当然!”老高脱口而出,“肯定要去!”
“我们明天晚上出发。”杜老头看了看路直,“明天白天请三位好好休息。这里外来的人少,大家如果出去得多了,恐怕会……”
“我们在你们之前跑到靖远寺去的,特别是明天白天,我想售票员是不会允许我们爬到四大天王像的上边,搬他们手里的东西的。”路直站起来,“你们也早点休息吧,晚上不用动脑子,累。”
杜老头回敬了一个笑容说完晚安就走了。
路直关上门,走到我旁边坐下。
“明天晚上,我们也去么?”我问。
江虎一直在睡觉,可他们一走,他就起来了:“去。”
我有点想不通,我其实好奇心是有的,但是,他们是警察啊,至少路直是警察,为什么要选明天和那伙人一起去破坏文物呢,除非他们想抓现形,但是如果他们要执行任务的话,不用把我也捎上吧。
我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路直和江虎已经两顿饭吃回来了,两个人在那拿着图纸研究着什么。
“什么东西?”我走到他们旁边。
“这是靖远寺的平面图。”路直看了看我,“今天我出门搞到的。”
“你偷着弄的?”我问。
“是啊。”路直回答,“旅游景点啊,这种图有得是。”
我想吧,如果昨天路直说的都是真的,那地道门打开之后,让他们那伙人先下去,然后最后一个一旦进去了,我们就马上关门,报警。路直完成上级任务,我也可以回家去了。不过这话我没说,只是看看他们是怎么一个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