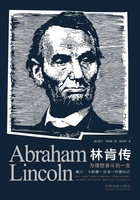林语堂一直认为制度是一项很糟糕的东西,这种对于刻板制度的反叛以及对自由的热爱精神,在他小学时代就彰显无遗。
为师不尊
要当好林语堂的学生,你必须具备一颗强大的心脏。他给你上的第一堂课,是教你怎样在课堂上吃花生米,而他给你上的最后一堂课,则是把你叫过去相面,从而决定你的学习成绩。
林语堂曾经在苏州的东吴大学兼任了一年的英文教师。在第一节课上,林语堂就给学生们留下了惊世骇俗的印象。刚进教室不久,他就拿着一大包带壳花生逐个分给班里的学生。
学生们一个个瞠目结舌,不知道这林老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更有多疑者认为这可能是老师对自己的一个考验,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带头剥花生。
林语堂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开玩笑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说着,自己先动手剥起花生来。
学生们听了林语堂的话,一个个哈哈大笑,课堂里剥花生和嚼花生的声音响成一片。看着大家把花生吃完,林语堂心满意足地宣布:“今天的课就是这样,下课!”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班上如雕塑一般呆坐的学生。
如果要寻找林语堂这种上课方式的源头,我认为近的可以追溯到英国的下午茶。在剑桥大学,学生们获益最多的场合,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与导师喝下午茶的地方。喝下午茶的时候,你完全不用像正式上课一样拘束,这种远离课堂、自由而随性的气氛,最容易产生思想的激情与火花。在剑桥,有个不成文的制度和呼声:“来吧,来喝下午茶,不付费。”剑桥的下午茶迄今为止已喝出了六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的下午茶风气,不仅见于剑桥,在西方的大学里都普遍存在,想必林语堂一定深有体会。
至于远的,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上课时,从不一本正经,高高在上。他喜欢的方式是跟学生们围坐在一起,彼此之间不过分注重尊卑,而后孔子会提出问题看大家有什么看法,鼓励大家随意发挥,我口说我心。夫子高兴的时候,时不时还要跟学生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在这样轻松而愉悦的氛围中,学生们的灵性和秉性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升。这也是我们尊称孔子为伟大教育家的原因。林语堂对孔子的智慧有深入的研究,这一点他不可能不明白。
但你如果就此认为林语堂的课可以轻易地蒙混过关,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林语堂同样会考察学生成绩,只不过他考试的形式绝对在你我的想象之外。到了最后一节课——这可能是林语堂一学期唯一一次在讲台上正襟危坐,他手拿学生的花名册,按照顺序念班里学生的名字。每一个被念到的学生,就自动站起来。接着林语堂会像看一件艺术品一样把这个学生从头到尾打量一番,之后在成绩册上像模像样地记上一个分数。
这样别出心裁的考试形式源于林语堂对考试制度的厌恶,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他还把考试比成大煞风景的“煮鹤”:“恶性考试艺术就是煮鹤艺术,可惜被煮的是我们男女青年。”
老师的学生时代
林语堂一直认为制度是一项很糟糕的东西,这种对于刻板制度的反叛以及对自由的热爱精神,在他小学时代就彰显无遗。
林语堂读小学时做的最让他引以为豪的事情是一次他在考试前夕窃取了老师的考卷,使得整个班级的同学在这次考试中一致得了高分。考试后,老师为了搜捕出潜伏的“敌特分子”忙得晕头转向,但最终一无所获。不过这样的事情林语堂也只做了一次,金盆洗手的原因很无厘头,原来他觉得干了这么引以为豪的事情却只能憋在心里实在太痛苦。
而到厦门寻源书院读中学的时候,林语堂的自由天性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寻源书院是个教会学校,身为牧师子女的林语堂可以免费上学,但这并未激起他的感恩之心。相反,寻源书院死板的教育让林语堂极其反感,以至于他在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时竟然说:“我的中学教育完全是一个浪费!”
寻源的校规严格,学生们从每天早晨八时到下午五时,都必须静坐在教室里读书,“偷看杂书,或交换意见(即所谓课堂闲谈)者,皆是罪过,是犯法”。对此,林语堂采取了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方式,老师在上面讲得唾沫乱飞,而他却在下面看自己喜欢的书而逸兴遄飞。对此,他抱怨道:“上课和不上课的分别是,在假期,我可公然看书,而在上课的时候我只好偷偷地看书。”
林语堂从心眼里鄙视那些所谓的最优秀的学生,他认为这些学生只不过是老师肚子里的蛔虫,靠揣摩老师心思来获得高分。对于这种学生,他有—种“韩信羞与绛灌伍”的感觉。
上了圣约翰大学之后,林语堂照样我行我素。大考之前,众人都在“头悬梁,锥刺股”,林语堂却一个人跑到苏州河边去钓鱼。后来,他还“蛊惑”了一个同室好友,考试前夕跑到苏州河边跟他钓了一天的鱼,结果考场之上兵败如山倒。这件事也使林语堂反思,看来自己的学习方式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林语堂学生时代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在哈佛大学度过的,哈佛大学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他受益匪浅,在这里他可以跟自己的老师上午争得面红耳赤,下午照样坐下来一起喝茶侃大山。而哈佛大学卫诺德图书馆瀚如星海的图书典藏更是让他如获至宝,他的灵魂在这里可以痛快地畅游。后来,他把自己与哈佛的关系形容为猴子与丛林的关系。
当圈养成为一种时尚
陈丹青曾经愤慨地说道:“中国大部分大学生就像被圈养的家鸡、家犬。就这样放出去谋生,当然比不上那些草鸡、野犬。”
其实,陈丹青先生无须大惊小怪,中国的学生被圈养,大学并非罪魁祸首。这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小学时代,那时的圈养是一种强迫性圈养,而大学的圈养只不过是习惯性圈养,前者的悲哀要远远大于后者。
最可怕的是,自从近年来发生一两起针对小学生的校园血案之后,全国各地草木皆兵。甚至有媒体报道说,有的小学规定学生下课后除了上厕所以外什么地方都不准去,以免出“意外”,这一做法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学校所效仿。校园杀手只能残害几个学生,而我们的教育者却能谋害整个民族的未来。鲁迅若在世,他一定会重新发出那句振聋发聩的话——救救孩子!
我们为林语堂感到庆幸,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身上这种原始的野性从来没有被制度所驯化。林语堂所就读的教会学校绝不像他所说的那么死气沉沉,反过来它们可能要比某些国立的大学有活力得多,当年的中国,圣约翰、燕京、辅仁、震旦诸多教会大学都是中国学界的佼佼者。就连林语堂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
很遗憾,林语堂这样的学生如果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很可能会被定位为一个不可调教的学生而走向另外一条道路。而林语堂这样的老师如果生活在现在的中国,大半也是要被作为异端分子看待的。作为老师的林语堂从不用正规的教科书,光这一点他就要被冠之以误人子弟的名号而被批斗。
中国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其实从一本书就可以知道了。书的名字叫《别闹了,费曼先生》,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主人公费曼,他得过诺贝尔奖,被誉为现代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这本书讲述了费曼从一个无可救药的顽童成为大师的过程。直到成名后,费曼仍然“恶习难改”,他在领取诺贝尔奖的同时也被按摩院请去画裸体画、偷偷打开放着原子弹机密文件的保险箱、在巴西桑巴乐团担任鼓手。他曾跟爱因斯坦和波尔等大师讨论物理问题,也曾在赌城跟职业赌徒研究输赢机率。
美国的社会可以宽容地接受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科学家,不知道在中国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