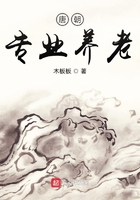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
——《天下文宗司马相如》序
谭继和
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赋圣词宗的地位。宋人林艾轩、朱熹称其为“赋之圣者”,明人詹景风称其为“赋家之圣”,甚至还有人把他视为独步天下的第一文人,明人侯一元就认为“古今文人,独一司马相如哉”。不过,对这位赋圣,历史上也有人提出疑难、訾议,集中在出生地之谜、大赋的历史地位、通“西南夷”的评价以及同文君的自由私奔等四大问题上。本书即是针对这四大问题产生的历史语境,根据学术界多年来研讨的前沿学术成果而写出来的。书中对这四大问题的描述,也汇集了十多年来以四川的相如文化研究会为中心一些海内外学者研究的智慧和心血。尤其是相如故里问题,今天能得出相如“生于蓬安,长于成都”的结论就很不容易,经过学者间多少次论难才能有所依据地把它确定下来,本书作者邓郁章先生以及蓬安、南充、成都的一些学者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不羡千金买歌舞,青灯黄卷研相如。疑义精要相析论,墨畦生涯尽入书。”郁章先生多年来的艰辛付出,本书算是一个回报。
有关司马相如的研究,其基本轨迹大体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一是关于相如故里的争论和探讨;二是关于相如文化的多方面研讨。这两个阶段体现出由相如个人文本的研讨向汉代精英集体文化性格和时代精神的研讨转型的特点,也即马克思所说的由原初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的研究特点,我曾在《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究论集》一书的序言里对此作过解析,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着重强调的是,由本书的探讨,引起了对相如文化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司马相如不只是一个个体,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相如文化,我认为今后需要深入研讨下列特点:司马相如是汉代“综群书”的“通儒”。相如大赋是“孔氏之门用赋”升堂入室的产物,是孔子诗文教化的结晶,实具有“文以贯道”当以“文章为最”的崇高文化地位,这也是汉代时人的文化观念,是文化中国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个特色现象。文化中国熏育出了“文伯”司马相如,相如又以其站在那个时代高度的赋论、赋作和文韬武略,对文化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司马相如是汉代文化中国“采儒术以文”的开发者,是以其大赋而成就为汉代“文章诗教”的奠基者。总而言之,“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的关系”是需要我们做的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至今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专题涉及,而这又是我们深入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以“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为主旨,应该是未来研究方向的待望。
这里简要地说一说我的四点看法:
一是司马相如在文化中国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
相如绝不只是一个文学家,只是单纯“为汉词宗”(《华阳国志》),他应是“以诗书而儒”的“通儒”,是百科全书式的汉代大儒家之一。宋人王俦说:“吾侪蜀人诗书而儒自长卿始,诚如(秦)宓云。”明人李贽称相如为“词学儒臣”,这些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抓住了相如文化性格的本质。司马相如《解客难》一文曾针对客人关于相如即为儒人,为何不“作汉一经”的责难,提出了自己关于文即“六经”的看法,这是当时非常大胆的精辟见解。在后人看来,相如此论正表现了西汉时期“以文章为盛,以诗书为儒”的时代特点。王充《论衡》说:“农无强夫,谷粟不登 。国无强文,德闇不彰。”强农与强文是国家关乎命运强弱的两大支柱。而相如正是“国之强文”这一支柱的代表。他死前挂念的是《封禅书》,死后献给汉武帝,果然八年后封泰山,禅梁父,礼中岳。以后封禅遂成为历朝定制。相如此项举述,遭到非议甚多。其实,“封禅”从本质的原初抽象看,正是中华一统凝聚力和向心力信仰的表现。相如为封禅制提供的理论依据,今天原文已佚而看不到了,它应该是对大一统的文化中国的礼仪性信仰做出的一个奠基性的贡献。由此观之,相如其人在文化中国发展史上实占有一席重要地位,而且首先是以“润色王道”的圣门儒术为主要特色,其次才是文学方面的词赋之宗,应该摆正这个位置。唐人称相如为“文伯”、“雄伯”,正是从儒宗这个层面说的。唐人张说曰,相如“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之人谓之文伯”。这个看法,正好说明相如的文化个性特点。他是“润色王道,发挥圣门”“以古圣贤为法者”的儒之“文伯(霸)”、“雄伯(霸)”,“绝后光前”(陈子良语)的“文雄”(李白语)和“通人”(《隋书》)。对这一特点,龙显昭先生等少数学者曾经指出过,但未引起学界重视。
二是相如大赋在文化中国经典上的地位问题。大赋能否与儒经同等看待,是否以“文”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是今天学者尚未触及而需要辨证的一个大问题。
重视“文章之盛”,是汉代的时代特征,前人曾多所论述:“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 “孝武之后,雅尚诗文”(《周书》),汉以“文章为盛”,“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班固:《两都赋》)。正因此,汉代上自公卿,下至庶民皆通文章。韩愈说“汉朝人莫不能文”,柳宗元说汉朝“风雅益盛,自天子至公卿、大士、士、庶人咸通焉。四方之文章益烂然矣”。
汉代“文章”二字的内涵,首先是指汉大赋。这是因为汉赋为“骚之余”,是承袭诗骚发展起来的。《诗》是儒经的重要门类,诗教更是儒家礼教的核心。诗骚赋系统,发展到汉代才明确与六经训诂之学分途发展,成为两大系统。而汉赋则是“文章”系统即诗教系统的代表。这是其一。
大赋创作是一门专门学问,必须要通经和通文字,这是汉赋的基础学问。宋人晁说之曰:司马相如造诗赋,“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其意”。作大赋必须具备“古字之学”与“通经之学”这两个基本条件。这是其二。
“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相如赋为何能出人头地,是因为他“命意宏博,措词富丽,千状万汇,出有入无,气贯一篇,意归数语,此长卿所以大过人者也”(谢榛语)。要有万卷才学,特别是儒术根底,才会有作赋能力。这是其三。
更重要的是,作赋要有儒者的正气。宋人周紫芝认为相如赋“大哉气之为用,虽上下与天地同流可也”,刘壎认为其“雄浑之气溢出翰墨外”。除儒学以外,相如赋还特别融入仙道之学的想象力,成为以羽化飞仙为特征的道学的滥觞。相如赋体现了“列仙之儒”(《大人赋》)的鲜明特点,这是其四。
因了上述四个条件,相如大赋的地位就提升到了与儒学六经并行的儒学文章(诗教)的崇高地位,故相如也被历代一些文人称为汉文章之祖,“长卿之于文章,实全蜀开创之祖”(清人钱谦益语)。不仅是全蜀文章之祖,也是汉代整个圣门辞文之祖,其“辞文遂最一代”(明人尹台语)。“后世文必称汉,言汉文之雄,必曰司马、扬、王”(明人詹景风语)。“圣门论赋,相如为入室之雄”(唐人卢照邻语)。
总起来看,相如大赋是汉代中国诗教文章的代表,具有儒学经典“兴废继绝,润色洪业”(班固:《两都赋》)的作用,属于汉代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可登汉文大雅之堂。所以,不能把相如赋只看作“词赋之祖”,而要从“汉文章经典”的广视角来给予肯定。
三是相如大赋的浪漫主义精神内核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地位问题。
相如论赋家之心是“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论赋家之迹是“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赋家之心与赋家之迹,构成相如浪漫主义文学精神的根基,开启了巴蜀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成为“西蜀自古出文宗”,以相如为榜样,他之后,从扬雄、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杨升庵、张问陶、李调元,直到郭沫若、巴金皆“比肩相如”,始终坚守的精神追求。它体现了司马相如凌万乘以峥嵘之气,贮千古以磊落之胸,洗宇宙以磅礴之神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总览天地人的大一统宇宙观。这是汉代雄阔宏伟盛世的时代精神的反映,这也是文化中国共同精神家园中坚守的情怀,是仰望星空、洗空宇宙的民族文化相象力的结晶。
四是相如通“西南夷”在民族融合、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上的作用问题。
“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史记·平准书》),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举措对民族交融,开拓巴蜀的历史作用。“西南夷”有两支:一支是“南夷”,一支是“西夷”。相如开通“西夷”和“南夷”,不仅是地理中国的统一问题,更重要的价值是文化中国的认同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它促进了大中华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在推动文化中国认同方面也起了重大作用。例如,开通“南夷”,促使夜郎文化与巴蜀文化交融。开通“西夷”则使冉、駹、邛、笮、徙、榆等族群进一步与蜀人融汇。所设冉駹邛笮徙榆六都,就是文化认同与交融的体现。相如通“西南夷”的举措,统一和稳定了西南地区,促进了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向中原文化凝心聚力,至今都还有深远的影响。
南怀瑾先生曾说:“立国之本是文化。”文化是中国形成和发展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的血脉,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文化中国的认同,是文化立国的历史过程,是大一统中华多民族国家融合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中国是养育历代知识精英的肥壤沃土,而历代知识精英则对文化中国的核心文化——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本体、终极诉求和终极核心价值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这个层面观察,司马相如的浩然之气、浪漫之韵、大雅之声,在文化中国巨人的长廊里实占有一席不可磨灭的地位。尤其是在汉代,以文章教化为盛,儒家文明定型初曙,诗教和礼教第一次国家法典化的关键时期,司马相如是站在这个时代高度上的一颗闪亮的北辰之星,是汉代文章之盛的一个闪亮的文化路标。因此,对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的研究,正是我们应该取向的有关司马相如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谨以待望,故乐为序,以求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