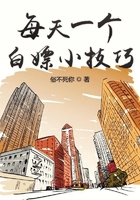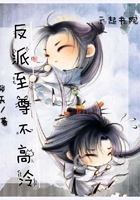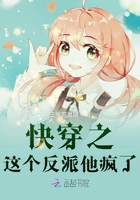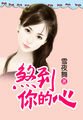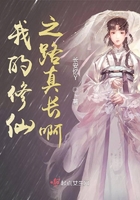普希金的迅速成长,引起了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注意,他们都知道,皇村学校有一个天才的少年诗人,都想一睹他的风采。于是,在诗歌史上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由于普希金无权随意外出,当时的一些大诗人便亲自到学生宿舍来拜访他,向他表示敬意和鼓励,而在最先前来拜访普希金的诗人中,竟然有他少年时代最喜爱和最景仰的诗人巴丘什科夫。
从此以后,写诗似乎成了普希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短短的几年里,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很使人怀疑,他哪儿来的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呢?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爱好是真正的老师。确实如此。对于普希金来说,他所热爱的只是诗歌,而别的一切,都被他放到次要的位置。拿学习来说,对于那些他所认为的无关紧要的学业,他不屑于花费过多的精力,更何况皇村学校的教育目的和教学方法本来就令人怀疑,与普希金同一时代的许多学者和教育家都对此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不过,皇村学校的教育者们却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
这样一来,普希金在皇村学校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他总是那么随心所欲,总是对教师的训导不理不睬。在学校的6年间,他一向对“功课”、“大部头书籍”、“书呆子”及“冷漠的智者”掩饰不住自己的讥讽,对学校里只为装饰门面的教学持排斥的态度。所以大多数教师给他的评语都是“学习不努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学校规定的功课才是值得学习的,至于什么诗歌创作,他们才不看重呢!而他们的校长甚至连这一点也拒不承认,他对普希金的评语是:“有一颗空虚而冷酷的心,不信奉宗教,其最高和最终目的,不外乎以做诗炫耀自己。
不过,他写诗也未必有牢固的基础,因为他不肯认真写任何东西。”在教师里,只有普希金的语文老师对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817年6月,普希金结束了6年的皇村学校的学习生活。当他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是18岁的青年人了。虽然他的考试分数不高,但他却已经开始写作《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是他著名的作品之一)了。尽管他没有作为一个好学生从学校毕业,但后来却成为了全世界最著名的诗人。而且,他并不仅仅是个诗人,更是一名追求自由的战士。
雨果
法国文学家(1802—1885)
1802年的法国。大革命的余晖还没有在法国上空完全散尽,拿破仑已经当上法国的第一执政官,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挣扎在专制的军事独裁统治下。
在征服世界的欲望的驱使下,拿破仑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不管这场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到底是什么,但受苦的总是人民,连年不断的征战,使得无数家庭骨肉分离。更惨的还是军人,他们东征西讨,南拼北杀,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无数次的枪林弹雨中,他们得到的只是遍体的伤痕和满手的鲜血。
维克多?雨果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在一个法国军人的家里。他的父亲是拿破仑军队里的一名营长,几年来东征西讨,几乎没有一天能得到安宁,先后有两匹战马死在他的胯下,可是他却并未像预想的那样得到升迁。
母亲望着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心里充满了愁苦和不安。他是那样的瘦弱,助产妇甚至断言这孩子是活不长的。值得庆幸的是,孩子居然越长越结实,6个星期以后,他已经能够经受住旅途的劳顿,随父亲服役的那个营从贝藏松转移到马赛,并从此开始了他颠簸不定的童年生活。
转眼间,雨果和他的两个哥哥都长大了,该去上学了,长期的近乎流浪的生活显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接受教育。这时,父母之间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和其他一些原因,早已产生的裂痕也越来越大了。于是,母亲带着他们回到了巴黎,住在斐扬丁纳瓮巷的一幢旧式楼房里。最使小兄弟们高兴的是他们可以不用再坐在颠簸不已的马车上艰辛地跋涉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家,而且这幢房子周围是一座花园。这花园成了孩子们的乐土,他们住下的第一件事就是接收这片新的领地,把各个角落和荆棘丛细细地勘察了一番,把花园的地形整个记熟在心里。但是,他们到巴黎来,并不是专为享受这花园的,他们还必须学更多的东西。
由于年纪小,雨果还进不了公学,母亲把他和二哥送进了一家私立学校。在这里,雨果显示出他惊人的天赋——他学的是拉丁文和希腊语,很快,他就能流利地阅读和翻译贺拉斯的作品了。
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客人。
“这是你的教父。”母亲对雨果说,“他要在咱们这儿住一段时间。”但她并没有对孩子说,这个人就是因参与反对拿破仑的活动而被判了死刑的拉渥列将军。他正在逃亡。
从这天起,雨果每天放学后,教父就和他一起玩耍并帮助他做功课,给他讲历史。从教父那里,雨果第一次听到了“自由”这个词,并从此牢牢地记在心里。
可是不久,教父突然被抓走了,雨果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年长的朋友,只是在两年以后,看到了教父已被执行死刑的布告。
雨果的母亲酷爱读书,是图书馆里的常客。她允许孩子们自己去图书馆,让他们凭自己的喜好去读他们想看的书。雨果似乎什么都喜欢,在这个小图书馆里,他阅读了莫里哀、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著名作家的作品,而其他的什么散文、诗词、游记以及哲学、法律、历史等书籍,他也是来者不拒。
但是不久,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就被迫结束了,雨果的父亲回到了巴黎。
这时的雨果已经13岁了,父亲决定把他送进一家寄宿学校,在那里他要准备功课以便报考综合工科学校,父亲的想法是他的孩子应该成为工程师或者军事专家。
刚进学校的那段时间,学校里的生活对雨果来说简直是苦不堪言,学校里有严格的纪律,甚至常常对学生进行体罚。起床、睡觉、游戏和读书,都得按口令进行。雨果第一个反应是:他没有自由了。
幸亏还有诗。
使雨果认真地做起诗来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一次,他和一些同学溜出学校。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可就是在这样美好的天气里,却响起了恐怖的隆隆炮声,在不远处的田野里,拿破仑的军队和保皇党的军队正在拼杀,士兵们一个个地倒在地上……
雨果心里急剧翻腾着:他们为什么去送命呢?难道他们真的愿意这样做吗?难道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流尽自己的鲜血?太阳怎么能放射出如此快乐的光芒照耀着这样恐怖的场面?
他非常想选择一些特殊的词语来表达自己还不十分明确的思考,来表达自己愤怒、痛苦和困惑的心情,他想到了写诗。
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凶狠的老师严密地监视着他们,不许学生做学校规定以外的任何事情。
这并不能难住雨果,他常常在夜晚寻词造句,然后在白天偷偷地把夜里想好的诗句写在纸上,锁进抽屉里。在他的诗作中,出现最多的词是“和平”、“自由”。
他的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并未能完全躲过老师那鹰隼一样的眼睛。一天晚上,雨果发现抽屉的锁被撬开了,他的诗稿都不见了。不一会儿,他被叫到老师的房间。
“学生是不准写诗的,你为什么违反规定?”老师严厉地质问道。
“可是谁允许您撬别人的锁呢?”雨果严正地回答道,他认为,这种对自由的明目张胆的侵犯是不能容忍的。
接下来的是一场激烈的争执,最后,老师也许认为偷撬别人的锁对一名老师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对雨果进行了一阵训斥之后就放他走了。雨果胜利了,但他知道,这也许意味着以后的日子会更难。
还是诗,帮助他摆脱了这种窘境。
1817年,法兰西学院以“在任何生活情况下,学习所给予我们的快乐”为题搞了一个命题诗作评奖。雨果决定和真正的诗人比试比试,检验一下自己的才力,于是他写了一首长篇颂诗,列举了历史上出现的大量事例,雄辩地证明了在最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学习如何使人变得高尚起来。
诗稿写好后,他决定谁也不告诉,而是和他的一个朋友偷偷地送到了法兰西学院,不想在离开的时候迎头碰上了他的哥哥。
等待的日子是难熬的,但时间一长,雨果也不怎么把这事放在心上了。一天,他正在和同学们玩地滚球,突然看见他的哥哥走进了校园。
“你干吗把你的年龄告诉学院呢?”哥哥劈头就问,“要是你不写上你‘只有15岁’的话,说不定会发你个奖呢,可现在你只能得到表扬了。”哥哥看似严厉的脸庞上显露出掩饰不住的兴奋。
是的,在那个时代,受到法兰西学院的表扬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更何况是一个15岁的孩子!小雨果一举成名。家里人高兴自不必说,学校里的老师也转变了态度。从此,雨果可以光明正大地做诗了。
过了不久,雨果离开了这所学校,成为路易大帝学院的学生。
路易大帝学院对学生的约束不那么死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学自己所喜欢的课程。在这段时间里,最吸引雨果的是参加他的哥哥和哥哥的爱好文学的朋友们组织的每月一次的聚餐会。
在聚餐会上,每个人都必须拿出他上一个月所写的新作品读给大家听,然后大家进行评议。这种活动雨果非常喜欢,每次集会都必定到场。
在一次聚餐会上,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在座的所有人都会写诗,为什么不在散文创作方面尝试一下?他提议:“我们来搞一次集体创作吧,大家合起来写一篇小说。”
“那么,怎么个写法呢?”人们很感兴趣。
“我们可以假定,有几个要好的军官在战斗的间隙聚在一起,分别讲述一段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故事,然后合起来,就是一本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风格的书了。”
“那么,什么时候交稿呢?”一个人问道。
“两星期后。”雨果说。
几乎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大家都认为雨果在开玩笑——用两周时间完成一篇小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打赌吧!”雨果认真地说,“我要是写不出来,就在这儿请诸位吃一顿。两个星期以后见。”
两个星期以后,当所有的聚餐会成员又聚在一起的时候,雨果抱着一摞手稿走了进来,给大家读了他刚写好的小说《布格?雅加尔》。
一开始人们还不是很认真,到了后来,大家完全被吸引住了。小说读完了,人们仍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有人提议,雨果写出了这么精彩的小说,应该每个人都请他吃一顿。
这篇小说在1826年出版了单行本,这是雨果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当时他只有16岁。
1818年8月,雨果的父母离婚了,孩子们被判给了母亲。母亲了解儿子的才能,她允许雨果辍学,全力投身文学活动。于是雨果加入了他哥哥创办的一个小型的双周刊杂志《文学保守者》。开始他还只是一般的帮手,不久以后,雨果就担当起刊物的主角来。不过,即便是经常阅读这本刊物的人也不会知道,刊物上发表的许多不同署名、不同内容的文章,都出自这个不足17岁的少年的笔下。
1822年,雨果的第一部诗集《颂诗与杂咏》问世。
1823年,雨果的长篇小说《冰岛莽汉》出版。
从此,他便开始了自己辉煌的文学创作的历程,戏剧《克伦威尔》、《艾那尼》,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诗集《东方集》、《秋叶集》、《静观集》等纷纷面世。
在这些闪光的著作中,雨果对底层人民的悲惨处境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专制统治的残暴、虚伪和无耻进行了愤怒的抨击,他呼唤人道,歌颂自由。他永远是人民的作家,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
“我留给穷人10万法郎。我希望用穷人的大车将我的灵柩送到公墓。我拒绝所有教堂的安灵仪式;我请求所有好心的人为我祈祷……”
安徒生
丹麦文学家(1805—1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