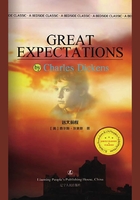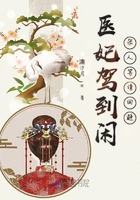从进入学习练琴就听人强调基本功,老师一上来就告诫,要练好基本功,否则将来搞不上去。这个基本功,往往被形容成房子的地基,地基没打好,房子自然造不高,造高了也会塌。不假思索地听起来,这话也显得挺有道理的,何况身边有无数例证,都是技术不过关,抠不下来大协奏曲,不忍卒听。我和同伴们都是这样被教导了那么久,最后拉琴没拉上去,大家都自认是因为基本功不好,往往还自认为是开始练习基本功不够早,那时候我18岁开始学琴,学吉他,都还自叹太晚。
可是所谓的“基本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真的就是像房子的地基吗?造房子前别的都不动,先打地基,等地基打好了再造上面的,而且一旦地基打好了,就一劳永逸了,上面的楼层就可以安心地造,不必隔三差五重新掀开地基加固。但练琴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有哪些技巧必须在某个年龄之前完全掌握、并且能够被完全掌握,之后就可以在音乐演奏中游刃有余了吗?
这年人在首都,跟着小朋友重新练琴,从头开始观察西方的音乐教育,把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都翻洗了一遍,发现好多误导好多陷阱,典型的就比如“基本功”一词,不仅特别具有误导性,简直可以说是个神话。
所谓“功”,很简单,就是演奏技巧,但是技巧有不同级别,哪些算“基本”的,又是怎么个“基本”法儿呢?确实,有些技巧算得上非常基本,没有这些技巧,连最简单的曲子都演奏不好。但是还有是高难度的技巧,这些技巧一点也不基本,没有它们虽然演奏不了高难曲目,但是也能把简单的曲子演奏好。两部分技巧分别谈。
前者那种技巧算基本功吗?大概得算吧。可是,练琴却并不像盖房子,从来就没有什么时候地基能算大功告成。事实上,小孩子从小学习演奏乐器,基本上所有的技巧,包括那些最初级的,都是在反复打磨不断进步,没有谁是小时候把某一套技能练完备了的。以弦乐器为例,哪怕是最基本的运弓、音色、揉弦,单音音准,也是要一辈子“拳不离手“的。专业独奏家仍然每天练习那些他们从儿时就开始练习的最基本的技巧,有时是为了保持技艺,有时甚至仍然在这些技艺方面争取提高,一个长弓就要练一辈子。而另一方面,学琴的人(不一定是小孩子)是在学习的难度逐渐加深中不断返工,哪怕是最初级的技巧,一个人也不必、也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掌握完好,技巧的反复磨练永远处于进行时,也没有任何确定的年龄边界,要求一个人必须在(比如)十二岁以前完成这磨练。就是说,如果仍然拿盖楼来比喻,那么地基是永远在修补改进的,永远没有完成的时候,然而并非在没有完成时就不能造上面的结构,一楼、二楼乃至十几楼都在建造地基的同时建造。所要注意的仅仅是,不要学习超过技巧能力太多的曲目,也就是往上造楼的时候得悠着点,别地基还不够厚的时候就一下子把楼造太高。其实,几乎所有的技巧在成年之后也能训练,只不过比小时候慢而已,哪怕是三四十岁的人,只要方法正确,也能改进技巧。而对于十几岁的人,改进技巧不仅完全没问题,而且简直是大好时光,甚至不比更小的小孩慢,有些训练结果还比小小孩稳固,因为那些骨骼肌肉还在发育中的孩子身体的控制感觉都还在变化,琴的尺码也得跟着增长,每换大一号的琴,或者每蹿一下个头,技巧都得调整修复。西方许多学生是在进入音乐学院之后才发生技巧的大规模改进的。我认识一位职业钢琴家,甚至是在三十岁之后发生了音色的巨大改善。音色(触键)应该算是钢琴相当基本的技术,甚至李赫特这样的天才,也自述遇到涅高兹之后音色才学会怎么打开,那时他也不老小了。技巧的提升,需要好的老师、正确的方法和训练步骤,与这些因素相比,年龄反倒是最不要紧的。我们的确时常看到大孩子和成年人学习演奏失败或者缺陷很多,但与其说是败在肌肉训练太晚上,还不如说是败在没有遵循正确的方法步骤上。多数年龄大一点的人,都没有耐心从简单曲目开始按部就班地慢练,急于求成,难度迅速提升,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地基打得太晚,而在于根本跳跃过去不打地基。
再说比较高难的技巧。这部分,一般都是学琴有过五六年(或七八年不等)之后才开始学习,大概算不上多么“基本”了,不过当人们谈论为什么掌握不好高难技巧时,却时常不分青红皂白把帽子扣到“基本功不好”上。我用小提琴举例,这部分技巧大概可以包括快速、跳弓、双音(包括八度)、高把位、左手拨弦等等。中国的很多学生,就是在这个关口上不去了。当年和我一起拉琴的同学们,几乎都在这个阶段卡了壳。前几天一个曾做过几天乐队首席的朋友还笑谈,当年练习门德尔松的协奏曲练不下去,因为双音拉不准,她自己总结——“基本功不过关”。我说,完全不是这样,不是之前的什么技巧不够她训练双音,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基本功”,她还掌握得非常好,十来岁的时候参加北京市比赛还拿过一等奖。她拉不准双音不是因为单音拉不准,不是因为弓不直,不是因为音色不好,不是因为之前是什么技巧没过关,而就是彼时彼刻过不了双音那关,因为没有得到好的指导以正确的方式训练双音。怎么才是正确的方法呢?我是最近才知道的。原来要左手保持双音手位,但右手先只拉单弦,先来低声部,再来高声部,反复很多次,最后再两根弦合起来。而八度练习时,如果连续八度把位上移,重心要放在低声部,literally左手重量要偏向低声部的一指上,由一指控制把位音高,而高八度的四指只是保持手型平移,同时四指控制逐步缩小一指与四指的间距;但如果是把位下移,则要反过来,由四指控制音高,由一指控制逐渐增加一指与四指间距。又比如分弓快速乐段怎么练习呢?快速分弓经常出的问题是左右手错位,听起来就是乱的。纠正错位的一个灵丹妙药就是在音符上加附点,十六分或三十二分音符,每隔一个加一个附点,先练奇数音加长的,再练偶数音加长的,如此多次反复。当然了,所有难点都必须隔离开单独慢练,慢速反复至少七遍以上。最关键的是,在练习难度较高的曲目时,要特别注意拆解技巧!因为技巧比较困难的乐段往往是多重技巧重合、且左右手的高难技巧重合,所以必须把不同技巧隔离开,单独训练,最后再合起来。如果不进行技巧拆解,而是就照着谱子上原样写的生生地硬抠,是攻不下来的。当年我们大概都是败在这里了,没有老师教我们怎么把难点拆开。
正确的练习方法破除基本功,才是真真切切的实际观念,或许你会觉得花钱请个老师指导才能进步,不一定,可能看个人的音乐天赋,也可能是能力。
音乐能力不是音乐天才或者一部分人的专利,而是每个正常人都具有的素质。判断音乐能力应该提倡多元化审视标准,不能仅靠表演能力与创作能力来评价,听赏能力也是重要的音乐能力,更是音乐得以存在的基础。判断一个人音乐能力还应基于其生活的文化背景去考量,摆脱欧洲中心的音乐能力话语霸权。提倡更多人通过听赏参与到自身民族音乐文化传统中来,彰显本民族音乐能力。
判断人的音乐能力需要知道不同的社会究竟选择了哪种音响、哪种行为而将其称为音乐能力。布莱金认为“如果音乐心理学和音乐能力测试的研究,没有在音乐能力的本质上达到一致,那么原因很可能是它们一直存在着排他性的种族中心主义。”
当今中国的音乐院校传授的大多是西方音乐知识,主要就是欧洲某一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音乐理论体系和实践,以欧洲巴洛克时期以来的音乐和音乐理论为主,进入不了这一体系的音乐能力则********。因此,只有“一部分人”才具备音乐能力,这种能力的判断往往是根据其依照乐谱表演音乐的能力,或者把音乐记在乐谱上的能力来确定。比如现在音乐院校的招生专业测试就是明显的例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每个正常人都存在音乐的本能,尤其是感知音乐的能力。如在没有乐谱的社会中,口头传授、准确聆听和表演一样重要,并且是衡量音乐能力的尺码,它确保了音乐传统能够延续。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音乐能力却没有像语言能力一样得到承认和培养。人们通过表演乐谱记载的音乐来判断此人是否具有音乐性,而大多数人的音乐潜能被无情的抹杀。
音乐是人类组织起来的音响,他的功效在下面情况下才能更好地被体现出来,那就是:和音乐创作者享有共同的文化体验,或用已经习惯的耳朵去聆听音乐时,在某些方式上能够共享文化体验。因此,断定一个人是否具备音乐能力就不能不考虑其个人文化背景。
当今社会普遍的现象是将音乐表演能力、音乐创作能力视作音乐能力,听赏能力则被忽视。比如现在学习钢琴的孩子往往以郎朗、李云迪等人作为崇拜对象,这正是片面强调音乐表演和音乐创作能力的一个表现。又如,在学校里,如果说一个孩子不会任何乐器,也不会演唱歌曲,他就会觉得自己是没有音乐才能的,也许在他的观念中,只有演奏音乐才是有音乐能力的体现。然而他也会被某段音乐深深吸引和打动,会与音乐作品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会因某种音乐强烈的节奏手舞足蹈。他忽视了自己重要的音乐能力——音乐听赏能力,甚至没有把这认为是自己的音乐能力。在这样的音乐能力话语体系下,在单一的音乐能力观的影响下,使类似的孩子抹杀了自己的音乐能力。事实上,音乐能力是一种近似本能的存在,是人社会化存在的重要条件(比如节奏感是协调劳动的基础),每个人都有音乐能力,尤其是听赏能力。
现实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前面提到的音乐院校招生专业考试,一般都会测试如下科目:乐理、视唱练耳、主项(声乐、西洋乐器、民族乐器等),这些测试项目着重考察的主要是依照乐谱表演的能力,而不是强调学生领悟音乐的文化能力。音乐院校的音乐教育中,还是更多强调欧洲古典音乐体系以来所认为的音乐能力,忽视自己民族音乐传统的学习。即使学习民乐的方式也采用了西方专业音乐教育的方式,很少有人参与到传统音乐传习的方式中来,这使传统的音乐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并逐渐消失。
社会音乐教育中,除了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之外,很多家长还为孩子选择了在校外音乐教育机构中学习吹、拉、弹、唱等音乐演奏技能,也反映了家长强调表演能力的音乐能力观。如今小区里面时常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艺术培训广告,大多居民小区都有音乐教室、钢琴小屋之类深入社区的音乐表演能力培养的机构。这些培训方式强化了将音乐表演能力作为音乐能力的思维倾向。
自古以来,音乐和人类的关系密切,音乐是每个人的生活组成部分。我们学习音乐并不是使每个人都成为演奏家、作曲家,而是真正享受到音乐的快乐,了解自己的音乐文化,使音乐成为自身生活的一部分。现在人们似乎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意识中还是过分强调了表演与创作音乐的能力,对听赏能力重视却不够。在我国古代就非常重视音乐听赏能力在音乐活动中的重要性,有“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孔子在齐国听赏韶乐后,迷醉于韶乐的魅力,以致三个月都吃不出肉的味道了,它强调的就是听赏音乐的能力。假如每个人都能意识到音乐能力不仅仅是表演、创作能力,还有听赏能力,那样大家将都可以参与到音乐活动中来,对音乐,尤其是民族音乐更多地聆听、认同、理解,则有助于重塑当代人的民族文化音乐底韵。
一个人的音乐能力主要包括演唱、演奏音乐的能力;分析音乐的能力;听赏音乐的能力。听赏音乐的能力是音乐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音乐的听赏能力创作了音乐本身,没有听赏音乐的存在,音乐活动也就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在评价人的音乐能力的时候,不能仅依赖其表演、创作的能力,而应该将听赏能力纳入到判断音乐能力的标准中来。其中,对自身文化中音乐的听赏能力更应得到强调。我国古代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它不单单告诉我们知音难觅的道理,它还提醒我们,听众是音乐存在的核心环节,如果没有了能够聆听欣赏音乐的人还谈何音乐呢?所以,“我们应该牢记,巴赫和贝多芬的存在,不但依靠诸多演奏者,同样要依靠有诸多鉴赏能力的观众……”。
在我国,长期在民间音乐传承体系中生存的民间艺人,世代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造就了他们可以不识乐谱仅凭听觉也能完成再现音乐作品的能力。他们在西肖尔等人的西方音乐测试评价体系下也许也会成为音乐的低能者,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他们的音乐能力。因此,判断音乐能力还应该将眼光放置到研究对象的文化中来考量的,我们既应当看到在自己的文化中音乐能力的表现,同时也要以他者的眼光去多角度的审视一个人的音乐能力,而不局限在单一、霸权化的西方音乐能力判断标准中。
然而我们当今的社会评价机制下,主流仍然是单一化的以西方音乐为中心的评价标准,这种单一化的评价体系会抹杀大多数人的音乐能力,带有很强的压迫性。强调每个人都可以发展自己的音乐能力,都可以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自己的音乐能力且不仅仅是创作表演能力,聆听、理解音乐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更重要。布莱金也提到:“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音乐共性,某些在音乐刺激下的共性反应是可能存在的。但这种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假设,而且尚未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中得到验证。迄今为止,仅有的共性看来只有一点,即各种人都具有某种‘音乐性的’行为。”
所以,能领悟自己音乐中的文化才是最根本的。
当今社会,对于音乐能力的价值判断主要基于音乐表演能力与创作能力,导致音乐从业者、音乐教育者、受教育者们判断一个人音乐能力全局性眼光的缺失。音乐的创作、表演、听赏是三位一体的,相互依赖不可或缺。判断音乐能力应该提倡多元化审视标准,表演能力、创作能力、听赏能力并重。大众音乐能力的培养更应该强调音乐听赏能力的提高。而判断一个人的音乐能力更须将其放置到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考量。每个人都是有音乐能力的,至少都能够欣赏、理解、认同并参与音乐活动,音乐应该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个“音乐”尤其要强调本民族文化中的音乐,借以提高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抵御欧洲中心的音乐文化霸权话语,重塑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