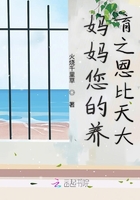幻象在中国文学里素来似乎很薄弱。新文学——新诗里尤其缺乏这种质素,所以读起来总是淡而寡味,而且有时野俗得不堪。《草儿》《冬夜》两诗集同有此病;今来查验《冬夜》。先从小的地方起,我们来看《冬夜》的用字何如。前面我已指出叠字法的例子很多;在那里从音节的一方面看来,滥用叠字便是重复,其结果便是单调的感效。在这里从幻想一方面看来,滥用叠字的罪过更大,——就是幻想自身的亏缺。魏莱(Arthur Wa1ey)讲中国文里形容词没有西文里用得精密;如形容天则曰“青天”,“蓝天”,“云天”,但从没有称为“凯旋”(triump hant)或“鞭于恐怖”(terror scourged)者,这种批评,《冬夜》也难脱逃。他那所用的字眼——形容词,状词——差不多还是旧文库里的那一套老存蓄。在这堆旧字眼里,叠字法究居大半;如“高山正苍苍,大野正茫茫”;“新鬼们呦呦的叫,故鬼们啾啾的哭”;“风来草拜声萧萧”;“华表巍巍没字碑”,等等,不计其数。这种空空疏疏模模糊糊的描写法使读者丝毫得不着一点具体的印象,当然是弱于幻想力的结果。斯宾塞同拉拔克(Lubbock)两人都讲重复的原则——即节奏——帮助造成了很“原始的”字。拉拔克并发现原始民族的文字中每一千字有三十八至一百七十字是叠音字,但欧洲的文字中每千字只有两字是的。这个统计正好证明欧洲文字的进化,不复依赖重叠抽象的声音去表示他们的意象,但他们的幻想之力能使他们以具体的意象自缀成字。中国文字里叠音字也极多,这正是他的缺点。新诗应该急起担负改良的责任。
《冬夜》里用字既已如上述之空疏庸俗,大体上也可想而知了。全集除极少数外,稍微有些淡薄的幻想的点缀,其余的恰好用作者自己的话表明——
“这间看看空着,
那间看看还是空着,
……
怎样的空虚无聊!”(一○八页)
最有趣的一个例是《送缉斋》的第三四行——
“行客们磨蚁般打旋,
等候着什么似的。”(五○页)
用打旋的磨蚁比月台上等车的熙熙攘攘的行客们,真是再妙没有了。但是底下连着一句“等候着什么似的,”那“什么”到底是什么呢,就想不出了。两截互相比照可以量出作者的“笔力”之所能到同所不能到之处了。
《冬夜》里见“笔力”——富于幻想的作品也有些。写景的如《春水船》里胡适教授所赏的一段,不必再引了。《绍兴西郭门头的半夜》的头几行径直是一截活动影片了——
“乌篷推起,我踞在船头上。
三里——五里—一
如画的女墙傍在眼前;
臃肿的山,那瘦怯的塔
也悄悄的各自移动。”(四六页)
同首末节里描写铁炉的一段也就惟妙惟肖了,——
“风炉抽动,蓬蓬地涌起一股火柱,
上下眩耀着四围。
酱赭的皮肉,蓝紫的筋和脉,
都在血黄色的芒角下赤裸裸地。
流铁红满了勺子,猛然间泻出;
银电的一溜,花筒也似的喷溅。
眩人的光呀!劳人的工呀!”(四八页)
还有《在路上的恐怖》中的这一段,也写得历历加画。——
“一盏黄蜡般的油灯,
射那灰尘扑落的方方格子。
她灯前做着活计,
红皴皴的脸映着侧面来的火光,
手很应节的来往。”(六三页)
有一处用笔较为轻淡,而其成效则可与《草儿》中写景最佳处抗衡。——
“落日恋着树梢,
羊缚在树边低着头颈吃草,
墩旁的人家赶那晚晴晾衣。”(一○九页)
其余的意象很好颇有征引的价值者,便是下面这些了。——
“……
也暂时温暖起‘儿时’的滋味,
依稀酒样的酽,睡样的甜。”(一一一页)
“或者傻小孩子的手,
把和生命一起来的铁链,
像粉条扯得寸断了,
抹一抹尊者的金脸。”(一一六页)
“锄头亲遍地母嘴,
刀头喝饱人间血!”(一九八页)
“……煨灶猫般的蜷着,
听风雨的眠儿歌,
催他迷迷胡胡向着一处。”(六二页)
上列的四个例在《冬夜》里都算特出的佳句;但是比起冰心女士的——
“听声声算命的锣儿。
敲破世人的命运。”
或郭沫若君的——
“弯弯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便又差远了。这两位诗人的话,不独意象奇警,而且思想隽远,耐人咀嚼。《冬夜》还有些写景写物的地方,能加以主观的渲染,所以显得生动得很。此即华茨活所谓“渗透物象的生命里去了,”——
“岸旁的丛草没消尽他的绿意,
明知道是一年最晚的容光了,
垂垂的快蘸着小河的脸。
树迎着风,草迎着风
他俩实在都老了,
尽是皮赖着。
不然——
晚秋也太憔悴啊!”(七二页)
但这里的意思和《风的话》里颇有些雷同,——
“白云粘在天上,
一片一团的嵌着堆着。
小河对他,
也板起灰色脸皮不声不响。
枝儿枯了,叶儿黄了
但他俩忘不了一年来的情意,
愿厮守老丑的光阴,
安安稳稳的挨在一起。”(二二页)
集中有最好的意象的句子,现在我差不多都举了。可惜这些在全集中只算是一个很微很微的分数。
恐怕《冬夜》所以缺少很有幻象的作品,是因为作者对于诗——艺术的根本观念的错误。作者的《诗的进化的还原论》内包括两个最紧要之点,民众化的艺术与为善的艺术。这篇文已经梁实秋君驳过了,我不必赘述,且限于篇幅也不能赘述。我现在只要将俞君的作品的缺憾指出来,并且证明这些缺憾确是作者的谬误的主张的必然的结果。《冬夜》自序里讲道:“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言语,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至于表现的……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的本意无关,我以为如要顾念到这些问题,就可根本上无意作诗,且亦无所谓诗了。”俞君把作诗看作这样容易,这样随便,难怪他作不出好诗来。鸠伯(Joubert)讲:“没有一个不能驰魂褫魄的东西能成为诗的,在一方面讲,Lyre是样有翅膀的乐器。”麦克孙姆(Hiram Maxim)讲:“作诗永远是一个创造庄严的动作。”诗本来是个抬高的东西,俞君反拼命地把他往下拉,拉到打铁的抬轿的一般程度。我并不看轻打铁抬轿的人格,但我确乎相信他们不是作好诗懂好诗的人。不独他们,便是科学家哲学家也同他们一样。诗是诗人作的,犹之乎铁是打铁的打的,轿是抬轿的抬的。惟其俞君要用打铁抬轿的身分眼光,依他们的程度去作诗,所以就闹出这一类的把戏来了,——
“怕疑心我是偷儿呢;
这也说不定有的。
但他们也太装幌子了!
老实说一句;
在您贵庙里,
我透熟的了,
可偷的有什么?
神像,房子,那地皮!”(一○七页)
“列车斗的寂然,
到那一站了?
我起来看看。
路灯上写着‘泊头’,
我知道,到的是泊头。
过了多少站,
泊头的经过又非一次,
我怎么独关心今天的泊头呢?”(二三四页)
“‘八毛钱一筐!’
卖梨者的呼声。
我渴极了,
却没有这八毛钱。
梨始终在筐子里,
现在也许还在筐子里,
但久已不关我了,
这是我这次过泊头,最遗恨的一件事。”(二三五页)
照这样看来,难怪作者讲:“我严正声明我做的不是诗。”新诗假若还受人攻击,受人贱视,定归这类的作品负责。《冬夜》里还有些零碎的句子,径直是村夫市侩的口吻,实在令人不堪——
“路边,小山似的起来,
是山吗?呸!
瓦砾堆满了的‘高墩墩’。”(一二六页)
“枯骨头,华表巍巍没字碑,
招什么?招个——呸!”(二○一页)
“去远了——
哙!回来罢!”(一五五页)
“来时拉纤,去时溜烟。”(一○九页)
同
“就难免‘蹩脚’样的拖泥带水。”(一○一页)
戴叔伦戴叔伦(732—789),唐代诗人。讲:“诗人之词,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作诗该当怎样雍容冲雅,“温柔敦厚”!我真不知道俞君怎么相信这种叫嚣粗俗之气便可入诗!难道这就是所谓“民众化”者吗?
五
《冬夜》里情感的质素也不是十分地丰富。热度是有的,但还没有到史狄芬生所谓“白热”者。集中最特出的一种情感是“人的热情”——对于人类的深挚的同情。《游皋亭山杂诗》第四首有一节很足以表现作者的胸怀——
“在这相对微笑的一瞬,
早拴上一根割不断的带子。
一切含蓄着的意思,
如电的透过了,
如水的融合了。
不再说我是谁,
不再问谁是你,
只深深觉着有一种不可言,不可说的人间之感!”(七七页)
集中表现最浓厚的“人间之感”的作品,当然是《无名的哀诗》——
“酒糟的鼻子,酒糟的脸,
抬着你同样的人,喘吁吁的走。”
只这“同样”两个字里含着多少的嫉愤,多少的悲哀!其次如《鹞鹰吹醒了的》也自缠绵悱恻,感人至深。这首诗很有些像易卜生的《傀儡之家》——
“……
哭够了,撇了跑。
不回头么,回头只说一句话:
‘几时若找着了人间的爱,
我张开手接你们俩啊!’”(一四五页)
比比这个——
“郝尔茂但是我却相信他。告诉我?
我们须变到怎样?——
娜拉须变到那步田地,使我们同居的生活可以算得真正的夫妻。再见罢。”
《哭声》比较前两首似乎差些。他着力处固是前两首所没有的,——
“说是白哟!
埋在灰炉下的又焦又黑。
让红眼睛的野狗来收拾,
刮刮地,衔了去,慢慢龈着吃,
咂着嘴舐那附骨的血,
衔不完的扔在瓦砾。”(一三二页)
但总觉得有些过火,令人不敢复读。韩愈的《元和圣德诗》里写刘受刑的一段至因这样受苏辙的批评。我想苏辙的批评极是,因为“丑”在艺术中固有相当的地位,但艺术的神技应能使“‘恐怖’穿上‘美’的一切的精致,同时又不失其要质。”
(Horror puts on all the daintiness of beauty,losing none of its essence)
如同薛雷的——
“Foodless Toads
Within voluptuous chambers panting crawled”
音节描写“高墩墩”上“披离着几十百根不青不黄的草,”将他比着“秃头上几簇稀稀剌剌的黄毛”也很妙。比比卜郎宁手技看——
“Well now,look at our villa!stuck like
The horn of a bull
Just on a mountain edge as bare
As the creatures skull
Save a mere shag of a bush
With hardly a leave to pull!”
倒是下面这几行写得极佳,可谓“哀而不伤”——
“高墩墩被裹在‘笑’的人间里,
一年的春风,一年的春草:
长了,又绿了一片了!
辨不出血沁过的根苗枝叶。”(一三二页)
这首诗还有一个弱点,——其实是《冬夜》全集的弱点——那就是拉的太长了。拉长了,纵有极热的情感也要冷下去了,更怕在读者方面,起了反响,渐生厌恶呢!这首诗里第二节从“颠狂似的……”以至“这诚然……”凡二十二行,实在可以完全删去。况且所拉长的地方都是些带哲学气味的教训,如最末的三行——
“我们原不解超人间的‘所以然’;
真感到的,
无非人间世的那些‘不得不’!”(一三六页)
像这种东西也是最容易减杀情感的。克慈讲:
“All charms fly
At the mere touch of philosophy”
近来新诗里寄怀赠别一类的作品太多。这确是旧文学遗传下来的恶习。文学本出于至性至情,也必要这样才好得来。寄怀赠别本也是出于朋友间离群索居的情感,但这类的作品在中国唐宋以后的文学界已经成了一种应酬的工具。甚至有时标题是首寄怀的诗,内容实在是一封家常细故的信。《东坡集》中最多这类作品。作诗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不可救药了。新文学界早就有了这种觉悟,但实际上讲来,我们中惯习的毒太深,这种毛病,犯的还是不少。我不知道《冬夜》的作者作他那几首送行的诗——《送金甫到纽约》《和你撒手》和《送缉斋》——是有深挚的“离恨”没有?倘若有了,这几首诗确是没有表现出来。《屡梦孟真作此寄之》是有情感的根据,但因拉的太长,所以也不能动人,魏莱在他的《百七十首中国诗序》里比较中国诗同西洋诗中的情感,讲得很有意思。他说西洋诗人是个恋人,中国诗人是个朋友:“他(中国诗人)只从朋友间找同情与智识的侣伴,”“他同他的妻子的关系是物质的。”我们历观古来诗人加苏武同李陵,李白同杜甫,白居易同元稹,皮日休同陆龟蒙等的作品,实有这种情形。大概古人朋友的关系既是这样,我们当然允许他们,什么寄怀赠别一类的作品,无妨多作,也自然会多作。他们已有那样的情感,又遇着那些生离死别的事,当然所发泄出的话没有不真挚的,没有不是好诗的。我很不相信杜甫的《梦李白》里这样的话,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是寻常的交情所能产出的。但是在现在我们这渐趋欧化的社会里,男女关系发达了,朋友间情感不会不减少的,所以我差不多要附和奈尔孙(William Allen Nelson)的意见,将朋友间的情感编入情操(sentiment)——第二等的情感——的范畴中。若照这样讲,朋友间的情感,以后在新诗中的地位,恐怕要降等了。《屡梦孟真作此寄之》中间的故事虽似同杜甫三夜频梦李白相仿佛,但这首诗同《梦李白》径直没有比例了。这虽因俞君的艺术不及杜甫,但根本上我恐怕两首诗所从发源的情感也大不相同罢!近来已出版的几部诗集里,这种作品似乎都不少(《草儿》里最多),而且除了康白情君的《送客黄浦》同郭沫若君的《新阳关三叠》之外,差不多都非好诗。所以我讲到这地方来,就不知不觉的说了这些闲话。
《冬夜》里其余的作品有咏花草的,如《菊》《芦》《腊梅和山荼》,有咏动物的,如《小伴》《黄鹄》《安静的绵羊》,有咏自然的,如《风的话》《潮歌》《风尘》《北京的又一个早春》等;有纪游的,如《冬夜之公园》《绍兴西郭门头的半夜》《如醉梦的踯躅》《孤山听雨》《游皋亭山杂诗》《忆游杂诗》《北归杂诗》;还有些不易分类的杂品。这些作品中有的带点很淡的情绪,有的比较浓一点;但都可包括在下面这几种类里,——讽刺,教训,哲理,玄想,博爱,感旧,怀古,思乡,还有一种可以叫做闲愁。这些情感加上前面所论的赠别,寄怀,都是第二等的情感或情操。奈尔孙讲:“情操”二字,“是用于较和柔的情感,同思想相连属的,由观念而发生的情感之上,以与热情比较为直接地倚赖于感觉的情感相对待”。他又讲“像友谊,爱家,爱国,爱人格,对于低等动物的仁慈的态度一类的情感,同别的寻常称为‘人本的’(humanitarian)之情感……这些都属于情操”。我们方才编汇《冬夜》的作品所分各种类,实不外奈尔孙所述的这几件。而且我尤信作者的人本主义是一种经过了理智的程序的结果,因为人本主义是新思潮的一部分,而新思潮当然是理智的觉悟。既然人本主义这样充满《冬夜》,我们便可以判定《冬夜》里大部分的情感是用理智的方法强造的,所以是第二流的情感。
我们不妨再把《冬夜》分析分析,看他有多大一部分是映射着新思潮的势力的。《无名的哀诗》《打铁》《绍兴西郭门头的半夜》《在路上的恐怖》是颂劳工的;《他们又来了》《哭声》是刺军阎的,《打铁》也可归这类;《可笑》是讽社会的;《草里的石碑和赑屃》和《所见》是嫉政府的压制的;《破晓》《最后的洪炉》《歧路之前》是鼓励奋斗的;《小伴》是催促觉悟的;《挽歌》《游皋亭山杂诗》中一部分是提倡人道主义的;至于《不知足的我们》更是新文化运动里边一幕的实录。大概统计这类的作品要占全集四分之一,其余还有些间接地带着新思潮的影响的不在此内。所以这样看来,《冬夜》在艺术界假若不算一个成功,至少他是一个时代的镜子,历史上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