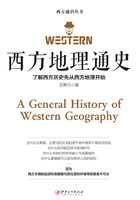对社团之外的人固然有此断然界限,但在罗马自由民社团分子之内,则几乎一切权利区分尽行扫除。我们已经提过,家庭中存在着明显区别,但这些区别在社团中却可以忽视;在家庭中,儿子是父亲的财产,但就以自由民的身份而言,他可以成为父亲的司令。自由民之间没有阶级特权:泰提人优于罗姆尼安人,而两者又优于鲁塞尔人,但这在法律权利上对他们的平等毫不影响。在那个时期,自由市民的骑兵,系用于前线在马背上甚至徒步单独作战,他们是精英分子,是最富裕的,是武装最好、训练最精良的人,因此自然比自由民步兵得到更高的评价;但这只是“事实上”的分别,而无疑,任何罗马贵族都得以加入罗马骑兵。从法律立场言之,自由民之间若有分别,只是由于体制上的次要分别使然。即使在外观上,诸份子的法律平等亦显然表明。社团的首领与社团份子,元老与非元老院之自由民,有服兵役之义务的成年人与未达此年龄者,固均有服装之别,但在公共场所,无论贵贱贫富均一律着简单白色羊毛宽外袍(toga)。自由民之间权利的完全平等。无疑源自印欧法制,但在意义的领会与体现之严格上则形成了此拉丁民族最特殊、最有影响力的特点之一。有一件事倒该在此一提,即拉丁移民并未发现该地有文化低落的早期居民须臣服于他们足下。这和印度种姓之产生的环境不同,也和帖撒利、斯巴达及希腊的贵族之产生的环境不同,甚至与日耳曼的阶级之分亦有其不同之背景。
国家经济当然由自由民负担。自由民最重要的功能是服军役;因为只有自由民有权利与义务参军。自由民亦同时是“战士团”(“战士”populus,与populari“破坏”和popa“屠夫”有字源关系)。在古老的祈祷书中,祈求战神马尔斯给予降福的,是“荷矛之战士”,国王在对他们致词时,则称他们为“矛士”。我们已经说过军“团”(legio)如何形成。在三分罗马社团中,一军团包括三百骑兵,由三名骑兵分队长分别率领;三千步兵,由三名步兵分队长分别率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若干轻装备者,尤其是弓箭手。一般言之,将军即国王本人;由于骑兵有特别指定之队长,因而国王可能只率领步兵,而步兵亦可能很早即是武装主力。除军役外,自由民还可能有其它负担,如平时与战时执行国王委派的任务、耕种国王田地、建筑公共工程等。城墙的建筑之艰辛在环墙的名称上留下了证据·名之为“重任”(mamia)。固定的直接税收是没有的,因为国家没有直接固定的支出。为社团服务不需支付报酬,因为军役、派定之工作和公众服务,一般言之皆无报酬;若为地区服务,或为个人服务,则该地区或该个人可提供酬佣。公共祭神所用之牲畜由法定税捐购买;公共比赛之负方,以比赛项目之价值向国家缴付“牛金”(以牛只为罚金而缴纳之)。文献中未曾见到自由民向国王缴纳之任何固定贡品,但居住于罗马的非自由民则显然要为所得之保护而向国王缴付金钱。此外,尚有其它几项流入王库者,即港口税和领地收益——尤其是草地贡和产物配额。前者来自公共草地的放牧,后者来自承租国有土地者。此外还有“牛金”所出产之物、充公之物,以及战争所得。在必要之际,有税物之征收,但此乃强迫税,时局改善后,需得偿还。此税究系加于全部居民——无论自由民与否——或只加于自由民,则无法确定,但后者之可能性较大。
金融由国王处断。不过,国产与国王私产(从有关罗马最后王室之广大土地所有权之报告看来,国王私产必定可观)并非相同。由武力取得之土地,特别被视为国有财产。在处理公有财产时,国王实际受到多大限制,已无可考证。不过可以确定,这一方面从未征询自由民之意见:而在分摊税捐与分配战利之土地时,则可能惯于征询元老院之意见。
然而,国王并非在需要税捐和服役时才想到自由民;在公共治理上,他们也参与其中。为此目的,社团中所有分子(妇女与未能持兵器之男童除外),也就是所有的“矛士”,都聚集在法庭中,举行“沟通”。国王为此目的,指定正式集会日期,每年两次,一为3月24日,一为5月24日;此外,国王若认为必需,可随时召集,次数不拘。然而,自由民之受召,并非为发言,而系为谛听;非为发问,而系为回答。除国王之外,集会中无人说话,如有,则为国王准予发言之自由者。而自由民之发言则只在单纯回答国王之间题,不讨论,不推理,不加条件,甚至亦不将问题分为部分。然则,罗马自由民社团,也像日耳曼,或原始印欧社团,构成了政治主权观念的真正最后基础。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主权是潜伏的,或说,只表现在自由民对国王的自动效忠上。为了获得自由民的效忠之誓,国王在从教士手上接得其就任礼的同时,向集会的族人询问,他们愿不愿做他真诚忠实的子民,愿不愿意照惯例承认他和他的仆人——即调查官(quastores)和使者(lictores)——这个问题得到否定回答的可能性几等于尢,正如世袭的帝王遭到拒绝效忠一样稀少。
正由于自由民系主权拥有者,因此他们在日常事务上不必插手;这两者在精神上是完全相合的。只要公共行为走在现行法制之内,则一国之内的主权便不能干预:治理政事的是法律,而非立法者。但若现在法制有所改变,或者,即使在某个特例上有所偏离,则主权必须出面干预。罗马体制中凡有此类事件出现,则自由民必定展示其权力。如果国王于死前未指定继承人,则共和国之指挥权与神圣保护权即落于自由民肩上,直至新主人选出为止。在这种状况下,自由民社团自动指定第一暂时王。然而,这种状况只是例外,非在必要情况之下,自由民是不会自动指定的;而由未受召即自动集合的自由民指定的暂时王因而亦被认做是并非完全有效者。通常,国家之主权则系由自由民与国王或暂时王合作施行之。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像合约一样,由口头的问与答来批准,因此,社团的一切主权行为均由国王——必须由国王亲身,而不能由他的替身(另一自己,alter ego)——向自由民提出问题,并由大多数自由民做肯定之回答来完成。因此,罗马法和我们一般以为的不一样,基本上它不是由君主向全社团分子所发的命令,而是由发言与回言在国家的基本力量之间达成的合约。从法律观点言之,凡有偏离通常法制体系之一致性的情况,都必须经过这样的立法性合约。就法律常规而言,任何人均可以把他的财产给予他所愿给的人,但必须立即转让。但若财产暂时仍归原主所有,待其死后再转让他人,在法律上则属不可能——除非社团允许;这个允许不仅在自由民集会的时候可以应允,而且在列队参战时亦可。这是遗嘱之源起。就法律常规言,自由民不能丧失或放弃其不可让渡之自由,因此,凡无家长者不得以儿子之身份受制于他人——除非社团给予许司。这乃是真the adrogatio。就法律常规而言,自由民之权利只能由生身得之,并永不能丧失——除非社团允许给予之,或允许其放弃。无疑,此等行为在最早期,假设无族人之判定,便不可能有效地发生。就法律常规而言,罪当死刑的犯人,一旦由国王或其代理者宣判,则必杀之无赦;因为国王只能审判,却不能原谅——除非被判的自由民恳求社团的悲悯,而法官又给予他求取原谅的机会。这乃是the provocatlo之始。这种原谅不是给予拒绝认错而被证实有罪的犯人的,而是坦白承认罪行而恳求减轻者的。就法律的常规而言,跟邻国所订之长期条约不可废除——除非自由民因该条约遭受伤害而同意将之废除。因之,在攻击战欲发动之际,当商询自由民之意见,但当其他国家破坏条约而本国发动防御战一时,以及缔结和平条约时,均不须商询自由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向族人之集会提出,而系向军队。总之,当国王欲做任何创新之举,对现行公共法有任何改变之时,都必须商询自由民。因此,自古代开始,立法权即属社团,而非属国王。在这类事例中,若无社团之合作,国王的行为便无法律效力;一个人,若只有国王宣布其为自由民,则他仍像以前一样为非自由民,此无效之行为只能产生“事实上”的结果,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结果。由此可见,自由民的集会初看之下虽然受到限制与阻碍,却自古以来即是罗马联邦之基本构成元素,自由民集会的特权与行为跟元老院的不同,并非以国王之随意意志为其最终之依据。
让我做一总结。在罗马人观念中,主权寓存于自由民之中;但只有在必需情况下始有权施用之,当偏离现行法规时,始有权会同国王施用之。王权如萨鲁斯特所说,既系绝对,又受法律限制(imperium legitimum);绝对,因国王之命令无论对错,初发之际必须服从;受限制,因命令若与已定之常规不合,又未为真正的主权所有者——即人民——所许可,则无长期合法效力。因此,罗马的最早宪法,就某种意义而言,正好是君主立宪政体的倒转。因为在后者的政府形式中,国王被认为国家全权之拥有者与荷载者,因之,譬如说宽赦只能由他发出,而国家的治理权则属于人民代表及向人民负责之行政单位。在罗马的体制中,人民所施行之功能颇为类似于英格兰:宽赦权——在英格兰,此为国王之特权——在罗马则为社团之特权;而政府的一般功能则完全落在国王身上。
如果我们追问国家与个体分子之间的关系,则我们会发现,罗马国既非仅止于疏松的防卫集合体,又非现代观念中的绝对权力国。确实,外在的限制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力仍小于对国王的限制力;但由于“合法权利”的观念本身即寓含着对权利的限制,因之国家的权力绝非无限。无疑,社团对自由民个体有权,例如分配其负担公务,惩罚触犯法律者;但任何法律,若惩罚、或意欲惩罚个人,而此个人所做之行为并未为人共认为可罚者,则即使在形式上无瑕可寻,罗马人仍认其为肆意而不公正之程序。在财产权与家庭权益方面,受到的限制更为严格。在罗马并不像里可加斯的警察组织一样,家庭可以绝对消失,并因而使社团扩大。罗马原始宪法最无可否认又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国家可以监禁或吊死自由民,但不可夺取他的儿子或田地,甚至不能向他课税。没有任何社团像罗马社团一样在其自己的范围内有如此的全权;但也没有任何社团像罗马社团,使清白的自由民可以过着近乎绝对安全的生活,免于其它自由民和国家的侵犯。
罗马社团就是以这些原则来治理自己;他们是自由的民族,了解服从之义务,摆脱了一切神秘观念,在法律上绝对平等,相互之间亦绝对平等,有明显的民族界限,而同时也慷慨地将门户向其它民族开放。这种体制既非制造,亦非借取,而系伴随罗马人自然成长。当然,它是以早期法制为基础——意大利的,“希腊——意大利”的和印欧的;但荷马的诗及泰西塔斯的Germania所描述的状况与罗马最早的社团组织之间,必然有连续的政治发展阶段。在希腊集会的欢呼和日耳曼集会的敲击盾牌中,有着社团主权的表现;但这跟罗马族人集会中有组织的裁判和有规章的意见宣布法还有很大的距离。再者,由于罗马国王的紫袍与象牙令牌必定是从希腊借取而来——而非从伊特拉斯坎人——则十二个开道小吏以及种种其它外在安排,很可能也系从外国取得。但罗马宪法的发展却断系属于罗马,至少也是属于拉提阿姆,其中借取的元素,小而无关紧要;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事实看出,即其所有的观念均一律由拉丁新创的字来表达。
罗马联邦自此以后赖以为基础的诸基本概念,实际上即由此宪法而出;因为,只要有罗马社团之处,其外形无论如何改变,必有如下之固定原则:——行政官有绝对指挥权;元老议会乃一国之最高权威;一切例外之决定均须主权人——换言之,即人民社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