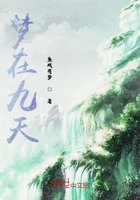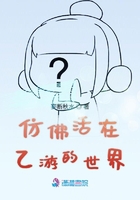正这时候,大门有响动,然后就听见:“妈!我回来了!”严振宇平淡的声音。
扇子姐姐一惊,立马站起来,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儿,紧张得光张嘴喘气,频频瞟着君婶,求救似的。
君婶拍着她的手,哄小孩儿的口气:“没事。没事。”说着迎出屋去,大声问:“怎末这点回来了?吃了吗?”
“这屋什么味?谁来了?”
扇子姐姐听见了,悬点没背过气,柳眉倒竖,银牙咬碎,就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严振宇已经踱到里屋门口,坦胸露怀,正扒衣服,朝里瞄了一眼,那表情是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冷冷瞥了眼扇子姐,转身走了。“妈,还有剩饭吗?”他在屋外问。
“那谁……小房儿……来了”君婶没底气的说,就跟饿了几天似的。
“看见了。您还没吃呢?”
“吃完了,我给你热饭。”
“甭管了……”
“瞅你那得性,甭挺着了,屋里,屋里,歇着去!”严振宇被君婶连推带搡轰进屋来。
他不知什么时候,套上个背心,顶一脑门子官司坐下了。扇子姐姐也没好气儿的坐下。我坐在地板上抱着毛毛玩儿,我们俩玩的正热闹,听严振宇叫我给他拿包烟。
我问:“搁哪了?”
他正在揭胳膊上晒爆的皮,有来到趣儿(注释:津津有味)的,眼皮也不抬,说:“衬衣兜里。”
我拿来给他,他说:“洋火。”
我找着洋火递给他,他又说:“报纸。”
我把报纸拍在桌上说:“要嘛?你一快说行吗?”
他叼着烟卷点烟,还拿眼横着我。抖灭了火柴,手夹着烟卷,腾出嘴来说“哪来这么多废话!”
“好好!我废话多。”看他累得臭死,还跟他争什么呀。
他又叼上烟卷,腾出手,不一会儿就用报纸折个纸盒儿。正好烟头上积了一大截儿烟灰儿,磕在纸盒儿里。
扇子姐叫我过去,她指着五斗橱上的烟碟,咬着我的耳朵,悄声说:“拿给他。”
我跑去拿着烟碟搁严振宇面前,说:“扇子姐让你用这个。”
严振宇撩起眼皮看着扇子姐,不识好歹:“你不拿走吗?”
“我想还是先放在这里好。用纸盒儿,容易着火。”扇子姐姐口气温和,可怎末听怎末都象教训人,当老师的派头。
“哪那么容易着火,别竟念丑。”(发“顺”音,二声。天津方言,说丧气话的意思)严振宇简直就是狗咬吕洞宾。
扇子姐姐要说点什么,见君婶端饭进来,就忍住了。严振宇强打精神闷头吃饭,那边两个女人窃窃私语,也不是顾意保密,就是怕吵着他,所以轻出气,低压声,搞得跟特务接头似的。
其实内容谁都听得见,说的就是严振宇,君婶唉声叹气的讲他吃苦受累,抱怨政府不长眼,骂当官的腐败,埋怨严振宇死性(倔强),没啥新鲜词。忽然想什么来,问:“振宇,你喝水吗?”
严振宇一愣,含糊的应了一声。君婶倒杯茶水,放在他跟前笑说:“你说怎么这么寸呢。林天雯进的中学就是扇子他们学校。”
严振宇端起茶杯,刚碰嘴唇,就愣住了,看看我又看看扇子姐,喝了口水,却不着急下咽,含在嘴里咋么滋味。
扇子姐姐笑道:“我也是刚知道,学校里发榜,我无意中看见新生里有个叫林天雯的,我还心想同名同姓呢。真没想到就是她。”向谁作解释的似的。
严振宇吃完收拾碗筷,君婶忙拦住说:“快放下。赶快歇着去。”
严振宇网着眉头,着急上火的说:“不行!您刷不干净。碗里还嘎巴着饭粒儿呢。这样我吃不下饭去。”毅然决然,奔厨房去了。
君婶恨得牙根痒痒,倒不生气说她刷碗不干净,而是心疼严振宇又拿他没治。冲扇子姐姐说:“累得都这得性了,还穷讲究。”
扇子姐提鼻子嗅了嗅,表情就跟见了鬼似的,轻声问:“什么味儿?您闻闻?”
我也仔细嗅嗅。“煤气!”扇子姐眼瞪得溜圆,确定的喊。
君婶大惊失色,一拍大腿,嚷道:“哎呦!我忘了!”
扇子姐姐三步并作两步,朝厨房冲去……我噌的跟上她……可是,我们不是火箭,连声音也追不上,只听见有人说:“你瞧我这,又忘带火柴了。振宇,你有火吗?” 段城他妈又来占便宜,自家有煤气炉不用,偏爱用人家的。
我们跑到厨房门口,就见严振宇正拿着打火机对着座水的炉眼打,“不要……”扇子姐锥心刺骨的尖叫。
蹦出几点火星儿……腾起巨大的火球,一声爆响,玻璃震碎,噼了啪啦零落的响声。然后听见锥心刺骨的惨叫,鬼哭狼嚎一样。
厨房里火蛇乱窜,浓烟滚滚,有人冲出来全身被火裹住,就地十八滚。扇子姐姐和我抱成一团儿,吓得直往楼梯上退.
“躲开!”扇子姐姐和我紧紧贴着墙,看老爸大吼,挥着扫帚冲下来,照着火人身上狂拍,还喊:“水!拿水!”
我松开扇子姐姐的手,冲到家里,拎个洗脸盆,接满水,端下来。扇子姐姐也醒过味儿来,在楼梯中间接过盆,递给我老爸,老爸泼水,楼下也有人往上递水,跟过泼水节似的,人身上的火灭了,看上去跟鬼一样,楼道里乌烟瘴气,谁也不认不出那是谁?
君婶原本让几个邻居拦腰抱住,哭不成腔,喊不成调,突然停住了,疯子一样挣脱出来,扑在地上,狂喜的嚷:“儿子——!”
段城听见扑过来,抓着严振宇拼命的摇晃,大声责问:“我妈呢?我妈呢?”
严振宇猛然推开他,跳起来跟掉魂儿了一样,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一头窜进厨房……
君婶半晌撕心裂肺的喊声:“回——来……”来字刚说一半,嘎然而止,她两眼一翻晕过去了。
不知谁喊了声:“救火呀!”大家才醒过来。我接茬拿脸盆接水,递给扇子姐姐,扇子姐又递给老爸。从楼下也有人源源不断的送水到二楼,几个大小伙子轮番往厨房里泼水。
或许过了很久,或许只是片刻间,严振宇背着段城他妈冲出来了,好几盆水,同时朝他们浇过去……
严振宇扔下背后的人,就地一滚,灭掉身上的火,跳起来直着眼,奔到君婶跟前,君婶早被老邻居摇醒,只是还犯糊涂,听见严振宇的声音,她才明白过来,憋了半晌,失声痛哭。
严振宇一直不停得念叨:“没事儿了。妈,没事了。阀门关上了。没事儿了。”声音平和,似乎真的没事儿了。咕咚一声,他一头栽倒。
段城他妈那边儿,也是一片哭丧声。
林天雷蹲下,手放在振宇鼻子底下试了试,说:“房同志,赶快叫车!”
扇子姐姐得令,末头跑下楼。
林天雷背起严振宇,老爸看着有点悬,不信任的问:“你行吗?”
林天雷没好气的道:“我不行!您来!”练过就是不一样,背着个大活人,不当回事,疾步走下楼梯,在胡同里一路小跑,汽车敞开着车门就停在前方。 段城他爸也背起老婆,拼命撵上我哥他们。
林天雷跟扇子姐一起,把严振宇小心翼翼放到车上,然后,扇子姐姐又帮忙把那两个胖子塞进车里。车门砰的关上,小轿车疯了似的,开野了。
正这时候,消防车队来了。
后来,我们到医院去看严振宇,看床头的卡片才知道,这个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直挺挺好象埃及木乃伊的东西,就是他严振宇。扇子姐姐却不甚担心,轻松的说:没什么大事儿。大夫说烧伤面积虽大,可烧伤程度轻。尽管这样,她也没敢让君婶去医院,怕她受刺激。
段城她妈,捡回条命,可她伤得不轻,面积不但大,还是深度烧伤,喘气系统也给呛出毛病。段家开始还对严振宇感恩戴德,后来,随着医药费呈火箭上天的态势急剧飙升,态度也如瀑布,飞流直下。最后良心喂狗,两口子一口咬定是严振宇故意纵火,扬言报案打官司。发狠要讹严振宇给他们出钱。段家还找君婶闹了几回,让邻居们劝开了,气得君婶,差点吐血。
扇子姐姐知道了,专派两个老妈子日夜陪着君婶。还请来消防局,警察局,几路人马,联合行动现场办公,最后拿出什么鉴定报道,结论就是大家公认的煤气遇明火。段家父子,立马没尿儿(注释:服软),在不敢乍刺儿。
胡同里又给镇了,纷纷传说,扇子姐姐手眼通天路子贼野!连官面上的人都能请动。就她?一个小丫头片子?没后戳,后戳不硬,成吗?邻居们无不感叹君苇没福儿,搞上这么好对象,可他却死了,还死得那么的不值!
不过,如今严振宇代替君苇养活他老娘,不知道有没有戏……大概也不行了,严振宇说不准烧得都没人样了,别说使美人计,恐怕只能拿出来装鬼吓唬人。说到严振宇,胡同里的婶子大娘很为他惋惜,不惋惜别的,就惋惜他出众的脸蛋和有名的好皮肤。
连林天雨也慨叹:“貌美如花,冷如冰霜的严振宇,以后恐怕只能上巴黎圣母院,吓死卡西莫多,接替他敲钟。”
看见段城他妈……心里咯噔一下,她的样子不是吓人,而是恶心。我再没去医院,因为不敢……不敢想象,更不敢再看拆掉纱布的严振宇。
慕容蓉来我家,带来一饭盒糖醋排骨,还有个包装的特别漂亮纸盒,上头印着英文。打开才知道是巧克力,盒子挺大,没装几个。那巧克力一个个穿金挂银窝在丝绒小圆槽儿里,金贵的让人一看,就没食欲。
就这慕容蓉还说:“少吃点,给你哥留几个。”
“还真是两口子!谁疼谁就甭说了。”我大口嚼着巧克力,翻白眼说。
她一指头戳在我脑门上,咬牙道:“该死的!小白眼儿狼!这是我爷爷刚打国外寄来的。我爸爸妈妈都没尝,就给你们拿来了。没想到,便宜到狗肚子里去了!”
她提防着我再拿,捂住盒子说:“不许吃了!你手里还有两个呢。别以为我没看见!”
我赶紧把手里两个巧克力,塞进嘴里,皮都没顾上剥,张开双手给她看,还含混着说:“没了……”
看她咬着嘴唇笑,我知道又可以吃两个,果然她说:“再赏你一个吧。”
我鼓着嘴,瞪眼直摇头,竖起两个手指,她白了我一眼,撇着嘴说:“好没出息!馋猫儿我见多了!就没见过你这么馋的!”拿出两个巧克力,拍到我手心里。我赶忙把嘴里那俩吐出来,再不吐就化了。
慕容蓉一脸恶心相,瞟着我,打鼻眼儿里直喷冷气。
我冲她翘下巴,朝天喷冷气说:“这就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没羞没臊,吃个贼饱!就你这号儿,给你搁节粮度荒那会儿,一打儿都饿死了!”
慕容蓉嘴都撇到后脑勺,气不打一处来,咂嘴道:“呵!还节粮度荒呢?那会有你了吗?比我还小五岁呢,跟我这儿瞎撇!”一副看了不上我的样子。
我朝她翻个白眼,小心剥开包巧克力的锡纸,把那个一坨屎状的东西,填嘴里了。
“林天雯。”她一本正经,满面愁容的问:“你哥今年中考都没参加,他这算怎么回事呀?”
“你都不知道!我哪敢知道?我比你小四岁呢,敢跟你这儿瞎撇?”我仰着脸,装傻的看着她。
她狠狠的剜我一眼,脑门上又挨了她一指禅,只听她咬牙切齿道:“该死的!你个齿音字,还敢顶嘴!“是”跟“四”都咬不准!还中学生呢!”
我捂着脑门,弄出一脸苦相,说:“你要成武林高手,我举双手赞成!可你也不能光拿我脑袋练吧!”
她打我胳膊一下,板着脸道:“别耍贫嘴了。说正格的呢!”
我咽口唾沫说:“这半年,给他算休学,明年他才中考呢,还有混头。”
“休学?他哪休学了?这半年,不是天天去学校么?虽然没正经上课!”慕容蓉嘟着小嘴,不解的问。
我笑道:“你花岗岩的脑袋?实着的高压水枪都打不出眼来?”
“什么意思?”她横眉竖目的问。
我说:“这还不就凭人一句话?”我学着林天雷的口气,摇头晃脑的说:“他们办主任梁老师跟学
校说:我哥上半年住院,拉下半学期的课,下半年也跟不上溜了。与其让他参加中考,给学校拉分儿,不如算他休学,再给他一次机会。”
“还有这是事儿?怪不得他说,留级没问题呢?”慕容蓉皱着眉头,恨狠的说。她忽的一笑:“他们班主任,对他还真不错。今年,他真要参加中考,那还不崴泥呀?”
我说:“那是!我哥说了,他跟梁老师,谁跟谁!铁着呢!”
慕容蓉撇嘴道:“小投机分子!”
“什么呀!他们梁老师都说: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懂吗你?”
慕容蓉脸上的表情,挺说不上来路,有气有恨,还带点儿瞧不起人的鄙视,咬着后曹牙挤出俩字儿:“德行!”
门外有响动,侧耳一听,是林天雷的脚步声,果然,他推门进来了。慕容蓉假装诧异道:“哎呦!大忙人,今天怎么有空儿回家呀!”
“我算准了你得来。”林天雷腆着脸凑近慕容,撩起她一撮儿头发,搁鼻子底下闻个没够,那倒霉眼神倍儿享受。
“没看出来!这儿还有个半仙儿。”慕容蓉闪身一甩马尾辫儿,辫梢儿正抽在林天雷脸上,敢情她练过神鞭。
“眼睛……我的眼睛……”林天雷当即捂着半边脸,痛不欲生的样子。慕容和我都吓一跳,急忙一边一个搀他坐下。
慕容的后悔心疼全写在脸上,俯身温柔的说:“手拿下来,让我看看……快别捂着了……”
林天雷一边装出随时要死的样子,一边英勇的说:没事没事。可他的另一只眼,正贼着慕容蓉的领口,往里瞟。
我白了他一眼,撂下他的胳膊,绕到椅子后头。忽然发现有个东西,支楞在他的裤兜口。我蔫不流丢,伸着两个指头,轻轻夹住,回手扣在手心里。躲在窗户底下,撕开包装纸,抖出来一瞧,心说:什么气球,还这么高级?可这气球颜色也忒素了,说白不白,说粉不粉。逮着气球,我就得吹爆了。所以习惯性的,搁嘴里,一运气,鼓起老大。不过形状有点怪,前头还有个尖,象奶头。
我正叼着气球满处找线绳儿,忽然听慕容蓉,以前所未有的恐怖语气问:“林天雯?你……你那是……那时干吗呢?!”
我小心翼翼掐紧气球嘴儿,腾出我自己的嘴说“吹气球。”
林天雷蓦地回头,也不装洋蒜了,直眉瞪眼问我:“哪来的?”
我一笑,得意的说:“没发现吧。刚从你裤兜儿里拿的。
慕容蓉瞬间变脸,咬着仇恨的嘴唇,瞪着林天雷,大义凛然,好像老电影里碰上叛徒的女公产党员。
林天雷仰望着她,嗤的一笑说:“你这是干嘛?我又不是反革命?绷着阶级斗争脸,吓着我!”我听出他底气不足,心虚得紧。
“那是怎么回事?”慕容蓉不为所动,保持阶级斗争的敏锐警惕,瞪圆眼睛指着我问,不是,应该说指着我手里的气球问。
林天雷挺英勇的把头一甩,瞅着慕容,笑的倍儿邪行,说:“不明白?非让我给你演示?”
慕容蓉先脸红,可马上就怒了,甩手给他一巴掌。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林天雷一惊,挨了打也不恼,反倒绕有兴趣的笑了,把另一边脸,腆给慕容蓉指着腮帮子说:“来!来!接着打。圣经上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应该把右脸也伸给他。怎么样?够有涵养吧。”
慕容蓉没再动手,半晌,才含泪问:“林天雷?你真是雷哥哥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一酸,眼睛发热。
林天雷眼也红了,狠心把眼泪逼回去,鼻子里冷笑一声,说:“你看呢?你真是看不出来?还是根本不想?”
慕容蓉怔怔的瞪着他,咬着嘴唇,蓦地掉头就走。林天雷僵直的坐椅子里,绷不住的露出苦相。我低头才看见气球撒气了,赶紧叼上,接着吹。
正这时,慕容蓉规矩的唤了声:“林叔叔。您回来了。”林天雷立马惊了,老爸就立在门口,脸色出奇的吓人。
他绕开慕容,直冲着我就过来了,吓得我腿肚子直哆嗦,把眼一闭,抽紧了骨头,预备挨打。就觉得一阵风扫过,嘴上的气球给摘走了。耳边狮子吼:“说!哪来的!”
我都快哭了,眼都不敢睁,指着我哥,战战兢兢的说:“从他口袋里拿的。”
“从您口袋拿的。”几乎是异口同声,林天雷平静的说。
我一睁眼,就见老爸抓起我哥的衣领,气急败坏的问:“你揣着这儿玩艺儿干吗?”
林天雷看着老爸笑了反问:“您揣着这儿玩艺儿干吗?”老爸不待他说完,大嘴巴就抽上了。
不想林天雷一偏身,从椅子上弹起来,闪开了。老爸用劲儿猛点儿,人栽倒椅子上,让椅子背把牙都给磕了。
林天雷说:“您一个鳏夫,还用得着这儿玩艺儿?”老爸爬起来,蓦地反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抡圆了一拳头凿在林天雷脸上。
我哥撞倒身后桌子,茶壶茶碗都摔了,稀了呼啦满地碎茬儿。他半天才站起来,舔了舔牙,啐了口血,昂起头从容不迫说:“爸!都是爷们。我理解!男人不流氓,生理不正常。男人不**,肯定有障碍。”他越说越来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