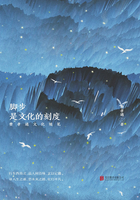吕映红骑车进入杜家村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人说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刚满十八岁的吕映红看上去确实像一朵花,她那亮丽好看的脸蛋配上造物主刻意雕琢的五官,西施见了也会艳羡。
初秋午后的天气依然很闷热,吕映红上身穿着那件在夏天最喜欢穿的白色T恤,下着一条乳黄色的细条绒筒裤,脚登一双黑色半高跟皮鞋。她的穿戴别说是在那闭塞落后小山村,就是在A市也绝对是一道难得一见的靓丽的风景。T恤衫和筒裤都是表姐给她买,当然,枊叶也有和姐姐款式一样的衣裤,只不过她的T恤衫的颜色是杏黄色,而裤子的颜色有点像荔枝初丹时的颜色。每年的暑假和寒假是姊妹俩最期待的时节,因为在北京上大学的表姐每次回来都会给姊妹俩捎件时兴的衣服或裤子。每当表姐把两件面料款式相同而颜色不同的衣裤摆在两人面前的时候,吕映红总是让妹妹先挑。吕映红喜欢素雅一点的服饰,柳叶却对色泽鲜明的衣饰情有独钟。吕映红所喜欢的颜色恰恰是妹妹不怎么喜欢的,因此姊妹俩从来没有因为要争同一颜色的衣裤红过脸。唯一一次姐姐让妹妹不开心的是去年暑假,表姐带回四件T恤衫,妹妹一下子看中了那火红色的。当时,吕映红抢下妹妹手中的T恤衫对妹妹说:“这一件是同学说好要的,其它三件你可以随便挑。”因为这件事,妹妹还生了她一天的气。
在大喇叭裤刚刚流行起来的乡村,吕映红的那件能让人显得秀挺的筒裤,即是县城里的俊男靓女身上也难得一见,她那优雅的身姿配上超时尚的衣着愈发显得风姿绰约。
在大街中央,吕映红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忙刹住车下来,礼貌地叫了一声“大婶”后向她打听起姜忆南来。中年妇女想必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新潮标致的美人,从上到下地打量了她一番才说:“俺村没有叫姜忆南的。”
“怎么没有?他今年高中才毕业。”
“噢!你是说姜有财吧?”
“对对,他以前是叫姜有财来,上高中后改名叫姜忆南了。”
“那你跟我来吧。”
在中年妇女的引导下,吕映红走进姜忆南家里,推开栅栏门一踏进姜忆南家里,吕映红立刻意识到:要说服他复读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是怎样一个家呢?
三间低矮的草房,历经风雨的侵袭早已变得破败不堪。砖线以下乱石勾砌的墙基已经露纹跋缝了,砖线以上石灰抹的墙皮有多处已经脱落,露出酥松的土墙胚,用秆草缮的房顶上面,满是半枯半荣的酸丁菜和大蔓草……
“姜忆南。”走到正间门口,吕映红朝屋里叫了一声没听到回应。
今天吃过午饭,母亲因儿子执意要到深圳打工,担心儿子一个人在外边无依无靠,到邻居家去问问有没有想外出打工的,若有的话也好跟儿子做个伴。妹妹到同学家写作业去了,家里只乘下姜忆南一个人,他躺在炕上不久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只从高考落榜后,姜忆南几乎天天晚上失眠,他一躺到炕上就会胡思乱想起来:如果回校复读一年考大学还是很有希望的,可是我怎么可以把生活的重担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如果不复读这一辈子也就完了……
吕映红更高一声的呼叫把姜忆南惊醒,他穿着背心和短裤从炕上爬起来,靸着三紧黑布鞋正要出来,瞥见是吕映红站在正间里,忙弯下腰提上鞋拽了拽绉巴巴的背心,走到正间望着吕映红问:“你怎么来了?”
“怎么,我不可以来吗?”
“看你说的,我欢迎还来不及呢!你先到东间坐会儿,我洗把脸。”他不想吕映红看到他睡眼醒松的样子。
趁姜忆南到天井洗脸的功夫,吕映红环顾了一下屋内的陈设,心中徒生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触。靠西壁有一个圆肚小口的泥烧水缸,紧靠北墙横只一张矮腿的长桌子,上面放着些锅碗瓢盆之类的生活用品,除此之外再就两个锅台,因为烟熏火燎的缘故,两个锅台的灶面都黑乎乎的不堪入自。
姜忆南洗完脸回来,把吕映红让进东间。这个贫穷的家庭相对值钱的物件都在这里,靠北墙横卧着一张红漆大柜,由于几十年没有刷漆的缘故,陈旧得连大柜正面上的漆花都看不分明了;靠东山墙临炕的地方,是一张方柜,当然方柜也是旧得老掉牙的,柜子上放着一把暖瓶,几只白瓷水杯;那张古董椅子,威严地坐在方柜的前边,扶手和椅背上所发出的暗亮的光泽,像是在向屋内暗淡无光的一切炫耀着自己身份的高贵。那黑栗色的椅子是真正的古董,那紫檀木质的椅子,扶手和椅背上都有雕刻的纹饰。据卖给姜忆南父亲椅子的主人说,那是打上豪分田地的时候,分到的地主家的椅子,八辈子也使不坏,不叫生活困难,是决不舍得卖的。当时,姜忆南父亲化五块钱卖回来的时候还被母亲抱怨了一回。
姜忆南把吕映红让坐在椅子上后给她倒了一杯白开水放在方柜上。姜忆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二十一个年头,打记事起到现在就不知道茶味是酸是甜还是苦。在这个贫穷的家庭,那开门七件事不得不缺失一个“茶”字。
“姜忆南,梅老师让我来劝你回校复读。”
“我不可能复读了。”
“为什么?”
“你看看我这个家。”
“我觉得你应该把眼光放这一点,你不考大学还有什么出路?难道你要像父辈们一样,一天到晚吃饭、干活、睡大觉吗?”
“哎!”姜忆南无可耐何地摇了一下头:“现实已不允许我有选择的余地。”
“我认为你只有考上大学,才是对母亲最好的报答。等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明白,可是……”姜忆南痛苦地摇了两下头。
“姜忆南,你别再固执了,”吕映红说完站起来接着说:“你忘了你在那首《即使》诗里写过的话了吗?”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着抑扬顿挫地吟颂道:即使,即使生命赋予我的,只有一片单调的灰色,我也决不,决不做温顺的羔羊,任霸王的屠刀,随意地,随意地宰割。即使,即使有一天,生活无情地抛弃了我,我也决不,决不抛弃生活!
吕映红吟颂完后略显激动地质问道:“忆南,你以前的远大志向呢?”
“以前,以前太狂妄太幼稚了。”姜忆南自嘲又绝望地说:“一个连饭都快吃不上的人还奢谈什么志向?”
“忆南,”吕映红双手拉住姜忆南的一只胳膊柔声地劝道:“为了你的前途,也为了我们的未来,再搏一次吧!啊?”说完轻摇了一下有点木然的姜忆南。
姜忆南望着吕映红那期待的目光,痛苦地摇了摇头语无论次地说:“前途?未来?我们的未来?未来,未来我们是不能同路的。”
姜忆南,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所表露出的抑郁的忧伤给人一种少年老成的印象。
吕映红失望地垂下双手,她透过他那忧戚绝望的目光,看见的是他内心无可耐何的忧伤,想着曾经才华横溢充满自信而又朝气蓬勃的姜忆南,如今变得如此消沉,心里一阵难过泪水立刻润湿了她美丽的双眼。姜忆南看到吕映红那满是泪水的双眼,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便端起了水杯。
吕映红上牙紧紧地咬住自己的下嘴唇,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没有让泪水流出来,趁姜忆南端水的功夫,迅速地抹拭掉眼里的泪水。
“喝口水吧。”姜忆南双手把水杯递向吕映红。
吕映红接过水杯只喝了一口,感觉有点烫觜又将水杯放回到方柜上。一时间两人都无话语,沉默了片刻,姜忆南无话找话地问:“吴婕在复读吗?”
“她一直在复读。前几天她说过不想复读了。她现在是二心不定,如果找到合适的工作她是不会复读了。”吕映红说完,叹了口气接着说:“咱班平时学习好的几乎都没考上,倒是平时学习一般的考上好几个。”
姜忆南听了吕映红的话,一份愧疚袭上心头,望着吕映红自责地说:“我知道是我害了你,请你原谅我。那时我是让鬼迷了心窍,一时难以自制。你能原谅我吗?”
“什么也别说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时候我要是听了吴婕的话接受你的爱,也许……算了,过去的事还是别提了。‘’说完,吕映红迟疑了一会又说:“我去看看雅鹃,最后顺便再去看看吴婕。”
尽管姜忆南的心里很想和她多相处一会儿,可是在仙子般的吕映红面前,他那难以洗脱的负罪感让他恨不得立刻从她的面前消失。所以,吕映红告辞的时候也没留她。
送走吕映红回到家中,姜忆南坐在那张紫檩坐椅上,想着吕映红“为了我们的未来,再搏一次吧!”喻意深刻的话,再想想自己破败的家院,自惭形秽地觉得今生是无缘与她了。忘了她吧!再不要在暗夜里想她,在破晓的曙光里,也不要再把她记起!可是他怎么能埋葬自己的记忆,此时此刻,吕映红那高挑的身姿,优雅的步态,流光溢彩的眸子,瀑布般垂泄的长发,甚至于她那纤纤的玉手,都像是在循环播放的视频,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眼前不停地播放……
杜雅鹃一个人在家复习功课,吕映红的造访让她疑肚从生:还有三天就开学了,她来干什呢?她心里虽然这么想却并没问她,而是以极其欢迎的姿态把她让坐在父母的睡房兼客厅的简易沙发上。杜雅鹃的父亲杜福贵是杜家村才上任两年多的党支部书记,之前是生产队的小队长。在中国,小队队长是小得连最小的芝麻官也算不上的村里的一方“长官”,但因掌控着村里集体的一部分财经大权,或多或少地将集体的部分财产变成自家的私有财产的事,在某些村官身上还是时有发生的。在那山高皇帝远县官也不管的杜家村,杜福贵同志在担任生产队长的那些年,通过给自己和家人多记公分的方式,为自己还是谋了一些福利的。所以杜雅鹃的经济条件,比姜忆南家那是要强老鼻子了。别的且不说,光是杜雅鹃家那五间大红瓦房,靠姜忆南和母亲“修理地球”要盖起那样的瓦房,恐怕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行。
吕映红把受梅老师之托劝说姜忆南复读的事跟杜雅鹃说过后,两人为姜忆南不回校复读感叹惋惜了一番,吕映红喝了两杯杜雅鹃给她冲的茉莉花茶,辞了杜雅鹃来到吴婕家里。
吴婕不在家,她母亲把吕映红让进屋里。吴婕的母亲六十多岁,生有三男一女,儿子们都已成家。同所有旧时代不幸的女人一样,小时候裹脚的成果让她不能大步地走路。寒暄过后吴婕的母亲去找女儿了。等老太太踮踮着双小脚走后,吕映红走进吴婕的闺房。吴婕的卧室里靠西山墙放着一张米黄色的写字台。写字台上左边有一台小小的台灯,右边挨墙整齐地码放着一摞书本,一本相册靠墙平放在写字台中央。吕映红走近写字台,拿起相册随意比翻看着,相册里多是男女同学的相片,她翻看到姜忆南的相片停了下来。相片中的姜忆南和他给她的那张一样,也是面带微笑。吕映红端端地望着姜忆南的相片,慢慢地陷入了回忆之中……
毕业之际,同学们都难舍难分。不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抛下世俗的偏见,相互交谈互赠相片和留言。全她收到了所有同学的相片,唯独缺少一张她最希望得到的姜忆南的相片。她知道是自己把他得罪了,因为只从她拒绝了他的求爱,再也没有看到过他温情的顾盼,他的那双能撩动少女情怀的黑亮的眼睛,在她的眼前已然变得暗淡无光。尽管)她曾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后悔过,也曾伤心地偷偷哭过,甚至一度还想过要接受他的爱,可因顾虑多多,她不敢也就没能用自己的爱去平抚他那颗受伤的心……
吕映红中断了对过往伤感的回忆,心事重重地刚重合上相册,突然一个问题在她的脑海中闪过:姜忆南给吴婕留了什么样的留言?因为很想知道,于是重新打开相册找到存放姜忆南相片的那一页,从塑料格套里拿出他的相片,看到相片背面“你是我忘不了的怀念,友谊地久天长!”留言的时候,她想到了姜忆南给自己的留言的同时,又想到他在给自己情书里的旦旦誓言:天长地久有时尽,爱你绵绵无绝期!
他把“爱你”变成了“此情”,也就是说他巳不再爱我了。她虽然如愿得到了她最想要的相片,终算是填补了耿耿于怀的缺憾,可是随之而来的疑问,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他把“爱你”改成“此情”是什么意思呢?曾经她一次次臆断过:他说的“此情绵锦无绝期”和“爱你绵绵无绝期”是一个意思吧!可是,今天姜忆南的“未来,未来我们是不能同路的”的话,让她对“此情”和“爱你”有了明析的定义,那就是:他不爱我了!忆南,你这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誓言,难道就因为我一时的“无情”吗?忆南,我那时的“无情”可能让你心伤、难过、绝望,所以你才用“此情”取代了“爱你”忆南,因为我的“无情”,你可以绝望,可是,难道我相片背后的留言,还不能催醒你那冬眠已久的爱?
就在吕映红拿着姜忆南的相片遐思迩想的时候,吴婕回来了。听到动静吕映红把相片放归原处,走到正间,看到一只脚迈过门坎的吴婕还没来得及开口,吴婕先笑语盈盈地说:“映红,才别几天,又想我了?”
“噢!想你了。”吕映红的脸上免强地掠过一抹笑,显然她还没有从刚才的情绪中走出来。
“怎么了映红?看样子不太高兴,是谁惹你生气了?”天生乐天派的吴婕笑着说完,拉她走进自己的房间,从写字下面拖出靠背椅,说:“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泡杯茶。”
一会功夫,吴婕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回来,屋里立刻弥漫起茉莉花的香气。吴婕看到倚在炕沿上的吕映红情绪有点底落,又跟她开起玩笑来:“是不是想姜忆南?”
“吴婕,以后你再别在我跟前提他了。”吕映红轻描淡写地说。
“怎么了?”
“可能是我伤他太狠了。”
“怎么,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今天,我受梅老师之托去了他家,他……哎!算了,不说他了。吴婕,我把你也不想继续复读的事跟梅老师说了。梅老师还是很希望你复读的。”
“其实,我也很留恋学校生活。”
“那就还读吧!”
“等看看再说吧。你去劝姜忆南,他怎么说。”
“他是百分之百不能复读。”
吴婕听了吕映红的话,又替姜忆南惋惜了一番……
接下来,吴婕又问了吕映红关于姜忆南的一些情况后,吕映红看看时间不早就辞了吴婕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