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忆南一走,马秀花就和女儿打扫起卫生来。她要把家收拾得干净整洁一些,以便给没进门的儿娘妇留下一个好印象。可是,因房屋破败,家中又没有像样的家具摆设,任她和女儿如何收拾还是不能称心如意。最后,马秀花只好安慰自己:等儿媳妇来了,告诉她明年就盖新房子。马秀花收拾停当,又把中午要做的饭菜准备好,坐到那把紫檀椅子上,光等儿子领媳妇来家了。
临近中午,姜忆南回到家中,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马秀花见儿子一个人回来,已经凉了半截的心一下子凉透了。
“咋才回来?她呢?”马秀花一脸不高兴地问儿子。
“她今天上班,没空。”
“那她哪日有空?”
“明天。”
“你们说定了?”马秀花的脸上又露出了欢喜的神色。姜忆南应了一声,走进西间屋里,马秀花跟进来问他:“她爹娘啥意思?”
“我没去她家。”
“噢,照你这么说,她爹娘还不知道。”
“行了,娘,你快别唠叨了。我累了,想歇会。”姜忆南有点不耐烦地说。
“那你歇着吧,娘去做饭。”马秀花说完,掀起门帘走了出去。
姜忆南走到桌子跟前,看到自己昨晚看的那本厚厚的《普希金抒情诗集》,脑海里随即响起普希金对于爱情的定又:一种爱情是平淡生活的快乐;一种爱情是对心灵的折磨。他在心里默吟了两遍普希金的诗句,继而在心里暗问自己:你的爱情属于那一种呢?他思来想去,觉得自己不曾有过爱情,至于自已对吕映红的爱,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罢了。可是,很快他又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她要是不爱自己,为什么要对自己说我的“生命中一刻不能没有你”呢?
姜忆南思来想去,那相思的苦痛催逼着他在心里不停地告戒自己:忘了吧,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吧!再不要在暗夜里想她,也别希望在黎明的曙光到来前,她会走进你的梦里!可是,姜忆南越是想把吕映红忘记,吕映红越是在他的脑际不停地闪现,如痴如梦的姜忆南,心里念道着吕映红的名字,随后在心里默念起一串伤感的诗句:
为了短暂的欢聚,
为了遥远的会期,
我回到了盼望已久的天地!
可是,你在哪里?
相思的苦痛加上难舍的别离,
我真想把你忘记!
忘记,忘记,忘记吧!
让我们一起忘记,
忘记那断肠的痛苦回忆!
可我知道,我知道
自己欺骗不了自己,
如果真有一天,
我能停止想你,
那定是我丧失了全部的记忆!
这些由心而发的诗句,催生了他的眼泪,姜忆南那抑郁忧伤的脸上,一经泪水的流过,看上去给人一种凄楚得不凄楚能哀伤……
当夜,大雪纷飞,第二天仍然下个不停。吃早饭的时候,马秀花不无担心地问儿子:“雪这么大,她还能来吗?”
“谁知道呢?”姜忆南也拿不准相隔十多里路的吴婕还会不会来。
“早叫你领她来家,你不听,今日拖明日的,这不,拖到个好天气!下这么大的雪,八成是来不了了。”马秀花抱怨过儿子,见儿子一脸愁容的样子,又说:“你看看你,一天价愁眉苦脸的,哪像有个对象的样子!你跟娘说实话,到底有没有那回事?要是没有的话,现在说雅鹃还来的及。”
“哥,”姜婷婷插嘴说:“雅鹃姐多好,她还不嫌咱家穷,你为什么就不喜欢她呢?”
“吃你的饭吧!哥的事不用你管。”
“哼!真是……”姜婷婷的下话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知为什么,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取而代之的是将筷子往桌上一拍,离开了饭桌。当姜婷婷拎着书包走到正间门口的时候,被母亲喊住叮嘱一她:“今天早点回来,万一你嫂子来了,好回来帮我烧火”。因为家穷生不起炉子,怕冷的婷婷整个寒假,除了吃饭和睡觉在家中,其它时间大都在生煤炉子的同学家度过。姜忆南把手里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也离开了饭桌。早饭不欢而散。马秀花收拾停当,思前想后,觉得儿子说的对象八成够呛,摘下围裙也急急火火地离开了家。她要去二斤糖家,去求告二斤糖先别把雅鹃介绍给别人。
姜忆南把天井里新下的积雪清扫了一遍,抬头看一眼漫天的雪花,心里想过吴婕一般不会来了后,一脸愁容地走回屋内,于一片死一样的沉寂中站了一会,耳边又响起“你为什么离我而去”的悲歌,那凄怨的旋律引发起他心中无限的感慨,一下子似有千言万语要对吕映红说。于是,姜忆南坐到桌子跟前,拿起钢笔,铺开信笺,不加思索地就给吕映红写起信来——三年来,他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向吕映红表达他的爱:
映红,在别后三年的今天,我坐在低矮昏暗的茅屋里给你写信。虽然,我知道你不会看到我写的信,可我还是要写。因为,每当我痛苦思念的时候,只有把对你的思念之情写下来,我的心里才会好受一点。三年来,我弄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如此……怎么说呢?薄情寡义?可我知道你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当我怀着无法被解的疑问回到家乡,想找你问个明白的时候,我却听到了你移情别恋的消息。这一消息像晴天霹雷一样,一下子把我打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
映红,你还记得三年前那难舍难离的场面吗?那时候,我以为那只是我们短暂的分离,哪会想成是相会无期的别离!谈到别离,我又想到了写给你的《告别》里的诗句;告别流淌的小河……可是,我的痴心留下的爱情已是无处安居!映红,我要问你:为什么你的心弦,突然凝绝了《爱之梦》的青春旋律?
映红啊,映红,我爱你!我痴情的呼唤,你可曾听见?我那布满泪迹的脸,你可曾看见?记得十八岁那年,我在日记里写下过这样的“真理”:眼泪是女人的专利!可为什么,为什么我却时常泪流满面?
映红啊,映红,你不会知道,在异乡,在那寂寞的军营里。每天早晨,当我拉起窗帘的时候,滑轮的流声里总是杂糅着你的乡音。而今,回到故乡的痴迷情人,为什么却听不到你的声音?
姜忆南写到这里,因为太过激动,他的手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夺眶而出的泪水一滴滴地滴落在信笺上。接下来,姜忆南已不知再写什么是好,放下笔,双手托着嘴巴,一任凭泪水不停地流淌……不知是过了多久,当姜忆南止住了泪流,却又低声地吟唱起那令人心碎的悲歌:你为什么离我而去……
姜忆南唱完一段,第二段刚开了一个头便唱不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哽咽之声,伤心了一阵后,他又像痴了一般接着和泪低唱道:你为什么离我而去?你曾说过生命中一刻不能没有我,可为什么却要把我无情的抛弃?啊!美丽的你,你在哪里?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我怎么才能停止一次次地想你?啊!美丽的你,你在哪里?
姜忆南唱到最后,唱得有气无力泪如泉涌的时候,一只纤细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头,他惊愕地扭回头来,看见满身是雪的吴婕站在身后,忙惊慌失措地站起来,一边用衣袖擦拭着脸上的泪水,一边羞惭地自嘲道:“你看我多脆弱,多没出息。”说完,见吴婕一言不发,含泪望着自己,又说:“你听见我的歌唱了吗?”
吴婕轻轻地点了点头,眼里盈含的泪水随之流淌下来。吴婕是在姜忆南唱歌的时候走进来的,他那哀怨的歌声所要表达的那种无奈和悲伤的情绪,也只有吴婕能够理解。
“你看你,下这么大的雪,就不要来了。”姜忆南顾不得擦净脸上的泪水,边说边给吴婕拍打着身上的雪花。
“我答应了你,怎么可以不来。”吴婕说着,先将装着皮鞋的布提袋放到炕上,接着脱下月白色的风衣,抖了抖衣服上的雪,搭放在椅背上,泪眼迷离地看看姜忆南,柔柔地说:“忆南,我来不只是为了扮演一下你的未婚妻,更主要的目的是来看看你。你住不几天又要走了,这一别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看见。”
“吴婕,你别难过。我知道曾经伤害过你,请你原谅我吧!”
姜忆南的话音刚落,吴婕扑进他的怀里,一边捶打着他,一边抱怨:“你们早就分手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吴婕,”姜忆南扶着她的肩头,说:“因为我爱她爱得太深,除了她,我心里已容不下别人了。”
吴婕听了姜忆南的话,愈加伤心了,竟呜呜呜地哭出声来。姜忆南扳着她的双肩,慢慢地把她从身上推开,然后腾出一只手来,一边给她擦着眼泪,一边安慰道:“吴婕,别再伤心了,一切都是定数。你对我的爱,我知道。可是,我们是没有结果的,就像我和映红一样。”姜忆南见她依旧流泪不止,又说:“吴婕,别哭了,我母亲不定什么时间就回来了。”吴婕终于止住了伤悲,开始用手背抹拭泪水。姜忆南去浸了一块热毛巾给她,自己也趁机洗了洗脸。吴婕擦完脸,把毛巾递给姜忆南,说:“忆南,你别痴了。一个对爱不专的人,值得你如此用情吗?”
“我想我今生今世是忘不了她了。”
“唉!映红太傻了,居然不知道珍惜这世间难得的真爱。”吴婕说完,随手拿起姜忆南刚写的信看了看,继而问道:“这是写给映红的信吗?”看到姜忆南点了点头,又问:“我可以看看吗?”
“我怕你看了后又要伤心。”
吴婕得到了姜忆南的默许,便低默默地看起来,看着看着禁不住又伤感起来,泪水又不知不觉地流淌出了。等她看完信,姜忆南重又浸了毛巾给她,她接过擦完脸,在递还毛巾的时候说:“忆南,我替你把这封信交给映红吧!好让她知道你是多么的爱她。”
“算了吧,她既然另有所爱了,我不想再去打扰她了。”
“你真是痴得可以,人世间不想竟有你这般痴情的人。”吴婕说完,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又说了声我先换下鞋来。说完,她坐下来,脱了系带的棉布鞋换上了黑色的半高跟皮鞋。
姜忆南听了吴婕的话,为了缓和一下伤感压抑的气氛,强作欢颜地笑了笑,说:“吴婕,别再谈我和映红的事了,谈谈你和张海涛吧!什么时间能吃到你们的喜糖?”
“我们还没打算呢!对了,我还是想再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认为我们合适吗?上学的时候,你们男生都说他小气,我最讨厌小气的人了,可在我面前,他并不显得小气,也不知他是不是装的。”
“我对他不太了解。上学的时候,我们关系不太好,这你也知道。不过,现在他成了你的恋人,我也会把他当朋友看待的。我劝你,不要管别人的看法,只要你觉得他好就够了。”
“唉!我也不知道他对我能好到什么时候。现在看来,他对我是不错。人人都说婚姻里爱情的坟墓,谁知道结婚以后呢?”
“谁也不能预知将来的事情,只能好好地把握现在。”
是的,将来的事是很难预料的!在吴婕看过姜忆南那封“错寄”的信后,她已认定他和吕映红是蜜不可分的一对了,怎么也没料到会是现在的结局;再如,吴婕曾在心里发誓婚前决不把贞操给人,可是,在与张海涛卿卿我我的缠绵过程中,她却没能守住自己的防线。她若预先有知,决不会和张海涛恋爱,更不会轻易地被他攻破防线。现在,她面对曾经深爱过的姜忆南,失去了贞操的她,也只有伤心和懊悔的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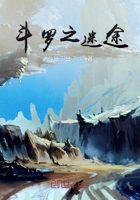


![骑士传奇[图说天下.世界历史系列]](https://i.dudushu.com/images/book/2019/10/08/0922180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