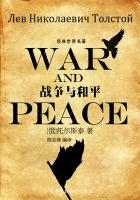一些人会认为所有的外国女人都是唾手可得的,但是熟悉可以产生尊重,大多外国陪酒女郎都承认常客的举止是最好的。
——尼古拉斯·伯恩奥夫,《粉红武士:当代日本的爱、婚姻和性》
大多数陪酒女郎酒吧对新人都有两个星期的试用期,在此期间,她只要简单地给第一次来的客人或是其他陪酒女郎的客人坐陪而已。如果一个陪酒女郎在两个星期的试用期后还没有赢得一些常客的话,她就会被开除或是被大量减薪。也就是说,这项工作的难度不在于看起来漂亮,会服侍客人喝酒和静静地坐着,而是在于吸引回头客。关于这一点,每个工作的女孩都有不同的策略。
就我个人而言,我过去常常在六点半左右——大多数上班族都已经结束工作——开始制订晚上的喝酒计划。我拿着手机坐在房间的小桌子前,旁边放着一堆名片和一杯加冰的纯伏特加。伏特加的作用是令我可以忍受打电话给每个男人——曾经给过我名片的男人——邀请他们晚上来“皇宫”。
有时候,我打电话过去,有些男人已经记不得我是谁了,就像我也记不得他们是谁一样。但在其余的时间里,他们听到我的声音会非常兴奋,并且对我的邀请感到高兴。但与此同时,我必须打大约二十通电话才能说服一位客人来“皇宫”找我。因为陪酒女郎酒吧的消费是天价,所以通常情况下,陪酒女郎必须自己去建立关系。但是大多数像我们这么年轻和新式的女人并不习惯主动邀请男人出来约会。于是伏特加就成为带给我信心的液体。
然而在周日,“皇宫”唯一歇业的一天,我的手机总是不停地响起。而我也得不断地拒绝这些来自中年男子的吃饭邀请——这些男人差不多正好就是在我工作的晚上拒绝接听我的电话的人。在他们的妄想中,我们好像真的在约会,他们真的认为我会不计报酬地跟他们出去。
一个周日早晨,我和林赛正坐着厨房里吃早餐,她的手机响了。当她挂了电话后,林赛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刚才是一个叫做井川的“皇宫”客人打来的电话。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打断了她。
“你好?”是个男人的声音,说着一口蹩脚的英语。
“喂?”我说道。
“我是井川。”
“谁?”
“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上星期在‘皇宫’见过面的。我们玩得很开心。你真是非常、非常可爱。”
“非常感谢。井川先生,你今天怎么样啊?”林赛大声笑出声来,不得不离开厨房。
“我非常好。你愿意今天和我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吗?”他问道。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我必须打扫房间。”我不假思索地说。
“好吧,没问题,下次见啦!”我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他就把电话挂了——可能是忙着打另一通电话去了。
这是个困难的过程,但是一旦你得到了一位常客,他就好像是属于你的。安藤是我的第一位常客,他每次来“皇宫”,花费的钱中总会有一部分是给我的。即使他从除我以外的女孩手里买酒喝,他的支票上面也会写着我的名字“黛西”。
我们必须假装与客人有关系或是假装爱上他们,以此来吸引常客。虽然我接受这份工作是因为我认为只需要在晚上工作就可以了,但结果是我不得不在空余时间里接听客人的电话,还要假装关心他们所说的内容。这种感觉太怪异了,仿佛在与成年男子玩假扮游戏。
在我第一次签约做陪酒女郎时,对于这个职业类型的很多方面我都没有认识清楚。大多数陪酒女郎酒吧的客人都会持续光顾同一间酒吧,因为他们在特定的女孩身上有特别的兴趣,而女孩们的工作完全就是让客人更经常惠顾。虽然所有的陪酒女郎都必须有不少常客,但是我们完全要自己负责安排时间表,注意不要让自己的常客在一个晚上同时出现。
如果意外发生了这种情况(一个陪酒女郎的几个常客同时光临),这位女郎不仅有丢掉客人的危险,而且会成为其他女郎的憎恶目标。因为显而易见,这位客人喜欢的陪酒女郎正在忙着招待另一位客人,你却不得不帮忙招待这位客人,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吗?
在极少的情况下,陪酒女郎会逐渐喜欢上她的某位常客,有时是因为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特别是如果这位客人还是位尊重陪酒女郎的绅士的话。实际上,陪酒女郎一直是客人柏拉图式的女朋友,她极有可能会迷失在这种礼节式的交往里,忘记年龄差距。同时,沉醉其中往往会模糊表演天分和真诚感情之间的界限。
虽然我经常事后重新审视自己的感情,但是我可以发誓,对于一位特别的常客,我真心地享受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遇到秀夫,时间已经很晚了,每个人都有些醉意。在他之前我已经招待了两位客人了。第一位客人是一个秃头的整形外科医生,他是一个人来的,我们酒过三巡之后,他示意“竹竿”让另一位女孩替换我。随后,我又给一个来这儿为他们经理庆生的公司坐陪。当派对结束后,每个男人都被一两位陪酒女郎护送着出门。当我们看着他们走进电梯时,我们微笑着向他们挥手,飞吻告别。可是电梯们刚一关上,我们虚情假意的笑容就立刻机械般地消失了,我们走回俱乐部,重新等待。
秀夫是一个体格魁梧的圆脸男人,坐在两位同事之间。当我被“竹竿”带到他身边时,他从头到脚地把我仔细打量了一遍,刚开始,我认为他很恐怖,但是像一位真正的日本人一样,我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感情。
我忘了我们聊了些什么,但是我肯定是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因为一个小时后他的同事回家了,而我们两个还在桌子旁紧挨地坐着,勾肩搭背,就好像时间还很早,而他也还很年轻一样。我们都醉得太厉害了,以至于都认为我们应该在卡拉OK机上点唱那首皇后合唱团的《波希米亚狂想曲》——当天晚上那首歌被无数不合格的歌手唱滥了。
我们唱完后,掌声雷动——来自许多漂亮姑娘们的掌声,她们的工作就是为我们鼓掌。秀夫去了盥洗室,德斯蒂妮妈妈利用这个机会走到我的桌子旁,递给我一条热毛巾,秀夫回来时我要例行公事地把毛巾呈给他。
“我一直在观察你们俩。”她凝视着我。
“不好意思,唱得那么难听。”在她开始批评我之前,我试着表达歉意。
“不,那不重要,”她说道,“他喝得够醉了,无论怎样都会认为你们俩唱得很好。”
“现在听我说,”在停顿了一下后妈妈桑坚定地说,“当他从盥洗室出来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要求他明晚和你约会。你们两个可以八点钟在俱乐部前碰面,出去吃个晚饭,然后十点整再回到这里。你今晚回家之前,我会向你说明其他要做的事情。”
既然我有了客人,妈妈桑对我就更加关心了。
像很多客人一样,秀夫在盥洗室待了很长时间。当他回来的时候,我完全按照德斯蒂妮妈妈的吩咐做事,因为我知道她一直在观察我们。我不知道妈妈桑是怎样做到的,但是她果然是正确的,秀夫根本无法拒绝我关于约会的请求。
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内疚,我好像是在利用这个醉酒的男人。然而同时,我心里又充满着怪异且无止尽的渴望——我想去取悦妈妈桑。我心里暗暗地想,德斯蒂妮真是太了解男人了,但是她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用来做一些“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