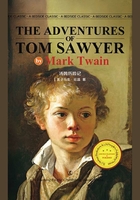并非苏树东是百事通,黑皮也不是道上人所周知的大人物,他在渝州混得不错,但还不是大哥,他的大哥是坤哥。苏树东知道黑皮是因为他好赌,三年前他可是白云湖景区最受欢迎的超级VIP客人之一,短短几个月就给赌场奉送了两三千万的利润,以至于赌王为了奖励他的杰出贡献,专门指示在晚上生意最好的时候,在大厅最热闹的一张台子,送一靴水钱给他吃。这个人虽然输得多,但没有辜负渝州人耿直的名声,从头到尾都没有欠过债、耍过赖和横,每次都是带现金来玩,输光走路,偶尔向苏树东他们借点高利贷,过两天也如数归还,这证明了黑皮的实力和为人,也证明了渝州大哥们的富裕,一个大哥手下的头目,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输掉这样一笔钱。出于对借款的负责,当时苏树东利用赌王的资源,对黑皮底细做过详细的调查,所以他非常了解这位渝州的黑道凶徒,整个晚上他都在考虑,最后,他还是决定向伍明询问,虽然有些冒失。
伍明沉吟着,他不是觉得丢局二的脸,而是他不太喜欢苏树东。出于一种直觉,他觉得苏树东充满危险。但是突然间,他决定告诉苏树东。因为苏树东脸上毫不掩饰地写着讨好局二的意图,他索性卖个乖,如果苏树东真想去碰这颗硬钉子,他乐于旁观。
这几年随着三峡工程的进行,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三峡成了盗卖文物的热地,渝州的大哥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立刻霸占了这波淘宝热的供与销,渝州一位大哥甚至投资一个多亿专门修建了古玩一条街。而自以为功成名就的局二像张宪一样,这些年开始关注这些附庸风雅的事情,他有这个闲钱,这也非常适合他现在的身份和心情。他从黑皮手中买了一樽青铜鼎,过程很曲折,辗转了不少人,还有一些专家鉴定过,但结局很简单,这是一个赝品。同时,这似乎也证明了一个永恒道理,没有人会因为害怕而放弃对于金钱的渴望,骗子们明知道局二的身份,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贪欲,而且,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局二对于自己名声的自信。局二亲自给黑皮打电话,无论是对方故意设局,找的托儿,还是黑皮也被蒙在鼓中,他要黑皮给一个说法。
或者是黑皮心中有鬼,或者年轻气盛,认为局二的长手伸不到渝州,没等局二把话说完,黑皮在电话里直接封口,根本不买账。刚才局二正在向伍明交代,他必须作出反击,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位大哥最重要的尊严。
“伍哥,你先等我两天,我去了解一下,如果这件事真是黑皮不对,我试着劝他一下,如果他能够服软,向二叔道歉,我们可以考虑接受他赔钱。”苏树东沉思半晌,客气地建议说。
“好吧,你去试试。”伍明淡淡一笑。
第二天中午,一辆普桑、一辆马自达商务车开进渝北区一家不起眼的宾馆,车上下来一群穿着T恤、短裤、旅游鞋的外地人,个个年轻健壮,沉默中带着凶狠,这群人就是苏树东精心挑选的战斗队伍,阴四爷,坦克,丁丁,任晓东和任晓东团伙的核心骨干。苏树东本来不想让阴四爷参与,他怕这个喜欢惹是生非的家伙节外生枝,但不知道为什么,又觉得有阴四爷在一起心中踏实。两辆车都套的渝州牌照,当然是假的,宾馆登记的身份证也不是真的。
半个小时后,一个剪着平头,矮胖的年轻人敲开苏树东的房间,他看着苏树东和阴四爷,试探着问:“东哥?”
苏树东迎上去:“我是,你是憨子?”
年轻人点点头,他和阴四爷坐到沙发上,苏树东坐到他们对面的床上。憨子一副渝州人的招牌表情,拍着胸脯说:“我是唐哥的朋友,东哥是唐哥的大哥,有什么事尽管说,能帮上的,绝不拉稀摆带。”
苏树东从手包中拿出一叠钱递过去:“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一点小意思,请憨子兄弟喝杯茶。”
憨子没有客气,接过去放在上衣口袋:“谢谢东哥。”
苏树东点头:“那我就直接……”阴四爷阴阳怪气地插了进来:“有人摸了老虎屁股,而且摸完了没给钱。”
憨子摸不清阴四爷的身份,但是看见他在苏树东面前大大咧咧的样子,小心问:“哪个?”
阴四爷盯着他,露出恶狠狠的表情:“黑皮。”
憨子从口袋中摸出移动电话,站起身,“东哥,我先打个电话。”往门外走去。
十分钟后,正自愕然的苏树东和阴四爷接到了唐松惶恐的电话:“刚才憨子给我打电话,说他不便介入这件事。那五千块钱他放在吧台了。他也说了,今天的事,他绝不跟任何人说。”
苏树东震惊异常,阴四爷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这个臭蟑螂,他交的都是些什么狗屁朋友!这娃说不定就是黑皮的人,这倒好,自己送上门去了。”
苏树东没有说话,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愤怒,开始思考现在该如何行动。阴四爷的怀疑肯定有道理,憨子说不定跟黑皮有关系,那么他刚才给唐松打电话就可能是麻痹他们。但是,进一步想,如果憨子真是黑皮的人,他准备立刻通知黑皮对付他们的话,他完全可以继续跟他们敷衍下去,所以,憨子应该不是黑皮的人。虽然如此,苏树东还是立刻让丁丁退房,小心驶得万年船,半个小时后,他们找了一家茶楼。他们不敢继续驻扎宾馆,如果憨子真要通风报信,黑皮完全可以把他们找出来,毕竟,像他们这样具有鲜明特征的一群人,任何地方都不容易隐身。
这次行动一开始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遭遇,所有的人都心情郁闷。这个时候,苏树东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头子,当年老头子第一次尝试黑道业务,跟着刘成远征雨城,他们遭遇伏击的时候,老头子心中又想了些什么?或者,他可能永远无法体会老头子当年那种感受,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完全不同。“给胡国林打电话。”他指示丁丁。
他们这次远征,首先得探清楚黑皮的行踪,他们准备了很多办法,憨子这条线断了,苏树东决定尝试一下胡国林的关系,这是一个警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向黎百胜求助。
十分钟后,胡国林那个叫毕波的警察朋友打来了电话,然后,他约苏树东到另外一个茶楼见面,要求只能苏树东一个人去。
“一个小警察还要做派!”阴四爷不屑一顾。但是他们都知道不能不按对方所说的去做。这是别人的地盘,他们有求于人。苏树东让坦克送他去,他一个人进入茶楼,毕波早到一步,已经在雅间里点好了茶,桌上还放着一整条烟,明显是从茶楼拿的,这让苏树东心中立刻不舒服起来。
“说吧,捞人还是生意。”毕波大剌剌地说。
苏树东感觉眼前这个满脸横肉的中年人更像何庆丰蒋疯子一样的大哥,完全联想不到他本来的职业。他开始询问渝州道上的一些人和事,准备慢慢迂回到他想了解的黑皮身上,这是吸取了憨子的教训,同时将来万一有事,也似乎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毕竟,毕波是一名警察。但是毕波立刻看穿了他的居心,不耐烦地命令说:“东哥,我们渝州人不喜欢绕,你想问啥就直问,我还在上班。”
苏树东压抑住自己的愤怒,迟疑一下,决定坦白。他简短说了事情经过,隐去了局二的名字,只说黑皮坑了他的朋友,他受朋友所托。
“只是要钱就好办了。要命的话,呵呵,谁也不敢趟这浑水。”毕波用手敲着桌面,沉吟一下,然后树起食指,“这样吧,我也直说,这个数,一万。我欠国林的人情,这忙肯定要帮。”
苏树东点点头,从手包中拿出一坨钱,放在桌上。他第一次遇见这么直接开口要钱的警察,而且怕他误解成一千,毫不忸怩地报出准确数目,完全体现了渝州人的性格。虽然价格有些高,但苏树东无法拒绝。毕波也正是知道这一点。
二十分钟后,苏树东回到他们团伙所在的茶楼,脸色阴沉,他简短地说了刚才从毕波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两年前黑皮的老大坤哥因为争抢客源,枪杀了另一赌场的杰哥,现在,杰哥一个兄弟刑满出狱,找上坤哥要给一个说法,实际上就是想敲诈一笔钱,坤哥当然不会就范,双方现在剑拔弩张,摆开架势准备血战。黑皮现在也领着他手下的兄弟进入全面警戒,很少在公众场所露面,身边总有三四个人,而且基本上都带着武器,这也是刚才憨子为什么不辞而别的原因。他以为苏树东他们是杰哥的兄弟从江城请来的杀手,他一个小混混,哪敢介入这种火并之中。
“这个屁娃不是光屁股串门,没事找事嘛!坐了几年都还没有改造好啊?一出来就惹是生非!”阴四爷愤怒地指责杰哥的兄弟。
“要不先回去?”丁丁小心地建议,“等他们打完咱们再来。”
“如果是寻仇倒是一个机会,不声不响地做了他,条子根本就想不到我们。可惜我们这次是要叫他拿钱。”任晓东说。这是对丁丁的支持,也是委婉表示自己的意见。他们这次行动成功的最大保证是敌明我暗,但是现在目标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无法偷袭。
“撤吧。回去再说。”苏树东做了决定。任晓东在他们团伙中很少发表意见,但是他既然开口,苏树东就会重视。
回到江城,苏树东跟伍明打电话,说自己通过一些朋友打听到黑皮的大哥正在跟人血拼,但他没有告诉伍明自己带人远征渝州,“那就等他们打吧。谢谢苏兄弟,有消息通知一下。”伍明懒洋洋地感谢,并不真诚。
乘兴而去,无功而返,这让准备大干一场的苏树东心中充满沮丧和郁闷。幸好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些事是注定的,人的一生中有很多这样的事,它们汇集起来,就是命运。仅仅过了三天,苏树东突然接到毕波的电话:“我免费提供给你一个消息,二哥出面替坤哥他们讲和了。”
于是,苏树东的战斗队伍再次出发,因为意识到自己最初轻视了对手,这一次他们准备充分,他跟任晓东和阴四爷商量后,从伍明那里调了两把短枪。
去的路上,阴四爷抓紧时间跟丁丁在后排熟悉这个冰冷的凶器,另一把枪交给另一辆车上的任晓东团伙使用,“不会真要用它吧?”丁丁吐了吐舌头问。
“你他妈以为是玩游戏啊!咱们是黑社会。”阴四爷一个巴掌甩过去,丁丁脸上多了五条红印。
苏树东静静地坐在前排,没有说话,也没有回答。他认为阴四爷说得对,阴四爷总能够一语道破问题的本质。他们是黑社会,如果一个黑社会分子必然要走到这一步,那么他就只能接受。
当天晚上,两辆车停在黑皮居住的一幢居民楼前,根据毕波提供的资料,黑皮在外面有一些女人,但跟妻子关系一直很好,尤其他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所以他几乎每晚都会回家。前一段时间由于提防对手,他可能待在外面,现在他的大哥跟对手讲和,战争状态解除,应该能够在这里守株待兔。
他们八点多进入阵地,一直窝在车里,虽然开着冷气,还是难耐。凌晨一点,依然不见目标出现,苏树东准备收兵,明天继续。
“我们吃点消夜?”任晓东建议。
这个时候喧嚣的城市差不多完全安静下来,除了一家火锅店还在营业,苏树东明白任晓东不想放弃,“好吧。喝点冻啤酒凉快一下。”
任晓东的坚持得到了回报,他们坐下后刚刚喝了几杯,一辆车就亮着大灯从街那边驶来,似乎有种奇异的感应,他们一桌人都同时停止了动作。阴四爷咳了一声,任晓东和他的兄弟们已经不引人注意地站了起来,扶着肩出了火锅店蹲在街边,像是醉酒的人和照顾他们的同伴。在所有人眼角余光锁定中,轿车挨着火锅店停下。整条街唯一亮着灯的店面吸引了司机,这是苏树东他们的运气。副驾车门推开,一个人下来,摇摇晃晃,正是黑皮,司机从另一边下车,似乎也有些醉意。
“弄。”任晓东低喝一声,他和他的兄弟们就扑了上去。苏树东和阴四爷也冲出火锅店,但没有上前帮忙,他们的目标是司机。
黑皮和司机还算机警,黑皮立刻往居民楼里逃跑,黑皮的司机转身回奔,拉开车门,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他没有坐进去开车逃跑,而是转身面对扑上来的埋伏者,面色狰狞地举起手。
“枪!”
阴四爷恐惧地低嘶,声音都变了,他一拐子把苏树东撞向旁边,自己倒向另一边,两个人都摔在水泥地上。几乎在同时,“啪”的一声脆响,司机竟然开枪了。
“啊!”一声怒吼,一道黑影飞过去,砸在司机头上,是坦克。刚才冲出火锅店的时候,他随手抓了一把小凳子做武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这也是他们的运气,司机被砸晕了,被跟着冲过去的坦克和丁丁扑在地上。
一分钟后,他们已经全部上车,驶离现场。黑皮的司机被丢在后备箱,黑皮在任晓东他们的商务车上,两个俘虏都上了警用手铐。直到他们离开市区,上了高速公路,丁丁才吁了一口气:“刚才好险。”
这句话打破了他们之间的沉默,刚才这段时间,他们一直没有说话,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高度紧张中回过神来。
“是险,没有想到那娃还有枪。”阴四爷干巴巴地说。他们现在都在回想刚才的惊险,谁也不知道那一枪是对着谁开的,那一颗子弹飞到哪去了,距哪一个目标更近,一尺还是两尺。一个醉鬼手中的枪,没有理性而没有顾忌,没有准头而更加危险,当时他们相距不到五米,那种情况下,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如果不是坦克随手抓了那张小凳子,不是他的准头,司机肯定会开第二枪,那就谁也无法想象。幸好,他们都中了彩票。
“你刚才想了些啥?”阴四爷问坐在前排的苏树东。
苏树东明白阴四爷问的“刚才”不是指现在,而是指司机开枪那一瞬间,他没有回答,他也在问自己,刚才那一瞬间,他想了些什么?
他记得某本书上写过,很多人常常在那极短的一瞬间想到很多人和事,似乎那一瞬间是异常的漫长,可以供一个人回味他的一生,那么,他刚才那一瞬间,想到了谁?想到了哪些难忘的事?他还有些什么事没有来得及去做?很多平时他从来没有想到的,或者他故意要去忽略的,突然间如同潮水退去复回,涌了上来。他愣了一下,觉得心中某处微微动了一下,他做了一个决定,明天,他一定要去看她。
第二天,苏树东让丁丁开车陪他去省城。
丁丁远比坦克机灵,而且丁丁形象光辉,不像坦克一看就是纯粹的莽夫。他们开的是局二的奔驰车,苏树东特意借的,这一次,苏树东准备充分,重视程度丝毫不逊于远征渝州。黑皮和那个司机交给了伍明,剩下的事他不用介入,要拿到钱,要应付坤哥可能的报复,都不会比绑架黑皮轻松,那是局二自己的事了,他没有必要继续趟这浑水,他已经做好了他想做的事。
这一天是周五,下午五点的时候,苏树东想见的人坐在办公桌前正在无聊。是海棠,苏树东以前的同学,现在是总经办一位秘书。她所在的公司是省发改委下属一家国有大企业,工作轻松,待遇丰厚,她毕业后能够端上这种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肯定是她家庭的原因,但是调入总经办,纯粹就是因为她个人的努力,或者说是她的某些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