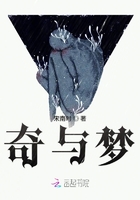“我是斯托克莫兰的格坦克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哦,医生,”福尔摩斯温和而礼貌地说,“请坐。”“别来这一套,我知道我的继女来过你这儿,她跟你说了什么?”“今年虽然天气很冷……”福尔摩斯说。“她都对你说了些什么?”老头儿气急败坏地叫喊起来。“但是我听说番红花会开得不错。”我的伙伴仍然微笑着说。“哼!你骗不过我!”我们这位新客人上前一步,挥动着手中的猎鞭说,“我认识你,你这个流氓!我早就听人说过你,福尔摩斯,一个专管闲事的人。”我的朋友报以微笑。“你这个专管闲事的家伙!”
他笑得更加开心。“福尔摩斯,你这个苏格兰场自以为了不起的芝麻官!”福尔摩斯哈哈地笑了起来。“你的话真有意思,”他说,“你走的时候别忘了把门关上,因为有一股穿堂风。”
“话说完我就会走,你竟然敢管我的事。我知道斯托纳小姐来过这里,我跟踪了她。我可没你想的那么软弱可欺!瞧这个。”他迅速地跨前几步,抓起火钳,双手用力把它折弯。
“千万别让我抓住你!”他咆哮着说,顺手把扭弯的火钳扔到壁炉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房间。“他可够和善温和的了。”福尔摩斯哈哈大笑说,“虽然我的块头比他小,但是如果他再多呆一会儿,他会发现我的手劲也很大。”说着,他拾起那条钢火钳,猛然用力,就把它重新弄直了。
“真是有趣,他竟然把我说成是官方侦探。但是,这却为我们的调查添加了乐趣,现在我只希望这个家伙别折磨那位可怜的女士。好了,华生,我们先吃饭吧,饭后我要步行到医师协会,我希望在那儿弄到一些有助于我们处理这件案子的材料。”
歇洛克·福尔摩斯回来时已快一点了。他拿出一张蓝纸,上面杂乱地写着一些笔记和数字。
“我看到了那位已故的妻子的遗嘱,”他说,“为了知道它确切的含义,我计算了遗嘱中所列的那些投资有多少收入。在那位女士去世时,全部收入差不多一千一百英镑,现在,因为农产品价格下降,最多有七百五十英镑。可是每个女儿一结婚就有权利拿走二百五十英镑。因此,很显然,假如两个小姐都结了婚,这位医生就只能得到很微薄的收入,甚至即使只有一个小姐结婚也会使他很狼狈。我早上的工作没有白费,他有足够的动机去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华生,现在事不宜迟,特别是那老头儿已经知道我们参与了此事;所以,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去雇一辆马车,前往滑铁卢车站。如果你能把左轮手枪放在口袋里,我会很感激的。对于能把钢火钳扭弯的先生,一把埃利二号是最能解决事端的工具了。我想再加上一把牙刷,所有的工具都备齐了。”
在滑铁卢,我们正好赶上一班开往莱瑟黑德的火车。到站后,我们从车站旅店雇了一辆双轮轻便马车,在萨里单行车道上赶了五六英里路。那天天晴气爽,春光明媚,蔚蓝色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树木和路边的树篱刚刚抽出第一片嫩芽,空气中散发着令人心旷神怡的潮湿的泥土气息。我感觉这春意盎然的景色和我们将要开始的调查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对比。我的伙伴双臂交叉地坐在马车的前部,帽子垂下来遮住了眼睛,头垂到胸前,陷入了沉思之中。可是蓦地他抬起头来,指给我看对面的草地。
“你瞧那边。”他说。一片树木浓密的园地,铺展在一处不很陡的斜坡上,在最高处形成了密密的一片丛林。透过树丛可以看见一座古老宅邸的灰色山墙和高高的屋顶。“斯托克莫兰?”他说。“不错,先生,那是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的房子。”马车夫说。
“那边正在进行修缮工作,”福尔摩斯说,“我们就去那儿。”“村子在那儿,”马车夫指着左面的一排屋顶说,“但是,如果你们想去那儿,可以走近路:跨过篱笆两边的台阶,然后走地里的小路。就在那儿,那位小姐正在走着的那条小路。”
“我想,那位小姐就是斯托纳小姐,”福尔摩斯用手遮住太阳,仔细地瞧着说,“没错,我想我们就照你的意思做。”我们下了车,付了车钱,马车吱呀呀地调头往回行驶。
当我们走上台阶时,福尔摩斯说:“我认为我们最好装成是建筑师,或者是来办事的人,以避免其他的麻烦。午安,斯托纳小姐。你看,我们是说话算话的。”
我们这位早上见过面的委托人匆忙地迎过来,一副很高兴的样子。“我一直在热切地等着你们到来,”她热情地和我们边握手边大声说道,“一切都很顺利。罗伊洛特医生进城了,不到傍晚他是不会回来的。”
“我们已经荣幸地认识了医生。”福尔摩斯说道。然后他把事情的大概描述了一番。我们就见斯托纳小姐的脸和嘴唇渐渐地失去了血色。“上帝啊!”她叫道,“他竟然跟踪我。”“看来是这样。”“他太奸诈了,我总是摆脱不掉他的控制,他回来后会做什么呢?”“他会想尽办法保护自己,因为他可能发现,他被更奸诈的人盯上了。今天晚上,你一定不要让他进你的房间。如果他很震怒,我们就送你去哈罗你姨妈家里。现在,我们必须立即行动,所以,请带我们去你姐姐的房间。”
这座宅邸是用灰色的石头砌的,石壁上满是青苔,中央部分比较高,两侧是弧形的边房,像一对蟹钳似的向两边延伸。一侧的边房窗户都坏了,用木板堵着,房顶也有一部分坍陷了,一副荒废已久的样子。房子的中央部分也缺乏修缮。可是,右首那边一排房子却比较新,窗子里窗帘低垂,烟囱上炊烟阵阵,表明这一家人就住在那里。靠山墙竖着一些脚架,墙的石头部分已经打通,但是我们在那里却没有看到工人。福尔摩斯在那块修剪得不太平整的草坪上缓慢地踱来踱去,认真地检查了窗子的外部。
“我想,这是你过去的卧室,当中那间是你姐姐的房间,挨着主楼的那间是罗伊洛特医生住的地方。”“完全正确。但是现在我在当中那间睡觉。”“是因为房屋正在修缮中吧?但是,那座山墙没有修缮的必要啊!”“是的,我相信那么做的目的是让我从我的房间里搬出来。”“啊,有问题。嗯,这狭窄边房的另一边是三个房间共同的过道。里面肯定也有窗子的吧?”“当然,但是那些窗子都很窄,人根本钻不进去。”
“你们晚上都锁着自己的房门,所以不可能从那一边进入你们的房间。现在麻烦你到你的房间里去,并且锁上百叶窗。”
斯托纳小姐照办了。福尔摩斯十分仔细地检查着窗子,用尽各种方法都没有打开百叶窗。上面甚至连一条可以插进刀去把闩杠撬起来的裂缝也没有。随后,他用放大镜检查了合叶,可是合叶是铁制的,牢牢地嵌在坚硬的石墙上。“嗯,”他有点疑惑地搔着下巴说,“我的推理看来有些说不通。一旦这些百叶窗锁上了,是不可能有人钻进去的。好吧,我们来仔细检查一下,看看里边有没有能弄明白事情真相的线索。”
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侧门走进刷得雪白的过道,三间卧室的房门都朝向这个过道。福尔摩斯不想检查第三个房间,所以我们直接就来到第二间,也就是斯托纳小姐现在的卧室、她的姐姐不幸去世的那个房间。这是一间简单的小房间,按照乡村老式宅邸的样式盖的,有低低的天花板和一个开口式的壁炉。房间的一角立着一只带抽屉的褐色橱柜,另一角安置着一张床,罩着白色的床罩。窗子的左侧是一只梳妆台,再加上两把柳条椅就是这房间的全部摆设。只是正当中还有一块四方形的威尔顿地毯。房间四周的木板和墙上的嵌板已被虫蛀得到处是孔,十分老旧,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这些木板和嵌板可能在当年建筑这座房子时就有了。福尔摩斯搬了一把椅子到墙角,沉默地坐在那里,他的眼睛却在四周转动,细致地察看房间的每一个细节。
最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悬挂在床边的一根粗粗的铃拉绳上,随后问道:“这个铃通向哪儿?”那绳头的流苏就搭在枕头上。
“通到管家的房间里。”“和其他东西相比,它无疑很新。”“是的,是最近这一两年才装上的。”“我想是你姐姐要求装上的吧?”“不是,她从来没有用过它,我们总是自己去拿需要的东西。”“那么,看来在那儿安装这么好的一根铃绳完全没有必要。对不起,给我几分钟,我想仔细看看这地板。”他趴到地上,手里拿着他的放大镜,迅速地前后匍匐移动,十分仔细地检查木板间的裂缝。接着他检查了房间里的嵌板。然后,他走到床前,眼睛直盯着它,好一会儿后又顺着墙上下地看着。最后他把铃绳握在手中,使劲地拉了一下。
“咦!这是假的。”他说。“不响吗?”“不响,上面甚至没有接上线。这真是有意思,现在你仔细看看,绳子其实是系在小小的通气孔上面的钩子上。”“真是奇怪的做法,我过去根本没注意。”“非常奇怪!”福尔摩斯手拉着铃绳自言自语地说,“这房间里有一两个地方很特别。例如,造房子的人很愚蠢,竟然让通气孔通向隔壁房间,用同样的工夫,他本来可以让它朝向户外的。”
“那也是最近的事。”这位小姐说。“是和铃绳同时安装的吗?”福尔摩斯问。“是的,那时候进行了几处小的改动。”“这实在是很有趣——装样子的铃绳,不通风的通气孔。这实在是很有趣,斯托纳小姐,我们到里面那一间去检查检查看。”
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的房间比他继女的宽敞一些,但陈设也是那么简单。一张行军床,一个摆满书籍的小木制书架,架上的书籍多数是技术性的,床边是一把扶手椅,靠墙有一把一般的木椅,一张圆桌和一只大铁保险柜,这就是这个房间的主要家具和杂物。福尔摩斯在房间里慢慢地走了一遍,很仔细地检查了每样东西。
他敲敲保险柜问道:“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我继父业务上的文件。”“噢,你亲眼看见过吗?”
“只有一次,那是几年以前。我记得里面装满了文件。”
“但里边不会有一只猫吗?”“不会,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哦,看看这个!”他从保险柜上边拿起一个盛奶的浅碟。
“不,我们家没有猫,只有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
“啊,是的,当然!嗯,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大猫差不多,但是,一碟奶根本不够满足它的需要。有一个地方,我必须确定一下。”他蹲在木椅前,全神贯注地检查了椅子面。
“谢谢你,事情差不多解决了。”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放大镜放回衣袋里,“喂,这件东西很有意思!”
引起他注意的是挂在床头上的一根小打狗鞭子。不过,这根鞭子是卷着的,而且打成结,使鞭绳盘成了一个圈。“你怎么看这件事,华生?”“只是一根很平常的鞭子。但是为什么要团起来?”“并不如想像的普通。哎呀,这真是个罪恶的世界,如果一个聪明人把脑子用在做坏事上,那可真是可怕。我想我现在已经看够了,斯托纳小姐,如果你允许的话,我们到外面草坪上去走走。”
我的朋友在离开调查现场时,脸色极为罕见的严峻,那表情简直是可怕的。我们在草坪上一趟趟地走着,我和斯托纳小姐都不敢打断他的思路,一直到他自己从沉思中恢复。“斯托纳小姐,”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照我的话做事。”
“我一定照办。”“事情很严重,一点也不容迟疑。为了你的生命着想,你必须听我的。”“请放心,我一切照办。”“首先,我的朋友和我今晚必须呆在你的房里。”斯托纳小姐和我都惊讶地看着他。
“对,一定要这样做,我一会儿再解释。我想,那儿就是村里的旅店?”“是的,那是克朗旅店。”“很好。从那儿看得见你的窗子?”“是的。”“你继父回来时,你要装作头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然后,当你听到他夜里就寝时,你就赶紧打开你那扇窗户的百叶窗,解开窗户的搭扣,把灯摆在那儿给我们发信号,这之后你必须带上你需要的所有东西,偷偷溜回你从前的房间,我想,虽然还在修理,你还是能住一晚的。”
“噢,是的,当然可以。”“其他的事情你都不用管。”“可是,你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在你的卧室里过夜,目的是要调查一下干扰你的声音是怎么来的。”“我想,福尔摩斯先生,你心里一定已经有了主意。”
斯托纳小姐拉着我同伴的袖子说。“也许是这样。”“那么,求求你,告诉我,我姐姐怎么死的?”“我想最好是在有了更确切的证据之后再让你知道。”“你至少可以告诉我,我认为的是否正确,她也许是突然受惊而死的。”
“不,我并不那么认为。我认为可能有某种可怕的原因。好啦,斯托纳小姐,我们必须走了,要是罗伊洛特医生回来见到了我们,一切的准备就白费了。再见,要坚强些,只要你按照我告诉你的话做,你大可以放心,危机很快就会解除。”
歇洛克·福尔摩斯和我很容易地就在克朗旅店订了一间卧室和一间起居室。房间在二楼,我们可以从窗子俯瞰斯托克莫兰庄园林荫道旁的大门和住人的边房。傍晚时分,我们看到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驱车进来,他那硕大的身躯坐在赶车的瘦小的少年旁边,显得非常不协调。男仆在打开沉重的大铁门时,很费了点事,我们听到医生不满的咆哮声,并且看到他愤怒地挥舞着拳头。马车继续前进。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那边突然射出一道灯光,原来有一间起居室点上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