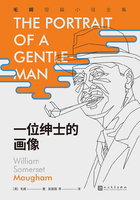在通过这片树林时,我以为我们真地会遭到一帮强盗的抢劫,说不准还会被他们杀害,而原先我们还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一切危险;直到如今,我还闹不明白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不知他们是龄期族奥斯蒂亚契人的游民,还是鄂毕河沿岸流浪到这儿来的野蛮人,还是西伯利亚的猎貂人,他们个个骑着马,人人都佩着箭,一开始有五十多人;他们来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那段距离不到火枪射程的一倍;没提任何问题,却骑在马上将我们团团围住,并且仔细地打量了我们两回;最后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由于我们总共才有十六七个人,见他们这样,我们便把队伍缩小,在我们的骆驼前面挡住,由于队伍已经收缩成这样,我们只好停下来,并叫那位侍候年轻爵爷的西伯利亚人过去。想弄清楚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的东家更是希望派他去,由于他担心这些人都是派来追他的西伯利亚驻军。那仆人打着白旗,走近了之后冲那些人喊话,尽管他用了好几种语言——更确切地说,是用了好几种语言的方言——但他们讲的话还是一个字也听不懂;然而,他们比划着告诫他,不许他再靠近他们,于是他就回来了,什么情况也没摸到;他说,从他们的衣着上看,他相信他们是拨靶人中的卡尔梅克人,要不然就是切尔卡西亚的游民部落的,总之在那大沙漠上肯定会有很多他们的人,尽管他从没听说他们会出现在这么往北的地方。
这一情况并没有使我们放心,然而我们也没有法子;幸亏在左边四分之一英里处有个小树丛,离路边很近,我立即决定我们应该到树丛那里,尽可能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首先我认为,如果他们射箭的话,那些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其次,他们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向我们进攻;其实,这建议是我的那位葡萄牙老领航提出的,他这个人就有这样一个好处;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候,他总能够为我们出谋划策,化险为夷,是最能鼓励我们的。我们马上全速前进,到达了那座小树丛;那些勒超人——我们不知如何称呼他们是好,也许可以称为土匪——按兵不动,并没有阻拦我们的意思。到达那里之后,我们非常高兴地发现那是一片沼泽地,一边有一股较大的清泉,它流进一条小溪后,在不远处又和另一条大小差不多的小溪流汇合,总之,这是一条大河的源头,那后面就是维尔茨卡河;二百多棵树围在这股清泉的四周,它们长得都很旺很密,因此我们一进入树丛,就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安全的所在,除非敌人是步行来攻击我们,否则他们是奈何不了我们的。
我们在这里待着,等待敌人采取行动,但等了几个小时也不见他们有什么动静;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葡萄牙领航在别人的帮助下,把一些树的树枝砍折而未断,让他们从这棵树搭到那棵树上,就像一道道栅栏护住我们。大约在天黑前两个小时,他们直冲我们奔过来;到这时我们才发现他们的人数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原来是另有些人加入他们的队伍。现在他们大约有八十人左右,不过,我猜想肯定有女人在其中。在他们来到离林只有射程的一半时,我们放了一些没有加子弹的空枪,同时用俄语向他们喊话,问他们想干什么,并且让他们离开;但他们越发杀气腾腾地向树林冲过来,因此他们没有想到我们已经设置了这么多障碍,从而使他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冲进来。那位老领航为我们策划,也指挥我们作战,他要求我们等敌人进入我们的手枪射程之后再开枪,这样可以保证置他们于死地,他要我们好好瞄准以后再开枪。我们等他下令后再开枪,可他迟迟就不肯开口,以至于我们射击时,敌人离我们只有两根矛长的距离。我们瞄得很准,击毙了十四个人,还伤到了他们一些人,同时他们的马也有一些死伤;由于我们的每支枪里至少装有两三颗子弹。
他们对我们的这次开火感到非常吃惊,一下子就退到五六百码以外,我们在他们后退的空当,又给枪装上弹药,见他们还保持着那么短的距离,我们就冲杀过去,夺过来他们的四五匹马,这些马的主人估计已被打死。来到死者跟前时,我们才发现他们是按超人,但怎么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长途跋涉的,竟来到异乎寻常的这个地方。
大约一小时以后,他们又想攻击我们,便骑着马在我们的小树林周围观察,想寻找突破口;但他们发现我们早就做好对付他们的准备只好再次离去,这样我们做出决定,夜里就呆在那儿不动了。
你们可以想象,我们这一夜没睡什么觉,而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给树丛的入口设置障碍上,我们同时也密切观察敌人的动静。我们在等待天亮,然而天亮以后,我们却发现了一个让我们失望的情况,原来我们以为敌人受到迎头痛击后,肯定泄了气,不曾料到现在他们的人数大为增加,而且似乎是要围困我们,竟然在离开我们大约半英里外的开阔地上搭起了十二个帐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营地。这个发现实在让我们吃惊,我承认,当时我就是以为自己和这所有的一切都完了,损失了这些身外之物倒是次要的,然而想到我经历了这么多艰难险阻,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已近在眼前,到了那里,我们就有希望得以安全离开,可偏偏要在这次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让那些货物落入这些野蛮人的手中,实在是不甘心。说到我那合伙人,他怒发冲冠地宣称,要他损失货物就等于让他破产,他宁愿死也不愿意忍饥挨饿,因此他主张战斗到底。
那位年轻的爵爷颇有骑士风度,也主张斗争到底,而根据老领航的判断,凭我们当时的处境,完全能够抵抗他们;就这样,在我们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上讨论来讨论去,白天过去了,到了傍晚,我们发现敌人的数目又增多了,并且我们不知道,到明天早上他们的人数是不是还会增多,因此我便去打听那些跟我们一块从托博尔斯克来的人,向他们打听是否有什么小路可走,好让我们可以在夜里躲开他们。也许还可以到某个城市,或者请人家护送我们过沙漠。
那年轻爵爷的仆人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准备打,而想避开他们的话,他可以带我们在夜间离去,去走一条往北通向彼特鲁河的小路,他认为我们走这条路逃走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那些拨靶人也不可能找到那条路;不过他说他的主人告诉他,宁可战斗到底也不能退却。我对他说,他误解了他东家的意思,由于他的东家是聪明人,不是喜欢打斗而打斗;而从他东家以往的表现来看,我知道他是有足够勇气的;但他的东家也很明智,不会希望用十七八个人的力量去和五百人作战,除非是被逼无奈而不得不这样做;我说如果他认为我们能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走,那我们就不干别的,就得这么去试一下。他回答说,如果他的爵爷给他下这命令,而他却无法完成,他情愿以死相报;于是我们立刻把他的爵爷找来,悄悄对他下了命令,接着我们就立刻准备起来,要打算实行我们的计划。
第一步,天色刚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小小的营地上点上一堆火,让它不断地烧着,准备让他烧一个通宵,好让那些拨靶人以为我们还在这里。然而等到天色一黑,当我们能看到星星时,便带上所有早已驮好的东西、马和骆驼,跟着一位新向导出发了,不大一会儿,我就发现,他是通过北极星确定方向的。
我们匆匆忙忙地赶了两个小时的路,天空开始变得更亮一些了,其实天空不是整夜都一片漆黑,现在月亮升起后,我们倒觉得它有些大明亮了,已经超过了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不过,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已走出三十多英里,我们的马差一点都累垮了。此时我们找到了一个俄罗斯人的村落,叫做克尔玛津斯克,就在那儿休息,而且那一天都没有听到关于那支卡尔梅克勒靶人的消息。在天黑前两个小时,我们又出发了,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然而这次不像前一夜那样急;在大约七点钟的时候,我们过了一条叫做基尔扎的小河,来到一个规模颇大的俄罗斯人的城镇,在这个叫做欧佐莫伊斯的地方,我们听说在这沙漠上有好几支卡尔梅克军队,而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现在不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了。我们不得不在这里重新买一些马,而且我们需要好好休息,因此我们待了五天;我和我的合伙人商定,拿出十个金币给那个诚实的西伯利亚人,由于他把我们带到这里。
五天以后,我们来到维尔佐格达河边的维乌斯里玛城,这条河流入德维纳河。我们非常高兴,由于到了那儿,我们离这次陆地旅行的终点已经很近了;由于那河是可以通航的,经过七天航行便可以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从那里出发,我们七月三日到了劳伦斯克。雇了两条运货的船和一艘供我们乘坐的大船以后,我在七月七日上船,十八日安全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在路上走了一年五个月零三天(包括我们在托博尔斯克待的八个月)。
在这里,我们为了等船,又耽误了六个星期,幸而有一艘汉堡船来得比最早的英国船还早一个月,要不然的话我们还得耽搁一个月;考虑到对我们的货物来说,汉堡有可能是个和伦敦同样好的市场,因此我们决定搭这船了;等我们的货物都运上了船之后,我极其自然地让我的管家留在船上看货物;如此一来,我们待在那儿的一整段时间里,我们那年轻的爵爷就可以隐蔽起来,没有必要非上岸不可了;他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省得在城里出现,由于那里极有可能会有认识他的莫斯科商人。同年八月二十日,我们离开阿尔汉格尔斯克,经过不算很顺利的航行,在九月十八日安全抵达易北河。在这里,我和我的合伙人发现我们的货物有很好的销路,不管是中国货还是西伯利亚的貂皮等等;售后所得,我的一份总计是三千四百七十五磅十七先令三便士,其中包括我在孟加拉进的大约六百磅左右的钻石。
那位年轻的爵爷在这儿同我们分别,他沿易北河而上,要到维也纳的宫廷去,由于他决定到那儿去寻求保护,去找他父亲还在世上的朋友。分别时,他对我为他做的事表示感谢,也为我对他身为王公的父亲所示的好意表示感激。
结束语:在汉堡呆了四个月,我从那儿走陆地去海牙,从那里登上定期班船,在离开英国十年零九个月以后,于一七零五年一月十日抵达伦敦。
我经历了七十二年变化莫测的生活,已充分领会隐退生活的价值,也完全明白在安宁中度过余生是一种幸福,因此我在这儿决定,要作一个比所有这些旅程更长的旅行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