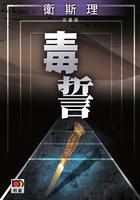一见他们这么笔直跑来,他们俩就决定在他们鱼贯而来时,每次由一个进行射击,打第一枪的人往枪里装上三四颗小弹丸,由于有可能一枪就能把三个人全都撂倒;而正好树上还有个可以作枪眼的洞。于是他就隐蔽在那儿把枪脑很难准的,而为了确保命中,他等着,直到那些生番到了距树不过三十码的地方。
他们俩看着生番过来,等在那儿,这时已经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三个中有一顿是从他们这里逃走的那个他们都熟悉的脸,于是他们当即下了决心要尽可能不让这个家伙逃走,哪怕是两个人同时开枪也罢;于是另一个人也把枪给准备好了,只要第一枪打过去,那个家伙没有倒下,那第二枪也非得把他干掉不可。
不过不会打不中的,由于那第一个人枪法极准;在他看到生番们都在一个直线上而又彼此离得相当近时,就一枪打过去,当时就把其中的两个人打中了,最前头的那个头部中了弹,马上就断了气;第二个即是那个逃走的生番,虽倒在地上却还不断气,被子弹打穿了身体,第三个人只是肩头擦伤了一点,也许是挨了那颗穿过前面那人的弹丸;尽管伤并不重,倒是把这家伙给吓坏了,竟然一屁股就坐在地上狂呼乱叫起来,那模样真是恶心极了。
当时尽管后面的五个人还没怎么感到危险。却被枪声吓了一大跳,马上就站住停了下来,枪声不断轰鸣的回声此起彼伏,由于枪声在这林子里被扩大了千百倍,各处的鸟群都鸣叫着离树飞起,而且不同种类的鸟发出不同的各自的叫声,这就像当初我在这里打第一枪时的情景,而在那之前这岛上也许还没有人放过枪。
直到一切都平静下来以后,他们还是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又若无其事地向前走上来,走到他们的同伴躺着的地方,这几个可怜的无知家伙见到倒地者的那种惨状竟站在他们的身边,七嘴八舌地说起话来,看起来可能是在问他是怎么受伤的,但却是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有可能遭到同样的打击。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会听到那个受伤者说,先是看到火光一闪,随后又听天神打了个雷,另两个人马上就死掉了,而他就立刻受了伤,这种推测我说有理由,是由于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既没见过这一带有什么人,而且是一辈子也没听见过枪声,甚至根本没听过枪是什么一种玩意,更不用说能知道火药和弹丸还能隔着一段距离伤人,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他们知道这些,他们是绝不会这般若无其事地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处境担心地站在那儿察看同伴的情况了。
在后来,我听我那两个英国同胞承认道,他们为自己不得不杀那么多人而感到难过,但这些倒霉蛋还根本不知道他们正处在危险的境况下,现在这五个人全在他们的射程之内,而那先前放了枪的那个得重新装弹药,因此他们决定一块朝那些人开枪;接下来他们商量,选定了一个准确对象,于是同时开了火,把其中的四个一下子打死或打成了重伤,那第五个人尽管没有受伤也和其他人一样倒了下去,原来是吓了个半死;那两个英国人见他们都倒了下去便以为把他们全给打死了。
这两个家伙便冒冒失失地从树里出来,连枪里的弹药也没装,由于他们以为这些生番们都已经毙命,而这就又走错了一步,待到他们走到跟前才发现至少有四个人还不死,而且其中两个人只是受了一点轻伤,还有一个人根本没有受伤,才不由得大吃一惊起来,只好举起枪托朝他们砸过去,第一个挨砸的便是逃去的那个生番,他是这个乱子的罪魁祸首;膝部受伤的是第二个挨砸者,于是他们俩立刻就脱离了苦境;这时,那个根本没有受伤的跑过来跪在他们面前,高举双手,嘴里发出可怜兮兮地咕哝之声,还一边作手势做动作,表示要求饶命,当然他们一点也听不懂他说的话。尽管这样,但他们还是比划了一下,表示要他坐到附近的树脚旁;正好一个英国人口袋里装了一根粗绳,于是就反绑了那个生番的双手,把他留在了那里,他们俩怕他们藏在林中隐蔽处的老婆和东西会被这两人发现,于是随即拼命去追那两个先前走过去的生番了。他们一度看见那两个人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后来总算放下心来,由于看他们在穿越山谷并向海边走去,由于是怕他们走相反的方向,那样就会朝那隐蔽的地方走去了。既然放下心了,他们就连忙去找他们在树下的俘虏,但可以看出他的同伴已经把他救去了,由于捆他的那根绳子成了两股纱,遗留在树根旁,而人已经不见了。
看到这些他们又同先前那样处心积虑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敌人离得有多远,有多少个敌人,于是他们决定去看看他们的老婆是不是全都安然无恙,再说她们得被安慰一下。由于她们准已吓得够呛,这是由于尽管那些生番是她们的同胞,但她们对他们却怕得要命,这也许就是由于更了解他们,因此才更害怕他们。
他们到了隐蔽处所在地,发现生番们已经进过林子,虽没有找到藏身之所,但离那儿已很近了;实际上,除非有熟悉这儿情况的人给他们指路,否则由于那儿的树长得密,一般人是找不到那儿的,而这些入侵者们没有这种指点。因此,这两个英国人除了发现那两个女人吓得非常够呛以外,这儿一切安然无事。他们到了这儿之后,使他们欣慰的是,又来了七个前来援助的西班牙人,另外还有十个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奴隶和老礼拜五(我是指礼拜五的父亲),以防生番们窜到了那藏有谷物和羊群的田庄那一带,于是就去守卫;不过那些生番还没窜得那么远。七个西班牙人来时,还带来了我说起过的那个生番——就是早先那三个俘虏中间的一个,另外他们还带来了被英国人捆住手脚捆在树下的那个生番,由于他们看来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见到七个被杀的生番,把这第八个人松了绑给带着一起来了,不过到了那儿以后,他们不得不像他们对另两个人做的那样,再把他捆起来——那逃走的人原先就是同这两个人在一起的。
现在,这九个俘虏已经成了他们的累赘;他们一度决定把这些俘虏全杀了,由于怕他们逃跑,而要保存自己,这么做就是绝对必须的了。但那位西班牙人的首领却不同意这么做,而是吩咐把他们送走,他们被暂时安置在山谷中我原来的那个洞穴里,由两个西班牙人去守看,给他们饭吃,让他们活下来——而实际上也这么办了,当天晚上,他们把那两个生番捆住手脚,让他们过夜。
西班牙人来了以后,那两个英国人信心大增,也不想死命地再守在那里,就和五个西班牙人一块再次出来去追踪生番了,并带了四支火枪,一支手枪和两根相当结实的铁头木棒。他们先来到那棵躺着那些被杀者尸体的树旁,然而可以看出,到过这儿的生番一定不止躺着的这些;由于可以看出来曾经有人打算把已经死的伙伴给挪走,而且已经把其中的两具尸体拖开了好长的一,段,但到后来却放弃了。他们又接着往前走,来到了当初站在这儿看着自己的家被烧掉的第一个小丘上,现在看到家里余烟袅袅仍然十分痛心,然而在这里他们仍然看不到哪怕一个生番,这时候他们决定要到毁掉的家园去看看,当然他们极尽小心;在距离家里还剩一小段路的时候,他们一眼看见在海边,生番们清晰的身影正纷纷上小船,准备离开。
起先,由于离得太远,没法攻击他们,令他们似乎感到懊丧,不能在生番们临走前给他们一次打击,但总得说来,能够摆脱他们也是令人很满意的。
对这两个不幸的英国人来讲,这已是第二次破产了,他们第二次付出的心血被毁于一旦,所幸大家都愿意给他们供应一切必要的东西,都愿意来帮他们重建。一向被认为是不安一点好心,不做一点好事的他们的三个同胞,却一听到这事(他们只是在完全平息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由于他们住在东面很远的地方)也来提供帮助,而且也确实是很友好地过来干了几天活,帮这两个可怜的同胞重建家园,为他们制备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在统统这些帮助下,不久他们生活又安定了下来。
在这以后又过了两天左右。由于看到了生番的独木船漂到了他们的岸边,离船不远处还漂着两个淹死的人,他们就更是高兴了,依据看到的这些,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生番们在海上遇到了风暴,打翻了他们的几条船。由于在他们离岛回去的那天晚上风确实太大了。
话虽这么说,但既然半路上有人失事丧命了,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就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侥幸存活,那么他们告诉其他人他们碰到了一些什么事,做了一些什么事,从而使他们那些生番们按捺不住,再来一次类似的侵略行为;后来看来他们确实决定要发动足够的力量,把他们碰到的一切全都掳走来这么尝试一下,由于毕竟他们在这里从来没有见到过人,要不是那第一个家伙告诉他们在岛上有人,凭他们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他们是决计得不出这种结论的,而本来没有别的人向他们证实这一点,由于向他们证实这一点的家伙已经死了。
在这以后五六个月的时间内,我们的人满怀希望,只盼生番们能够忘掉这次冒险的不幸遭遇,或者是放弃那种再来碰碰运气的想法,由于在这期间我们的人没再听到有关生番的任何动静;但突然之间,生番们又大举来犯,至少有二十八条独木船满载着他们,带着弓箭大棒、术刀以及诸如此类的武器,浩浩荡荡地驶来,总之,由于他们声势庞大,使我们的人感到极为惊恐。
在傍晚时他们在岛的东端上了岸,因此我们的人在当晚就急忙商议着对策;首先,他们意识到,他们以往唯一的安全之计是完全隐蔽起来。而既然现在有那么多敌人,就更应该如此了。于是他们决定,先把为那两个英国人造的小屋推倒了,并把他们家的羊群赶到原有的那个山洞里去,由于依他们预计,生番们将在天亮就直扑那里,他们还是会像上次那样来大干一场的,尽管这次上岸的地点离那两个英国人那儿至少有六英里远。
其次,他们把在老别墅——这是我的叫法,它现在属于西班牙人——里养的羊群全赶了出去;总之,要尽量在任何地方都做得看不出有人居住,不留痕迹;第二天一早,他们便集中全力埋伏在那两个人的庄园附近。果然不出他们所料,那些后继而来的入侵者把船都留在了岛的东端,而沿着海岸朝这边径直而来,他们的人数应该是在二百五十人左右,据我们的人估计。而我们的队伍当然是很小的了,并且还没有足够的武器分给所有这些人,这是更为糟糕的了;来看看他们的总人数吧,还是先说男人,有十七个西班牙人,五个英国人和老礼拜五(即礼拜五的父亲),还有和女人们一块带回来的三个生番奴隶(他们表现得很忠心),另外还有三个住在西班牙人那儿的奴隶。这些人总共的武器有二十一支火枪,手枪五支,鸟枪三支,还有不知是火枪还是鸟枪的五支。反正是我那次从那些造反失败的海员那儿没收来的,另外还有的就是两柄剑和三支老式的旧朝。
他们只是给奴隶们每人一把朝,而没有给他们发枪,这是一根两头都上了很大的铁矛尖的类似铁头的木棍,另外再让他们每个人身边挂把斧头什么的;当然同样我们的人也每人各有一把斧头。女人中有两个怎么说她们都不行,非要参加战斗不行,她们得到的武器是弓箭——我曾讲到过印第安人之间的一次互相残杀,这些弓箭就是西班牙人在那次战斗之后捡获的——另外,这两个女人也带上了斧头。
当总指挥的是我经常提到的那位西班牙人首领;那个威尔·阿特金斯这回当上了副指挥,由于他尽管为人凶恶可怕,却也是个敢作敢为的家伙。生番们像狮子一样地冲来,非常不幸的是,我们的人没有占据到很有利的地形;还好那个威尔·阿特金斯带了六个人去埋伏在一小丛灌木后面,算是前哨据点,现在就显得非常得力;他得到的指令是:打敌人的中路,让前面的人通过,而且在他开火了以后,必须马上尽可能机智地撤退下去、从林子里头绕到西班牙人的后方去,而西班牙人有一丛树为掩护,就守在那儿。
生番们三三两两,零乱地一批批往前奔来,威尔·阿特金斯让五十个左右的人跑了过去。接着,他便命令手下的三个人开枪,由于看见其他的人密集地一起奔了过来——而他们的火枪中都带有六七颗弹丸。他们不知道这一下打死打伤了多少人,然而这在那些生番中所引起的恐慌效果却不可言表,听到了这么可怕的一声轰响,看到他们的周围死的死、伤的伤,却无法弄明白是谁造成这一切,他们真是给吓得魂不附体,这时候,威尔·阿特金斯和另外的三人趁着生番中一片混乱,又朝着他们人最密集的地方开了火;而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第一次开枪的那三个人又已经上好了弹药准备好了,于是向他们放了第三排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