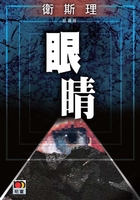可是有一情形的确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使我不得不想些办法;因为这位二公子性情是很坦白诚实的,他对于我并没有什么装假,也只是那副本色;他知道自己是光明磊落的,所以他这种对于柏蒂姑娘的好感,也不瞒他的家人,和他的兄长截然不同。虽然他没有让她们晓得向我求婚过,可是讲了许多话,他的姊妹因此看出他很爱我,他的母亲也瞧得明白;他们并没有向我说什么,她们却和他公开谈判,并且她们待我的态度也立刻变了,和往常绝不一样。我可说已经瞧见了乌云,虽然还没有看到暴风雨。我很容易观察出她们待我和以前不同,而且天天坏下去,最后我从仆人口中听到他们快要请我搬出外面住了。
这个消息不能够使我害怕,我知道她们总会另外想法安置我;尤其是我现在无日没有怀胎的危险,到那时我是非搬出去不可,并且没有理由请她们赡养我了。
没有过了多久,二公子找到一个机会来通知我,他对我的殷勤泄漏到家人的耳里。他并不诿罪于我,他说,他很知道消息是那方人泄漏出的。他告诉我这全是他素常说话太坦白了,因为他没有将对我的敬意当做一件秘密,他实在很可以这样办;他所以这么随便是因为已经决定我一答应嫁他,他就要公开地向她们说他爱我,打算娶我;不错,他的父母生气,会待他不好,可是他现在能够自己谋生了,他一向是学法律的,他有把握能够供给我使我满意;总之,他相信我既然不把嫁他当做一件可耻的事,他也决不把我当做一件可耻的事,他不屑在人前鬼鬼祟祟地不敢说出他是倾心于我的;因为将来我做了他的夫人时候,他还要当众宣布,所以现在我用不着恐慌,就答应他的求婚好了,其他一切的事情他都可以负责任去办。
我现在的情形,真是可怕,我深深地追悔我同他的哥哥太随便了;这并不是我的良心发现,只是想起不然我可以享多大的幸福,现在却是做不到了;因为不管我的道德观念多么薄弱,不会常来扰乱我的心境,可是我绝不肯当了第一个人的****,再去做他兄弟的妻子。并且,我想到那位大哥答应过我,他一得到财产,就可以娶我;可是我立刻记起我近来常常想到并暗自纳罕的一个情形,那是他把我勾引成功之后,就把这件事一个字不提;我说我常常想到,但是一直到现在我的确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入心,因为他爱我的热度好像一些也没有减低,所以他还是那样慷慨地给我金钱,不过他很细心,请我不要把他送的钱拿一便士去做衣裳,或者弄得打扮同寻常有点不同,因为这一定会引起家里人的猜疑,谁也晓得我素来是得不到这类东西的,那么一定是同哪位有了暧昧交情,她们立刻会这样忖度。
我现在真是进退两难,不知道怎样办才好。最麻烦的是这位弟弟不只天天纠缠着我,并且让别人看出他这痴情。他走到他姊姊的或者他母亲的房里,坐下说一大阵我的好处,对我讲了许多悦耳的话,甚至于当着她们面前,她们都在房里时候。这里渐渐弄得谁也晓得,全家里人都谈着这个问题,他母亲责备他,她们待我的态度也大变更了。总之,他的母亲故意露出几句话,好像她打算请我在外头居住;干脆一句话,就是想将我赶出家门。我现在想他的哥哥一定晓得这些事情,不过他或者不会想到,那是谁也想不到的,他的弟弟已经向我正式求婚过;但是我很容易看出他的弟弟还会进一步,所以我觉得绝对有同他谈论这件事情的必要,不然他也一定会来找我谈,是我先去告诉他呢,还是我不管这件事,让他来问我呢,我想不定那一种办法更好些。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我现在对于事情的确加以郑重的考虑,这是我一向所没有的。我说,经过郑重考虑之后,我决定先去向他说。不久我得到一个谈话机会,因为第二天他的弟弟有事到伦敦去,家里人又出外拜访人家,这些情形简直同从前一样,常常总是这种机会,他是照例地来和柏蒂姑娘玩一两个钟头。
他来坐了一会,很容易看出我的脸色和往常有些不同,我对他不像从前那样放纵快乐,特别是我才哭了没有多久,一会儿他全看出,很体贴地问我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苦恼没有。若使我能够隐瞒过去,我一定不说出来,但是我实在无法藏埋我的哀感;所以先让他追究好久,要我说出心事来(实在我的倾怀相告的渴望不下他的想听)我最后告诉他的确有点事情使我烦恼,是一件我不能不告他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向他说好;这件事情不单是叫我惊骇,并且把我弄得糊涂了,除非是他替我指点出一条途径,我真是不懂得如何是好。他温柔地说不管是什么事,我切不可暗自受苦,因为他要保护我,不让世上任何人欺侮我。
我故意由离题很远的地方说起,对他讲我恐怕有人暗地里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他们;因为很容易看出她们近来待我的态度变更了,现在她们已经常在那里找我的错处,有时和我很过不去,虽然我是一点错处也没有的;从前我总是和那位大姊同睡,最近她们叫我一个人睡,或者跟女仆同床;我好几次偶然听见她们很尖酸地谈论我;但是最明显的证据是一个女仆和我说她听说她们要把我赶出去,因为我是个危险分子不好再留在家里。
听了这些话,他微笑着,我问他怎么把这件事看得这么不重要,他该会明白若使我们的私情被人家发觉,我是一世不得出头的,甚至于对于他也有些妨害,虽然不像我那样终身毁了。我责备他,说他同一般男子一样,当一个女人的人格同名誉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听他发落时候,他常常拿来开玩笑,最少也是不当做一回事,将已经上了他们的当的女人的名誉破产看做是无关紧要的。
他看出我的态度是又激烈又郑重的,就立刻换一种口气。他说他觉得很难过,我会把他当做这样子一个人;他从来待我并没有什么不对地方,值得我这种谴谪,他一向是把我的名誉看得同自己的一样宝贵;他敢说我们的来往做得很机敏,家里人一些狐疑也没有;若使当我告诉他我的心事时候,他微笑着,那是因为他最近听到几句话,使他更加有把握我们的私情是没有人猜到的;当他说给我听他所以能够这样放心的理由,我一定也会像他那样开了笑口,他很知道他这个消息会使我十分满意。
“这真是一件我不懂得的秘密,”我说,“不然,被人撵出家门总不会反使我自己觉得满意;若使我们的来往并没有被她们发觉,我自己也不晓得做过了什么事情,使得她们全家都换一副脸孔对我,像现在这样待我,她们从前是多么慈爱地待我,仿佛我是她们自己的儿女一般。”“小孩子,”他说,“她们对你有些不放心,这是真的;可是她们一些也没有猜到真相,没有想到你我的关系,她们所怀疑的到是我的弟弟洛宾;她们的确相信他向你求爱;那个傻家伙简直是自己明白地告诉他们,他老同她们玩笑说他打算娶你,把自己做个笑柄。我承认我以为他不该这样,因为他一定会看出这些话将她们弄得很苦恼,因此对你冷淡起来;但是这使我觉得很满意,因为这更可以保险她们绝不会来怀疑我,我希望这也会使你满意。”
“就这一方面讲,”我说,“我自然觉得满意;但是我的大问题并不在这点,最使我烦的并不这一方面的问题,虽然我对于这点也有些关心。”“那么,你的大问题是什么呢?”他问。跟着我就呜咽流下泪来,不能够对他说什么话。他尽力地安慰我,渐渐一步迫紧一步地要我说出到底是什么事。最后我答道,我想也应当告诉他,他有知道这件事情的权利;并且我希望他替我指点出一条路来,因为我心里太乱了,实在不知道走哪条路好。我就将全部事情和盘托出。我说他的兄弟实在不该这样瞎讲,弄得大家都晓得,因为若使他很神秘地进行,这种事情应当是秘密的,我只须坚决地拒绝他,不说出什么理由;过了一时他自然会停止他的追求了;但是他起先就很自负,以为我绝不会拒绝他,后来又随随便便地通知全家人他决定娶我,这么一来,事情就不好办了。
我说我是怎么样地拒绝了他,他的求婚又是多么诚恳正经的。“但是,”我说,“我的境遇是苦上加苦,现在她们待我不好,因为他想娶我;将来听到我居然拒绝了他,她们一定会待我更坏,因为她们立刻要说里头总有些黑幕,自然会看出我已经同别人偷情了,不然我绝不至于谢绝这个在我地位以上的婚姻。”这些话的确很使他惊吓。他说这实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他也想不出一个使我脱身的良方;但是他要去仔细研究一下,下次我们相会时,他可以告诉我他考虑的结果,现在我对于他的弟弟既不要允诺,也不要干脆地谢绝,暂时可以取种犹豫不决的态度。
我仿佛惊得跳起来,听到他说我不要去允诺他兄弟的求婚。我说他该晓得我是无从去允诺他兄弟的求婚。因为他已经说好将来娶我,我也早已允诺他了;他不是一向总是说我是他的妻子,我自己也以为是他的夫人,好似我们已经行过婚礼一样;我所以会这样想,全是因为他始终要我自动做他的妻子。
“我亲爱的,”他说,“现在不要去管这些小节了,若使我在名义上不是你的丈夫,我对你还是像一个丈夫待他的妻子那样关切;现在不要让这些零碎的事情搅乱你的心,让我把这事情详细观察一下,下次见面时我可以把我所决定的办法说给你听。”他用这些话尽量地来安慰我,但是我看他的心事很紧,虽然对我非常体贴,吻我总有一千遍,恐怕还不止,还给我钱,但是我们同在一起有了二个钟头,他并没有什么别的举动,那时候我的确觉得很纳罕,想起我们从前的习惯同我们今天有多么好的一个机会。
他的弟弟五六天后才从伦敦回来,又过了两天他才有机会和他细谈,那时他就同他很亲切地讨论这个问题,当天晚上他找到一个机会(我们谈得非常久)把他们所说的话重述给我听,尽我记忆能力之所及,他们的谈话大略是如下。他告诉他的弟弟在他到伦敦以后,他听到一个关于他的奇怪新闻,就是人们说他向柏蒂姑娘求爱。“是的,”他的弟弟有些生气的样子说,“怎么样呢?谁配管这一类的事?”他哥哥说:“别生气,洛宾,我并不是说我配来干涉!我也没有为着这件事和你生了气。不过我看她们对于这事倒很关心,她们待那个可怜的女孩也不好起来了,我看她这种情形觉得也很难过,好似我自己挨人家的冷眼一样。”“你所说的她们到底是谁?”洛宾说。“我是指我的妈妈同那两位姑娘。”他的哥哥答道。
“听着!”他的哥哥说,“我问你,你不是开玩笑吗?你真真爱了那位姑娘吗?”“好吧,”洛宾说,“让我坦白地告诉你!我爱她超过世界里一切妇女之上,我总得娶她,让她们爱怎样说就怎样说,爱怎样干就怎么干罢了。我相信那女子不至于会拒绝我。”
当他告诉我这些话时候,我的心大受感动,因为虽然照通常道理说起来我是绝不会不承诺的,但是我深深地知道我是不得不拒绝他的,我又看出来我这次不得已的拒绝是我一生不幸的祸根;可是我晓得这类意思只好存在心里,口里应当讲出另外一种话,所以我就用下面这些话来打断他的述说。
“啊!”我说,“他想我不能够拒绝他吗?但是他将来会看出不管他的地位多么好,我到底还是能够说个不字。”
“亲爱的,”他说,“先让我把我们的谈话报告完,然后你可以任意批评。”
他继续说下去,告诉我他就这样回答他的弟弟:“但是,弟弟,你知道她是一个钱也没有的,你却很可以娶一个嫁妆丰厚的小姐。”
“这绝不能够影响到,”洛宾说,“我对于这位姑娘的爱情,我的结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位女人,永不会单为着要饱我的腰包。”所以,他对我说,“亲爱的,我们简直没有法子反对他。”“是的,是的,”我说,“你看我是能够反对他的,我现在学会了怎样去拒绝人,虽然我从前没有学到这套本领,若使世上最可羡慕的王公大人现在来向我求婚,我也能够笑着脸高兴地对他说句不肯。”“但是,我亲爱的,”他说,“你能够对他说什么话?你知道,我们前次会谈时候你不是说过,他要用百般的话来对付你,全家人都会纳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我说,微笑着,“我能够一下子立刻堵住她们的嘴,我只用告诉他同她们,我是已经嫁给他的哥哥了。”
他听着我的话也轻轻一笑,但是我看出我的话使他很惊吓,他那种失措的神情是没有法子掩饰的。他回答道:“虽然这话也有一点儿道理,但是我想你只是开开玩笑,说你要这样子答应她们,因为这种答话对于我们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
“不,不,”我欣欢地说,“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自然不愿意随便露出秘密。”
“但是,”他说,“当她们看出你坚决地拒绝一个对于你是这么有利益的婚姻,你要用什么话去对付他同她们呢?”
“我怎么会找不出话来回答她们?第一下,我用不着把理由告诉她们,这不是我的义务,并且我可以对她们说我已经嫁人了,不说出嫁的是谁,这样一来,他也是一筹莫展的,因为他没有什么理由能够再进一步追究我。”
“不错,”他说,“但是全家人都要来麻烦你!要你说出真相,就是我的父亲也会追究你,若使你断然地拒绝他们,他们一定对你翻脸无情,并且她们还要怀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