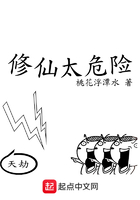我的伴侣因为戴上了老犯这个头衔,被处死刑了;那个年轻的罪人却蒙到宽赦,先得个暂缓处刑的判词,但是在监狱里饿了不少日子,最后设法把她名字也列在赦书里面,这样子就出狱了。我的伴侣这个可怕的例子深深地把我吓住了,有许久时间我不去街上流荡;但是一天晚上,在我保姆家的邻近,人们喊道:“火烧房了。”我的保姆往外看,我们那时都跑起来了,她立刻喊道某一位太太的家全屋顶都着火了,我也看见的确是这样的。她那时用肘推我一下。“现在,小孩子,”她说,“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既是这么近的地方着火,你能走进去,在街口被群众塞住之前。”她接着告诉我要怎样办去。“去,小孩子,”她说,“到那个屋里,跑进去告诉那个太太,或者你看到的任何人,你是来帮她们的,说你是这么一位太太(指那个太太的一位住在街上那头的朋友)派来的。”她吩咐我再到第二家一样办去,向我说出另一个名字,那又是第二家的太太的一个朋友。
我跑去了,到那屋里,我看见她们一团纷乱着,这是你们猜得出的。我跑进去碰到一个女仆,“天哪!我的乖乖,”我说,“这件凄惨的事怎样闹出来呢?你的主母在哪里?她干什么?她没有危险吗?小孩子们在哪里?我是从××太太那里来帮你们的。”“太太,太太”,那女仆跑去,尽量大声地嚷道,“这里有一个姑娘从××太太那里来帮助我们。”那个可怜的女人已经半疯了,膊里挟着一个小包,手上抱着两个小孩,向我走来。“天哪!太太,”我说,“让我带这班可怜的孩子到××太太那里;她请你把他们送去;她将照顾这两个可怜的小羊。”我立刻从她手里抱过一个,她把其余那个也递到怀里。“好,请你,看上帝面上,”她说,“送他们到她那里去吧。啊!替我谢她的好意。”“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要保存起来吗?”我说,“她也可以为你看守。”“啊,乖乖!有,”她说,“愿上帝赐福予她,你得替我谢谢她。拿去这包器皿,也交给她吧。啊,她是个好心的女人。啊,天哪!我们是全毁了,全倒霉了!”她疯头疯脑地离我跑去,她的女仆跟着,我就带着两个小孩同一个小包跑掉了。我一走进街上,我就看见一个女人来到我面前。“啊!”她用一种怜怜的声调说道,“太太,你抱的小孩快摔下了。来吧,这是个悲哀的时候,让我帮助你吧。”她立刻抓着我的小包,要替我拿。“不,”我说,“若使你想帮我,请拉着这小孩的手,只请你替我引他到街头;我将跟你一道走,你的劳苦,我也将有相当的酬报。”我说了这些话,她免不了跟我同走;但是,总之,这个东西是一个和我同行的人,她不要别的,只要那小包;可是,她跟我同走到那家门口,因为她不得不如是。当我们到了那里,我向她咬耳朵。“去吧,小孩,”我说道,“我晓得你是那一行的人,你现在还可以去兜不少的生意。”
她了解了我的意思,走开了。我和小孩一起打雷也似的打着门,那家的人们既然起先已被着火的消息惊起,很快地就让我进去,我说:“太太醒着吗?请告诉她——太太恳求她收留这两个小孩;可怜的太太,她将全毁了,她们的家全是一团火了。”她们很客气地收留那孩子们,哀怜在灾难中的家庭,我就带着小包走去。一个女仆问我要不要把那小包也搁在那里。我说:“不,亲爱的,那要拿到别个地方去;那不是属于她们的。”
我现在很用不着匆忙了,我于是往前走去,谁也没有问我,把这包器皿,那是很值钱的,一直带回家去,交给我的老保姆。她对我说她现在不去瞧它,却叫我再出去再兜些生意。
她给我相似的线索,叫我到着火的人家隔壁的太太那里,我就努力想法进去,但是此刻火警的风声到处传布得这么厉害,这么多的水龙在那里营救,街上挤着这么多人,我绝不能走近那屋子,无论怎么样干去;所以我又回到我老保姆家里,将那小包拿到我房里,我开始检视一遍。我现在还感到恐怖,当我说出我发现那包里有多么贵重的东西;我只用说,有许多件家庭用的银器皿之外,那已经是很值不了,我发现一条金链,一件古式的东西,上面的小锁已经断了,所以我想是有好几年没有用了,但是那金子并不因此而少值钱;还有一小箱的古式戒指,一粒女人的结婚戒指,几块旧式金锁的碎片;一只金表,一个钱袋,里面有一共值得差不多二十四金镑的古金币几块,此外还有几件值钱的东西。
这是我所染手过的最大的同最坏的赃物;因为虽然像我前面所说的,我现在关于其他窃案是心硬得绝无任何自悔之可能了,但是那的确真使我的灵魂战栗,当我瞧着这么多的实物,想到那个可怜悲伤的太太,她此外被这火灾已经损失不少了;她一定以为她救了她的金银器,同最值钱的东西;她将多么惊骇同痛心,当她发现她是被骗了,发现带着她的小孩子同她的东西走去的人并不是像我所冒充那样由邻街的太太派来的,这两个小孩却是莫名其妙地带到她家里的。
我说,我自认这个举动的不合人道很感动了我,使我非常怜悯她,那时一想到这事情,眼泪就包在我眼里;但是我心里虽然深觉得这是残忍同不合人道的,我却绝不愿拿出什么赔偿来。这种自责渐渐地消磨去了,我开始很快地忘却得到这些东西时的一切情境了。
不单如此;因为虽然靠着这回生意我变得比从前富得多了,可是我以前下的决心,那是说脱离这可怕的生涯,当我再得到一些钱之后,却没有回到心上来,我却反去立个主意,要再进一步,要再得多些;贪婪和成功如是携手前进,我简直不再想到及时变更生活的方式了,虽然没有变更,我就不能期望有安全同舒服地占有我这么毒恶地挣来的东西;但是再挣一些吧,再挣一些吧,这老是我的想头。
最后,听了我的罪恶的一再鼓唆,我撇开了一切的怜悯同忏悔,关于这件事的一切自责只变作这个念头,我或者能够得到一个足以完成我的心愿的赃物;虽然我的确得到了那贼物,可是每次的成功又引我再干一下,是这样地鼓舞我继续操这旧业,我真不愿放下手来。
在这种情形之内,我被成功弄得心硬了,决意往下干去,我坠入了注定我得碰到的陷阱,当我此生得到最后一次的赃物时候。但是这件事那时尚未发生,我还遇到几次成功的冒险,在这个朝着毁败走去的途上。
我仍然和我保姆住在一起,她有一时的确关心着那最后上绞台的伴侣的不幸,那个伴侣好像知道很多我保姆的事情,足够带她也往绞台走去,这使她非常不安;她的确是处在一个很大的恐慌之中。
那也是真的,当她死了,没有张开过口说出她所知道的秘密,我的保姆关于那点是放心了,也许还觉得高兴,她是绞死了,但是,在那一方面,她的去世,同感觉到她没有把秘密出卖这个盛情,这感动了我的保姆,使她很真挚地哀悼着她。我尽我的能力去安慰她,她报我以使我心硬得更该上绞台去。
然而,像我上面所说的,这使我更小心,我尤其不敢去窃店货,尤其是绸缎商同布商的,他们是眼睛精明,到处留神的人们。我冒险两次,去偷那班卖花边的同卖女帽的人们,内中有一回是在一家店里,那里我看出有两个年轻女子新做这号生意,不是自幼学大的。我记得我从那里拿去一块花边,值得六七金镑,同一颜色的线。但是这只干一次,这是种可一不可再的把戏。
那老是认为一种无危险的生意,当我们听到有一家新开的铺子,尤其是当店伙计不是学徒出身的人们。那是靠得住的,她们开头总得挨一两次照顾,她们必定真是非常精明的人们,若使她们能够免去。
我又冒一两次险,但是都是所得无几,虽然也够维持生活。此后有许久我没有碰到什么大宗生意,我开始想我必定要认真不干这种生意了;但是我的保姆不愿意失掉我,还期望我可以大成,一天带我同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男人相会,那个男人说是那女人的丈夫,我后来却看出,她并不是他的妻子,他们好像是做生意时的伴侣,同其他事件的伴侣。总之,他们一同偷东西,一同睡觉,一同被抓住,最后一同上绞台去了。
我的保姆从中拉拢,我同这两人就好像联合起来了,他们带我去冒三四回险,我却看到他们干些又笨又拙的勾当,他们所以能够成功真是全靠着他们的大胆胡为和被窃人们的过于粗心。所以我决定此后应当小心干去,当和他们一起冒险时候,真的,当他们提出两三个不妙的计划时,我不肯加入,也劝他们不要做。有一回,他们说要去从一个钟表匠那里偷三只金表,他们在白天里瞧过了,发现了他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他们中的一个有这么多钥匙,他把打开这钟表匠放表的地方不当做一回事;我们就定下时间;但是当我更仔细点去考究这件事情,我看出他们打算打破那屋子的门,这既是我素来不干的事情,我不肯凑进去,他们就独自去了。他们真用了强力闯进屋里去,打开了放表的关锁着的地方,但是只看见一只金表同一只银表,他们拿去了,毫无阻碍地走出那屋子了。但是那家人既被惊醒,大喊道,“捉贼”,那个男人被追着捉住了;那个年轻女人也跑丢了,但是不幸得很在不远地方被人捆住,表就从她身上找出。这样子我第二次又幸免了,因为他们定案后,都绞死了,这是因为他们是老犯,虽然都只是年轻的人。我前面不是说过,他们一起偷东西,一起睡觉,所以现在他们也一起上绞台了,我的新组合也在那时告终了。
我现在开始非常谨慎,因为曾经这么危险地逃了被人搜寻,同有这么一个例子在我目前;但是我有一个新的唆使者,她天天鼓唆着我——我是指我的保姆;现在有一件赃物现在当前,那既是她用心打听出来的,所以她期望可以分有一大部分的赃物。一个私人家里放有大宗的胡兰德斯地方出产的花边,她得到了风声,这项花边既是违禁的东西,那是海关人员的一笔好赃物,只要他能到知道贮藏的地方。我从我的保姆得到一个详细的叙述,关于货的总额,以及隐存的所在,我去找一个海关人员,对他说我可以告诉他这么一个风声,使他会得到这么多的花边,若使他答应我会得我应得的酬报。这是个这么公平的提议,真不能再公平了;所以他赞成了,连同一个巡警和我,去和那家人捣乱。我既对他说过我能够一直到那里去,他就让我去办;那个窟是很黑的,我挤进去,手里拿一根蜡烛,把花边一包一包地运出来给他,当我递出给他时,我设法暗暗存些在我身上,能够方便地安置多少就偷存了多少。那窟里有值得将近三百金镑的花边,我自己偷拿了值得五十金镑左右的东西。那家人们不是这项花边的主人,却是一个商人把这项货物托他们保存;所以他们不像我所预料的那么惊惶。
我离开那海关人员时,他很高兴得这项赃物,他得到这么多已是十分满意了,我还同他约好相会的地方,那是他指定的一个屋子,我就到那里去,当我安置好了我带在身上的货物,关于这些东西他一点怀疑也没有。当我会到他时,他同我磋商,心里相信我是不知道对于这项赃物我是享有一股的权利的,很想出二十金镑就跟我了事,但是我让他知道我并不是像他所以为的那么不懂事,可是我心里也很高兴,他肯这样向我老老实实地讲价。
我要一百金镑,他增到三十金镑;我落到八十金镑,他又加到四十金镑;总之,他出五十金镑,我答应了,只是要一块花边,我想大约值得八九镑左右,好像这将拿来自己穿的,他也许可了。当天晚上他付我五十金镑现金,这样子就把这宗生意结了;他既是绝不知道我是谁,也从不晓得到哪里去打听我,所以若使他发现了一部分的货被我偷运走了,他也无法找我理论这件事。
我很公平地和我的保姆分这份赃物,从此后在她眼里我是个会非常灵巧地将最难于措手的事情办好的人。我看我最近干的事是我这行里最好的同最易做出的工作,我就当做是我正经的事到处打听违禁货物的消息,我去买了一些之后,总是把他们陷害了,但是这些告发里没有一回得到什么可观的结果,绝不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一回;但是我却愿意做安稳的生意,还是慎重着,不敢冒大危险,我看别人大胆干去,他们却天天都闯出祸来。
此后值得说出的事情是一回去偷一位太太的金表。那事发生在一群人之中,在一个会场门口,我真是几乎被抓了。我把她的表链完全抓住了,但是当我重重地冲她一下,好像有人在我后面把我向她推去,我一面在这时光里将那只表全部拉出,我却看到那是拉不出来的,我就让它去了,那么大声叫着,好像我被人杀了,喊道有人踏我的脚,这里一定有扒手,因为有一个人拉我的表一下;你们要知道干这类事情时我们总是打扮得很好的,我身上穿的是很讲究的衣服,身上也挂有一只表,那种像个太太的样子真不下于别人。
我一喊出,那位太太也喊道:“有一个扒手。”因为有一个人,她说,试把她的表拉出。当我动她的表时候,我和她紧紧地站在一起,但是当我喊出时,我停住好像是吓了,那时群众带着她却一同往前走,所以当她也喊出声来,却和我隔了相当距离了,因此她一点儿也不疑心我;而且当她喊,“有一个扒手”时候,我身旁另一个人喊道:“是的,这里也有一个!这位太太也被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