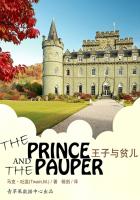好,那么,他说,他要我答应去拿我所有的一切钱来到他面前,每个小铜币。我告诉他我可以,我到我自己房里,拿来给他一个小小的私人匣子,里面我还有差不多六个金币,几块银币,把它全放在他的床上,告诉他这里是我一切的财富,诚实到一个先令也不错。他对着它看了一下,但是没有数它。又把它全堆到那匣子里,然后伸手到他的衣袋里,拉出一把锁匙,叫我打开他放在桌上的一个核木小匣子,拿来给他里面那样的一个匣子,我照他的话办了。在那匣子里有许多金币,我相信将近二百个金币,但是我不晓得实在是多少。他拿过那匣子,牵着我手,使我把手放在匣里,抓了盈握的钱。我是退缩着不干,但是他用他的手紧拉着我的手,把它放在匣里,使我拿出差不多我一次尽量所能好好地拿着的金币。
当我这样干了,他使我把它们放到我衣裙里,他拿来我的小匣子,把将我的一切钱全倒在它的里面叫我走开,把这许多全带回我自己房里去。
我特别详细地叙述这段经过,为着这里面所含的妙趣,同指示出我们交接的兴致。这事过了不久,他就开始天天吹毛求疵我的衣服,以及我的花边同帽子,总之,劝我去买更好的,那是我十分愿意的,虽然我没有现出那样子,因为世界里我所最喜欢的东西是漂亮的衣服。我对他说我必定要节省地用他借给我的钱,否则我就不能够偿还他。他于是简单地对我说道,他对于我既存个诚恳的敬意,又知道了我的景况,他不是把那些钱借我,却是送给我,他想我应当从他得到这笔款,因为我是这么不离地同他做伴,像我一向所干的。此后,他要我雇个女佣,多租几间房子,他那位同他同来巴斯的朋友回去了,他迫我和他同餐,这我是很乐意的,相信,照那情形看来,我是不会因此有什么损失的,那个女房东也没有忘记从这里面去谋利。
我们这样子过活差不多有三个月了,当那些游客渐渐离开巴斯时候,他也谈到离开,他甚欲我和他同到伦敦去。我对于这个提议是不十分放心的,不知道到那里去我会处在什么境况之内,或者他会怎样待我。但是当这问题正在辩论中,他生出很厉害的病了,他起先到索美塞得细耳里一个叫做瑟普吞的地方去,那里他有些事情,在那里生出大病,病得他不能旅行,所以他派他仆人回到巴斯,求我雇一辆马车,亲自去到他那里。在他走去之前,他留下他所有的银钱同其他贵重的东西,交托给我,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我不晓得,但是我只好尽我力量保护它们,把房子锁起,到他那里去。我看他在那里真病得厉害,可是我劝他躺在一架木床里抬到巴斯来,在那里能够有更多帮手同更好的医生。
他答应了,我带他回到巴斯,那是差不多隔了十五英里的路,我现在是这么记着。在这里他继续患着一种热,病得很厉害,躺在他床上有五个星期,这时全是我亲自看护他,陪伴他,这么周到地,这么小心地,好像我是他的妻子一样,真的,若使我是他的妻子,我也不能够再加上什么。我同他守夜得这么久,这么长,弄得最后,真的,他不愿让我再守夜了,然后,我搬一架草铺到他房里,躺在里面,刚依着他的床脚。
我真是深为他的情形所感动,深恐失丢了这样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如是,将来大概也会如是,我常坐在他身旁哭着,一连好几个钟头,可是,最后他渐渐好些,使人们生了他会痊愈的希望。他真是复原了,虽然是很慢地。
若使那实情不像我现在所说的,我也不至于退缩着不露出来,这可从在这本记述里说到别件事情时我所取的态度看出,但是我确定地说在这一切的来往里,除开了走到房里当我或者他在床上时候这个情况,同当他生病时候,昼夜看护着他必定要干的事情,我们中间未曾有过一点儿无廉耻的话或者举动。啊,倘然是这样的一直到底是多么好呀!
过了一时,他精力恢复,很快就好了,我要移去我的草铺,但是他不让我,要等到他能够独自在房里,不用谁守夜着看护他,然后我还回我自己的房里。
他利用许多机会来表示他感谢我的爱护同我的为他忧愁,当他完全复原时候,他赠我五十金币,酬劳我的劳苦,他是这么说的,拿我的生命去冒险,来救他的生命。
现在他深深地声明对于我拥有一种诚恳的,不可破的感情,但是始终表白同时对于我的道德同他自己的具有极端的谨慎。我告诉他关于这点我是十分满意的。他甚至于向我声明,若使他是光身跟我同床,他将那样神圣地保存我的贞操,正如他将那样的回护我的贞节,若使我受了一个强奸者的攻击。我相信他,告诉他我信得过他,但是这不能满足他,他要,他说,等一个机会给我一个关于这话的确实证明。
此后过了许久,我为着我自己事情要到布里斯拖去,这回他替我要辆马车,要跟我同去,他就去了,现在我们的亲密真是增加了。从布里斯拖他带我到格罗斯忒去,那只是一趟寻乐的旅行,吸些新鲜空气,在这里那是我们的运气,旅馆里没有寝室,只留一间大房子,里面有两架床。旅馆主人同我们上去指出他的房间,走进那个房子,很坦白地对他说道,“先生,那不是我的事情,去查问这位太太是不是你的夫人,但是若使不是,你们可以同样清白地躺在这架床上,有如你们是在两间房子里。”说着这话,他拉过一片布幔,那幔穿过了整个房子,结结实实地分开了那两架床。好,我朋友十分欣然地说道,这些床可以用,至于其他方面,我们的血统太近了,不能躺在一起,虽然我们可以彼此躺在很近的地方,这样子使这件事也现出正直不苟的样子。当我们快到床上时候,他规矩地走到房外,等到我已经在床上了,然后到他自己那部分的房子的床上去睡,但是躺在那里同我谈了许久。
最后,重述他那常说的话,他能够光身和我同睡,而没有给我以丝毫的损害,他从他床里起来。现在,我亲爱的,他说,你将看到我对你会是多么公道的,以及我能够不食言,他就来到我的床上了。
我稍稍抵抗了一下,但是我必定要承认我也不会很出力地抵抗他,若使他简直未说出那些约言,所以一些挣扎之后,像我所说的,我不动地躺着,让他到床上来。当他在床上,他双手拥抱着我,这样子我同他睡了整夜,但是他对于我没有其他的举动,或者给我什么,只是,像我所说的,用他双手拥抱着我,不,也没有整晚如此,早上起来,穿好衣服,离开我时我对于他正同我出世那天那么纯洁。
这是一件可惊的事情,在我的眼里,或者也是这样,在晓得自然律是怎样地发作的人们的眼里,因为他是一个强壮的,有力的,活泼的人。他这样干全不是出于一个宗教的信仰,却只是由于感情,坚持着虽然在他心里我是世界里顶可爱的女人,然而因为他爱我,他不能够伤害我。
我承认这是个高尚的主张,但是这既是我从来未曾知道过的,所以对于我这是十分可惊的。我们旅行过其他的路程,像我们以前一样,回到巴斯来了。在那里他既有机会随意到我这里,他常重演那种节制,我常同他睡在一起,他也常同我,虽然夫妇之间一切的亲热我们是都有分的,可是他从未曾有一次要再走前一步,他为着这点很看重他自己。我并不说我是这么完全地高兴这种办法,像他所想的,因为我承认我是比他更坏得多,你们就要听到了。
我们这样子过活了快两年了,只有这个例外,在那时期内他到伦敦三次,一次他在那里待了四个月,但是说一句公平话,他总是供给我钱,使我很舒服地过活。
如使我们继续这样子,我自认我们很有可以说的地方,但是聪明的人们说过,故意走到崖去勒马的是不妙的,我们就觉到这样。现在我又要说一句公平话,承认第一次破约不是出自他那方面。那是一天晚上,我们同在床上,温暖而快乐,那天晚上我们两个,我想,喝了比通常所喝的稍微多点的酒,虽然一些也没有使我们任一个神经错乱,做过了几种胡闹之后,那是我不能说出口的,我被他双手紧紧地抱着,我对他说(我现在重述这话,还带着恐怖)我心里愿意有一夜免他守约,只这一夜,他立刻照我的话办,此后就无法阻挡他了,真的我也不想阻挡他了,管他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子我们道德的统治权是打碎了,我拿朋友的地位换来这个难听的,刺耳的头衔。早上我们两个都在忏悔,我很痛心哭着,他自说觉得很难过,这是我们任一个当时所能做的一切,那条路既然这样开拓了,道德同良心的栏栅这样搬开了,我们此后没有什么大难关要去打破了。
那星期的其他几天,我们在一块时总是只有一种无味的谈话,我脸上飞红地望着他,时时发出那个悲惨的抗议,若使我现在怀孕起来,那要怎么样呢?那时,我将变成怎么样呢?他壮我的胆,对我说道,当我还是忠于他时候,他总会忠于我,既然弄到这样地步(这真是他从没有存心过的),若使我怀孕起来,他将照顾它同我。这使我们两人更死心干去了。我请他相信若使我怀孕了,我宁其因为没有一个接生婆而死去,却不肯说出他是那小孩的父亲,他请我相信我绝不至于没有人来救产,若使我是怀孕了。这种互相的保证使我们死心干这事了,此后我们随意常常干那种犯罪行为,等到最后,我起先既担心过,就成为事实了,我真是怀孕了。
我相信是怀孕了,我也使他相信之后,我们开始打算设法来处理这事,我提议,把这秘密告诉给我的女房东,征求她的意见,这个办法他赞成了。我的女房东,一个常干这种事的女人(我看出了),她看得很随便,她说她晓得最后会弄成这样子,她还为这事和我们大开玩笑。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觉得她是个对这事有经验的老婆婆,她担任一切的事情,答应去找一个接生婆同一个看护妇,把一切的查问回答得毫无毛病,以及替我们办得很有体面,她真是把这些事干得巧妙。
当我快要分娩的时候,她请我的男人到伦敦去,或者装着到伦敦去。当他去后,她通知教区里的官员,有一位太太将在她家里生产,可是她同这位太太的丈夫很熟悉,告诉他们,她做过的。一问到关于他名字的话,她把他叫做窝罗忒克利夫爵士。告诉他们他是一个很值得敬重的绅士,什么查问她都能回答,同其他这类的话。这立刻使教区里官员满意,我受人敬重地分娩着,我也只能这样,若使我真是克利夫夫人,我生产时受了巴斯里三四位最有声望的住民太太的帮助,她们住在附近。然而,这使他为我花了更多的钱。我常对他说出这点的担心,但是他吩咐我不要挂念着这点。
他既是很充足地供给我钱,做我分娩时这笔极大的开销,所以我生产里一切用度都极阔绰,但是我不喜欢弄得很华丽,也不爱胡用,并且晓得我自己的景况,知道了世界的情形,像我所经历过的,以及明知这类事情不是常常能够维持很久的,我因此留心能积多少就积多少钱,为的是随时预备雨时用,未雨绸缪嘛我是这么说的,一面使他相信这全花在我分娩时阔绰的铺张里去了。
用这种手段,把上面所说的他给我的也算在内,我在我分娩完结时候身边差不多有二百金币,里面有一部分还是我自己的钱省下来的。
我真生下一个好孩儿,那是个可爱的孩子,当他听到这消息,他写了一封很诚挚的信给我,说着这事,然后他告诉我他想那会使我更有面子些。我一能起床,身体一恢复,就到伦敦来,他在罕罗斯密已经为我预备了房子,那么好似我只是从伦敦到那里去的,再过一时我可以回到巴斯去,他将和我同去。
我很喜欢这个提议,所以特意要了一辆马车,带了我的孩子,一个看护妇他同乳他的乳娘,和一个女仆跟我同走,我于是到伦敦去了。
他坐他自己的四轮马车到勒定一接我,催我走进他车里,剩下仆人同孩子在别的马车里,这样子他带我到罕罗斯密里我的新居,我很有理由非常喜欢这新居,因为它们是很漂亮的房子,我手边有很周全的设备。
我现在真是达到我可以叫做我的好运的极点,我什么也不缺了,所缺的只是没有当一个正式的妻子;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是办不到的,这里没有可能的余地。所以我无时不是想法尽力去节省,像我上面所说的,预备将来一旦缺钱用的时候,很晓得像这类的事情不是永远继续下去的,有姘头的男人们常常更换他们的姘头,厌倦于她们了,或者吃醋起来,或者是这事,或者是别事发生了,使他们取消他们的慷慨,有时受人们这样良好的待遇的女人没有用一种贤慧的行为,留心去保存人们对于她们的敬重,或者好好地保存她们贞节所关的妙物,那时她们是应得其罪地被人们蔑视着掉开了。
但是在这点我是没有危险的,因为我既不想去换一个人,所以我简直是同整个屋子里的人们都不认得,所以也没有见异思迁这个引诱,我不同谁来往,除开了我寄宿的那个人家,同隔壁一位牧师太太。所以当他不在家时候,我不去找谁,他也从未曾遇到我不在自己房里或者客厅,每当他回来时候,若使我到什么地方去通通空气,那总是和他一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