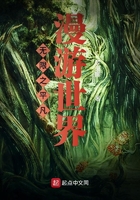知安向来随遇而安,停下思索此事就能止住疼痛,她当然照做。
米硕坐在田埂上,单腿支起,手里握着一个酒葫芦,仰头望明月,西风撩发,送来清香。
暗夜中,促织浅唱,知了低吟,水渠里掩藏的青蛙呱呱叫个不停。
亶爰山上溪流交错,一入夜,水面倒映着天空的朗月繁星,望之如在天空遨游,比此处不知美了多少倍。
自从来到人间,他常常坐在荒郊野外,怀念家乡,想念弃他而去的舍舟。
舍舟······米硕悠然的神色暗淡下去,舍舟······你悔吗?
次日,两人并双仆都起了个大早,用过早膳后,从驿馆高价购置了一匹骏马送与米硕。
“御风而行转眼便到,何必跨这慢吞吞的老马?”
“入乡随俗!”知安说了句,转身爬上马车,车外坐着两名家丁,一人赶车,一人随侍。
马车起行,摇摇晃晃碾压着乡间小道,米硕飞身上马,不急不缓,并驾齐驱。
“昨日看你状似临危,短短一夜便复旧如初,自愈本领不错嘛。”米硕拉紧缰绳慢下一头,与车内端坐的知安说话。
“承蒙夸奖。”知安不浅不淡地回道。
“既然痊愈了,为何还要去祟武城?”
“慢走不送”知安懒懒说道。
车前家丁听到,喷笑出声,好在米硕毫不介怀,接着说,“你大哥将你托付与我,不论你情不情愿,我都该信守诺言。”
若非有旁人在场,知安真想指着他的鼻尖痛骂,“少假惺惺的了,不就惦记我的妖灵么?”
“佩服佩服”,知安语调抑扬顿挫。
米硕听出了她的言外讥讽,笑道,“愧不敢当”
二人你来我往打着太极,走了大半日,方至祟武城门前。
城门楼上矗立数十名守城官兵,银枪铁甲,威风凛凛。
城门两侧站了四个巡查的士兵,抽检来往行人的通关度牒。马车缓缓前行,走到城门下被官兵拦住,“何方人士?公验何在?”
知安从身旁的小木箱中取出一卷纸券,自帘缝中递给家丁。
公验在回乡次日,狄少阳便到县里的过所办好了,临行前交给她,以便行事。
知安静静等待官兵查验完毕,索要米硕的公验。
“小人失礼了。”官兵走到另一侧小窗外,隔着帘幕恭敬道。
“官爷见谅,小女子偶染风疾,见不得光。”
“无妨,无妨,小姐可是要到行馆?小人为您领路。”
“谢过官爷,小女子并非官身,宿于行馆有违律法,自去寻一普通逆旅即可,不劳官爷领路了。”追随大哥半月,穿城过府,学了一副好官腔,知安乐滋滋地想。
官兵绕到车前,又从帘缝中将公验探入,说道,“小姐走好。”
知安道了句“多谢”,满怀期待地等着官兵向米硕索要公验,但她失望了,官兵高喊一声“放行”,米硕自然而然地随着马车入了城。
俄顷,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官兵一看她是丞相府小姐,怎么会再询问同行之人?
知安叹息,太遗憾了,若能借此甩掉米硕多好。
“公子常来祟武城?”随侍的家丁问道,“看公子熟门熟路的。”
“不错”,米硕柔和的面孔上露出笑意,在橘红色的阳光照耀下,雄姿英发,十分俊美。
“那这几日便仰仗公子了。”
临街店铺的伙计打着哈欠拉开门,见了米硕,熟稔地招呼道,“米公子,许久未见,不进来坐坐?”
“不了,要务在身,改日再来。”
“得嘞”
知安憋在车内,极想掀开帘幕看看外头热闹的景象,顾及菱角,只得强忍。
菱角仍然沉寂,不显形,不出声,与她说话,如石子投海,激不起半点风浪。知安打开木箱,无奈地看着荷包,先前菱角姑姑说要让她见识一桩阴谋,诸事耽搁,也没了下文。
阴谋——最大的阴谋莫过于罪恶昭彰的米硕了!
害人不成,还要摄取她的妖灵。坏妖怪。
知安思索着往日拜读过的神怪话本中牵涉类的,除了《山海经》中食者不妒,《异物志》记载“灵猫一体,自为阴阳”,只言片语,无从探究。
自为阴阳,知安脑中灵光一闪,类无雌雄之分,那米硕岂不是可男可女?
走了约莫一刻钟,米硕引路寻了一家名曰“易居”的邸舍,卸车下马,伙计在前领路,定下四间上等房,又为家丁叫了一桌酒菜,知安才疲惫地上了楼,而米硕早已踪迹难觅。
关好门,一头栽到床上,闷在软和的被褥中,松散地张开手脚。
旁人看她好了许多,内里亏损只有她自个清楚。女子本属阴,阳气比之男子稀薄,这小小的肉身哪里承受得住阴魂长伴身旁吸取阳气。
翻了个身,四仰八叉地合衣躺着,不一会儿,沉沉入梦。
菱角察觉其气息平缓,从荷包上飞出,飘在空中,扫视这间还算宽敞的屋子,桌椅齐全,正中立了一面童子抱金的屏风,门窗紧闭——知安入屋做的第一件事。
菱角心中不是滋味。
经过那几年的磋磨,她变得愈发不像她,阴沉,易怒,狭隘偏颇,沉默寡言,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越来越像娘——她极为憎恨的亲娘,却难以抑制,难以回头。
想起以前的日子,菱角痛不可当,时而烈火焚身,时而如坠冰窖。
花瓶中的绿叶急乱打颤,床脚的流苏翻腾滚浪,门扇开开合合,似有人随意玩弄,吃过酒的家丁腆着肚子上了楼,路过知安门前,发觉异状,问道,“小姐,可还好?”
菱角听到人声,倏然压下气势,屋内复归静寂。
家丁见无人应答,主子房间不得擅入,视线交汇后,不再多问,各自回房。
菱角飘到床前,望着睡梦中仍眉头紧皱的知安出神。
她的妖灵微如豆粒,却让她险些灰飞烟灭,回想起昨日虚空中所见,恐惧顿时如浪涛般滚滚袭来。
算了,莫想了,日后小心些便是。
米硕坐在二楼临窗的雅室中,眺望着对面的高门深府。
方阔的牌匾上黑底赤字描了“魏府”,府前立了两座一人高的石狮,面目狰狞。两扇厚重的府门徐徐朝内打开,从中前后走出四人。
为首的是一名年轻男子,浓眉大眼,扁鼻厚唇,不出彩,只称得上端正,可在米硕的眼中,比地府的牛头马面更令人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