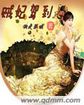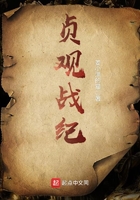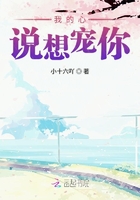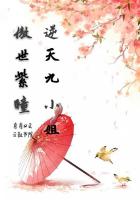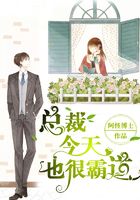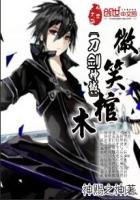太医匍伏在昏睡的安美人榻前,额前不住冒汗。“罪臣关眉,即日革去院判之职,押赴长乐宫听候太后娘娘发落。”宛初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感情。
只懂得谄媚的无能家伙,不过是一枚小小棋子罢了,微不足道得连关注都不需要给予。
替罪羊什么的,最适合这种人了。
从清芷宫出来,宛初一言未发。丹珠静静地跟着,不敢招惹主子。是谁做的?她不清楚,只知道事情绝不只是宫女失职这么简单。只是她家主子的反应,有些出人意料。
宛初的嘴角噙着一抹几不可见的微笑。
风冷冷地吹着,却掀不起宫车上厚实的夹棉缎帘。帘上镶了绒绒的雪色狐皮镶边,缎面纫了兰草暗纹,右上角一只火红的团风仪态万方地注视着下方。缎帘两侧用粗粗的锦绳缚在车门柱上,挽了个简单的绳结,垂下些丝丝络络。风一动,丝络也一动,风不息,丝络也不住飘,煞是好看。帘内还有一扇雕梅小门,此刻正紧紧闭着。车内透不进一丝冷风。四只錾银小炉嵌在车内四角,熏得车内暖香异常。宛初靠着绣垫,有一搭没一搭地玩弄手上的镯子。
斩草除根。
宛初想起幼时听训时,夫子说过的许多上代君王。
这就是上位者。她嘲讽地笑了笑。不可以放过一点可能的威胁。只是她没想到,太后会连自己的亲孙子也要抹杀。
宛初撩开窗帘,长长的甬道在窗格中飞速移动,一遍又一遍重复着相同的风景。
长乐宫屋檐上的七只小兽撞入眼帘。宛初低眉揉了揉太阳穴,调整好自己的表情。
戏还是要演的。
“是汉广宫的车子。”
长乐宫的粗使宫女们正在苑内扫雪,远远便瞧见了碌碌驶来的宫车。道上的积雪已经扫出,车子疾驰在汉白玉石板上,声如雷霆乍惊,不一会儿就到了宫门。
“怎驶得这么快!”迎出来的女官吃了一惊,小声斥着驾车的内监。小内监几番张口,却说不出话来。
帘子被从里面解开了,女官迎过去,扶了车上的人下来,抬头却见那位主子一脸焦虑之色。
“快去通报!”宛初的声音里竭力压抑着急切。女官楞了一下,道一声“诺”,小碎步急返殿内,一会儿便出来了。不等她开口,宛初提步便朝偏殿走去。她从不曾如此失了分寸,女官见状心下诧异,却不敢问,只得低了头跟进去。
“太后娘娘。”顿了顿,又道,“太妃娘娘。”
太后见她这副样子,不禁薄怒,正欲开口训斥,眼角却瞥到了坐在下首正小口啜茶的太妃,想起方才耳目报来的消息,心下了然。
仍是蹙了眉,沉声斥道:“淑妃何事慌张,竟在宫道纵车奔驰?卿代掌凤印,自当为六宫表率,今日却犯了宫规。卿自说,哀家当如何罚你?”
宛初焦虑之色更甚:“太后娘娘,臣妾的过错,请容稍后再议,臣妾自当按宫规领罚。现今要紧的是另外一事。”
皇太后抬眼望了望太妃,后者虽低了头,却一看便知是在侧耳倾听。
“你倒是快说呀!到底什么事情。”不知是否感觉到太后紧迫的目光,太妃终于从茶杯中抽出头来。
宛初的话倒像是被堵在了嗓子眼里:“这……”
太后深深看了她一眼,道:“说。”
宛初突然跪下,语带哭音:“娘娘,臣妾有罪。安美人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哗啦”几声,太后手中的杯子碎在了地上。
她一下子站起来,脸色煞白:“什么?!”
皇城里的事,就像风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
短暂的雪霁之后,大雪重新覆盖了整个京城。安络的事,很快便如被埋在雪里的一切一般沉入了人们的记忆深处。不是因为遗忘,而是因为无人提起。没有了龙子这根救命稻草,安络注定了要在皇宫这个深潭里溺死。无论当初有多么的风光,无论曾经的到过多少的关注,事实就是事实,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人,永远不会成为话题的中心。
宫内又重新恢复了平静。至少表面上如此。
如同一出闹剧,落幕得突然。从安络被关进清芷宫到她的名字在这座宫殿里彻底销声匿迹,不过月余。两宫为着龙子的失去悲恸了几日。事情便以几个宫女的以死谢罪作为终点。安络的娘家甚至不能摆起灵堂。
开始的时候秋已经结束,结束的时候冬还未最深。
几天后宫人们禀报安络的死讯时,宛初只是淡淡点了点头,连手中的羊毫也没放下。吩咐秉笔的女官做好记录,便又俯身在洒金宣纸上添了几笔。无需调查,皇宫之中让一个人消失太过容易。既然是那一位亲自动的手,与她无关,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了。
京畿百姓本来见落了一次雪,便已经是在准备着冬衣了,不料还是赶不上在第二场雪之前做好。朔风汹涌南下,寒气仿佛一夜之间席卷了整个世界。内需司所有的绣女织工都在昼夜不停地赶制宫内主子们的冬装,各宫的宫女也不例外,就连丹珠这样的大宫女也要夜夜拿着针线。
就在惠民署的人忙个不停地施粥赠药之时,各处的雪情也都陆续呈报到了未央宫的金案上。北边的杜州境内,四方驿完全瘫痪,只有硬是开出来的呈奏官道勉强能够通行。敏州粮价日日见涨,旁近的衢州粮价更是飞到了天上去。连温岭一带都已经有死了人的奏报。直隶的境况倒还算稳定,只是惠民署的食舍里也是日日挤满了领粥的饥民。
“这样下去,不知道还能撑几天。”芙依皱眉道,“国库的银子可没有堆成山,存粮也不多了。依惠民署现在的用度,早晚得把国库吃空。”
门闭着,宫女们都已退下,长乐宫佛堂里只有三人。“总不能叫它停下来吧?”皇太后道,“皇帝不是已经想了办法吗?”
“太后娘娘,让领粥的饥民去开路,路是通了,”芙依撇撇嘴,“可是没通到青州那边。银子倒是没怎么少用。粮价一日不降,任何办法都不过治标不治本。这些天未央宫的折子里尽是些无用的废话。朝里那帮人,主意没出几个,拐着弯骂人的话倒是一大堆。”
太后笑道:“淑妃不是让你堂兄去抑平粮价吗?怎么,你不去训他,倒来我这里倒苦水?”
“太后娘娘!”芙依跺脚。“如果没有三哥,敏州粮价怕会是现在的两倍,您知道的!”她撇了撇嘴,又心不甘情不愿地说:“只是按现在的这样的状况,三哥再怎么厉害也是独力难支嘛!”
“不插手是不行了。成晋这孩子,在敏州的根基到底浅了些。”笑着,太后翻开手边一本折子,细细读着上面的朱批。前日早上才递上去的奏请开仓的本子,圣上下午便批了下来。虽说女官的折子不像外臣的那样须耗时层层审批,这个速度也确是太快了些。芙依见太后这般,便肃立一旁,不敢再言。
“淑妃怎么说?”太后沉思一阵,转向正在品茶的宛初。
宛初徐徐咽下一小口茶,小心合上手中的细瓷白莲盖碗,方才说道:“圣上仁和。”
太后看她一阵,道:“你倒不急不燥。”
“其徐如林。太急躁了难免不会打草惊蛇。况且事情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宛初微微一笑,似乎是在回忆什么,“宛初记得,那几句话还是娘娘亲自教的呢。”
太后赞许地点了点头,又道:“依你徐如林,莫不成就让这粮价一直涨上去?”
“自然不可。”宛初道。
“西北大营可耐不住这样的煎熬。”芙依皱眉道。
宛初低头思索一阵,道:“我看圣上的法子倒也还使得。从前不也有过这样的先例?只是该在各州郡也都效仿才是。我记得今年秋天的收成也不算差,各处的官仓应该有些存粮才是。敏州的官仓不够粮就先从邻近的州郡调过去。只要那些屯粮的松了口就好办。”
芙依疑道:“敏州的官仓怎么会不够粮?”
“原因多了去,自个儿回去好好想想。”太后轻描淡写地说,“淑妃,你倒是说说,国库的银子要是不够留给西北大营的话该怎么着。”
宛初意味不明地道:“如此……两年了,时机该到了吧?已经没用的棋子,弃了也罢。”
芙依扬眉:“两年?你是说……”
太后正色看着宛初:“你可有把握?”
宛初冷笑,丹凤眼斜斜挑着:“九分。”
芙依看看太后,又看看宛初,佯恼道:“可打什么哑谜呢!”
太后笑着看她,只不语。宛初嘴角勾起,淡淡吐出三个字。
“贪墨案。”
当悬挂在未央宫侧殿的九九消寒图被勾到了第二个字的时候,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让举朝震惊。
“查,衢州巡抚……查,衢州布政使……查,衢州……”
连着几个大节的临近,本是一片欢喜的日子里,衢州大小府衙里却是哀鸿遍野。圣上连发十二道诏令,查办衢州大小官员二百一十六人。因一时找不出这许多合适的人手补缺,命郡守以下官员留职,衢州各府府尹、刺史全部撤换,衢州巡抚、布政使、布政司副使等几位更是当场拘了去。一时间,不但衢州,连邻近的敏州和蒲州都是人心惶惶。
“圣上有些鲁莽啊。”宛初拿起一个灯罩,将手中的密报凑到了烛焰边。薄如莎草的纸卷很快便燃烧起来。宛初随手将它放进了熏炉。火光从熏炉雕镂的空隙中透出来,很快便暗了下去。零陵香幽馥的香气里掺杂了些许纸灰的焦味。
“不过,是个好办法,”她好笑道,“简单快捷,直截了当。”
“可是这样一来,衢州的商人可不好拉拢啊。我们的人可是要牵扯进去的。”芙依喟叹道。
宛初坐回榻上,皱眉看了看棋局:“还没好吗?”
芙依皱着眉,犹疑不定地落下一子。
“那就弃子吧。虽然有些可惜,不过反正,小卒子有的是,也不差那么一个两个。”宛初笑得倾国倾城,拈了白子落在一片黑色中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十一月十四,御史在衢州粮储道的府邸里搜出了一本青皮账册,查得衢州官商相勾结屯粮,圣上惊怒。衢州粮储道交刑部候审。衢州数粮商入狱。
十八日,衢州益棠府尹因以官粮入私仓中饱私囊获罪。抄衢州巡抚官邸、益阳府尹官邸、兴安刺史府邸、恒安刺史府邸、得金银现物共计价九万两,字画古玩帛物共计价一十八万两,总计廿七万两白银,足抵三州两年赋税。
十九日,衢州新任巡抚开始以搜查出的赃银入市购粮以充官仓。
廿一日,有衢州粮商开仓济民。衢州粮价降。
廿三日,敏州粮价降,有粮商开仓。
廿六日,敏州粮价稳。
廿八日,蒲州粮价稳。
廿九日,直隶粮价稳。
……
-------
捉虫一只:原“独立难支”改为“独力难支”。虽然两个都是成语而且意思相近,但“独立难支”是贬义词,“独力难支”是中性词,此处应用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