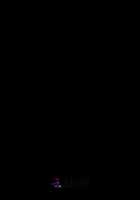两人步履匆匆地感到太后住的北苑。早有宫女等在了外头,一见苏若便上前施了个礼,道:“修容大人快些请吧!太后娘娘说,不必通报了。”
苏若跟着那宫女,一路疾步到了偏厅。太后正在听一个兰色裙裾的少女说笑话,不时愉悦地大笑;见她来了,便朝她招招手:“修容,快来快来,到哀家这里。”
“诺。”苏若恭敬地答道。她迟疑了一下,走到太后面前,跪了下去:“臣拜见太后娘娘。”
“行了行了,”太后笑道,“起来吧。”她指指那少女。“你看这一位却是谁?”
苏若转过头去。方才只是背影,已觉得很是熟悉;如今从正面看过去,苏若一下子便认出了那兰裙少女是谁,忙又施礼道:“端纪郡主。”
端纪俏皮一笑,冲她挤挤眼。
苏若不由得想起那****的恶作剧,便觉得有些无奈。太后宠溺地看了看端纪,又瞧了瞧苏若,道:“修容,这么急忙找你回来,真是辛苦你了。”
苏若连忙道:“劳太后娘娘挂心了。”
“你家老太君身子骨还硬朗吗?当年还真是多亏了她。”太后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地感叹道,“那时候,哀家还是个小姑娘呢,孝灵皇后也还在——那时候该称她太皇太后。啧啧,都这么多年了。”
苏若想不到自家祖母同眼前这位天下至尊的贵妇人还有些远远,暗地里疑惑,嘴上却谢道:“家祖母身体还算康健,劳太后娘娘挂心了。”
端纪瞅着苏若那一脸想问却又不敢问的神情,便替她问道:“太后娘娘,您认识苏修容的祖母?”
“有什么可奇怪的?苏玛尼氏好歹也是大族,每一辈里头都能出几个女官——只不过这十几年来不怎么见有罢了。”太后娘娘脸上露出了名为怀念的神色,“哀家第一次替孝灵皇后料理大宴的时候——那时她老人家都已经活过一个多甲子了,还在摄政辅佐新王——就是先帝,孝灵皇后嫡嫡亲的长孙——那时候我才多少岁呀,”她笑着看了看端纪,“也就比端纪丫头强些。”
端纪不高兴地撅起嘴来:“太后娘娘,人家都已经快要满十四了!”
“连笄礼都还远着呢,那还不算小丫头片子一个?”太后笑道,“——说实在的,不怕你们两个笑话。哀家那时候啊,可怕了,还是苏玛尼家出来的女官——也就是你家老太君,”她朝苏若点点头偶,“她暗地里替哀家张罗。哀家这才不必在孝灵皇后娘娘面前丢了丑啊。”语气中,似有一丝崇敬。
“太后娘娘那里会出丑呢?臣女看啊,就是没有苏玛尼家的老太君帮忙,太后娘娘您自己一个人来办也绝对能成。”端纪甜甜地说道。
太后哈哈笑了起来,点着端纪说:“就你最会说话!”她又对苏若说:“下回你再给家里去信,可要记着替我向苏老太君问候一句。”
苏若连连点头称诺。太后又道:“召你回来,是因为淑妃的身子有些微恙。德妃没有随行,这里也没有个主事的,偏又马上有要操心的。总不会要哀家这老太婆再来折腾吧?想来想去,还是你这孩子稳妥。修容不会怪哀家吧?”
“娘娘言重了。”苏若一面说着,一面微微福了福身。起来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同在西苑中的凌贤妃,便有些疑惑于为何太后会将她忽略了过去。但转念一想,太后向来就不待见她,也便心下了然。
“太后娘娘,您方才说马上就……”端纪歪了歪脑袋,“可大射猎不是礼部的人操办的吗?怎么要后宫来操心?”太后道:“楼楼的人来了,据说还是楼楼王的太子。总得招待招待吧?”
苏若迷惑的问道:“楼楼?楼楼人怎么来了?他们的国使不是才回去述职吗?”
“国书早就到了。是来谈青州商路的事的。去年冬天开始,那地方就没消停过。”太后似乎是不愿提起这事,道,“去淑妃那儿一趟吧,就当是替哀家这个老太婆去问候问候——明天再去,今儿晚了,她也该休息了。”
隔日早上,苏若估摸着时辰差不多了,便去了西苑。不知为何,西苑今日似乎特别多人。苏若奇怪地看着十余步便可见一个的侍立路侧的太监。离宛初的宫苑越是近,这样侍立着的人便越是多。在宫门那里,苏若被两个未曾见过的侍卫拦住了。
“吾乃长乐宫修容,来求见淑妃娘娘。”苏若不悦地说道,一面掏出牙牌来。两个侍卫对望一眼,其中的一个转身进了院子,不一会儿,带了一个宫女出来。
丹珠上前道:“修容怎么来了?”
苏若茫然地说道:“是太后娘娘吩咐下的,说是……”
不等她说完,丹珠便道:“无论如何,请您先跟奴婢来吧。”三绕五绕,她将苏若带进一处偏厅,手脚麻利地备好茶点,道:“请您务必先在这里等候。”
苏若迷惑地问道:“今天这是怎么了?外面那些人……”
“圣上来了。”丹珠说道,“委屈您了,但还是请您先在这里等候。”
苏若了然地点点头,目送丹珠离去,随即便悠游地四处察看起来。
汉广宫她常去,但青州行宫的这座宫苑,她却是第一次来。这里的装潢比云京的宫中要逊色不少,没有描金贴翠的梁画,也没有随处可见的古玩;但工夫还是下足的,其精细程度远在青州任何贵家之上。这一处偏厅同北苑里她昨日去的偏厅一样,绘满壁画,还挂起许多织毯。
她一幅幅地看过去,看了一会儿,便觉有些乏味。起坐好几次,有些急躁,苏若决定起来走走。
顺着连廊走着,没多久,却绕晕了。看着四处都有些相似的景物,苏若既是无奈又是焦急。忽然听到转角处传来人声,苏若忙躲到一旁去。
“恭送圣上。”是宛初的声音,有些虚弱,带着无比的温婉可人。苏若心里一惊。怎么绕到主殿来了?
一个好听的男声接着响起:“卿好好休息,朕明日再来看你。”
苏若突然呆住了。那声音她再熟悉不过。
子贤!
是他……竟然是他……
苏若靠在墙上,身体慢慢地滑下来。她缩在墙边,抱着膝盖。春寒未过,她紧了紧身上的衣服,忽然觉得有些发冷。
……奇怪,一般人发现自己……喜欢的人,竟然是万人之上的那一个的话,不应该是欣喜若狂的吗?
苏若想笑,却是无力扯起嘴角。
脑中闪过昨日重见时他那一身素色无花的衣裳。他在隐瞒。苏若想。他在故意的隐瞒。
失望泛上心头。该死的!为什么她不早些说出来?
……如果早知道的话,她一定不会放任自己傻傻地跳进去的吧?
……真是个天大的玩笑。邂逅翩翩公子,最后却发现那是万人之上的九五至尊,这不是宣人戏折子上才会有的故事吗?她不过是想在草原上过完平淡自由的一生而已。
生在贵族之家,她也不指望能拥有太过简单的幸福。也许嫁进青州的哪一户门当户对的高门,嫁个草原汉子,每年春夏,跟着丈夫一同去看自家的牧场,在大帐篷中住上个把月,拉着松木和马尾做的马头琴,听草原上远播的长调,纵马牧歌,如青岭上的苍鹰一般自由翱翔。丈夫出征的时候,亲手为他做一件铠甲,为他做平安荷包,然后在他得胜的时候,骄傲的在城门迎接……她想要的,只是这样一份小小的快乐而已。成为女官、进了宫,已经是她始料不及的一次变故。而今,老天还要将她卷进更复杂的漩涡中去吗?
祖母曾说,皇宫是一张巨大的棋盘,任何人只要身陷其中,除非能够成为掌控全局的下棋者,不然,必定只能沦为棋子;不是被无情的吃掉,就是被操纵着吃掉别人;即便侥幸活到了最后,也不过是成为孤家寡人。更为无情的事,这张棋盘上永远没有终局,一朝的覆灭,不过是另一朝的开始。所谓的幸存者,最终也只能是新朝的弃子罢了——就像长乐宫偏宫中那些失去权势和依靠的女人一样。
她实在怕。苏若想。
她原以为他只是哪位不曾见过的郡王,有或是哪位袭了爵位的侯爷。她想起那个初见的月夜,想起他玄色披风上的纹样。她一直以为那是螭或者蟒——月光太暗,她没有细细去数那细长盘曲的生物究竟有多少个爪子。
她是见过那天晚上的皇帝的,不是么?从乐师们的旁边,从女官席侧,远远地瞥过几眼。他被那三位尊贵的宫妃环绕着,穿着明黄色的龙袍——而不是梅林中所见的那一件,因此她才没想得这么远。
……是了,他说过他回来换了衣服的。
苏若嘲讽地勾起嘴角。
——她一直以为那披风是江牙海水纹样的。她看了那条龙附近的细纹,她以为那是海水来着……但原来那是云纹。
那是真正的五爪云龙,而不是四爪的螭龙。
她从第一天就该知道的。
她知道其实她喜欢他,她也知道昨日离开后他说了什么话——他的音量,其实不算小。她欢喜得很。
她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她想,以她青州苏玛尼氏和长乐宫修容的身份,也算是能够配的起公侯家的门槛。
只是,她不知道他竟是皇帝。
那深宫漩涡中的皇帝。
内心盘绕上升着一股恐惧。
祖母说,千万不要卷进宫妃们的明争暗斗中去,她只是长乐宫的女官。只要伺候好皇太后就够了。
但原来,她已经深陷其中了么?
进宫时间也不短了。宫中之事,从前家里人便已经说过一些;进宫以后亲见亲历的也不少。去年的安美人死得蹊跷,这件事,她又何尝不知道?
她是真的怕。
复杂的思绪一时间汹涌而来。
脚步声渐渐近了,苏若低头行礼,一动不动。
那双绣满飞龙的金黄色靴子在她的面前停伫了一阵,随即离去。
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不知过了多久,苏若才僵硬地起身,理理衣服。抬头,却对上了宛初若有所思的目光。
苏若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宛初却是很自然地牵起了她的手,婉声道:“早就等着你来了。昨晚太后娘娘那儿派了人来说,修容今儿会来。本宫可一直等着呢!谁知道圣上来了。让修容久等了吧?”她歉意地笑笑。
也许是仍旧沉浸在震惊中的缘故,苏若一时并未回应,只是呆呆地站着。宛初不急不缓地拍了拍她的手背,手上渐渐用力,眼中冷了下来。
苏若猛地回过神来,连忙就要跪下。宛初满脸堆笑地扶她起来。
“修容真爱走神。”
“是臣失礼了。”苏若道。
宛初仍是笑着,仿佛方才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咱们到里头聊去。”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