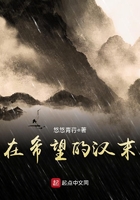我呆在父亲的书房,花了整整两周时间,把父亲从阁楼上取下的那些成捆的诗篇,一一阅读,分门别类。在其中一箱枯黄的稿件中,我看到一个残缺不全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有被一种被水浸润过的痕迹。
这年秋天的一个清晨,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轻轻地打开了这本笔记。
笔记的扉页上用红色的水笔写着:“碧水河工地创作选——1973年春”。字迹已洇散开了,有些模糊不清。1973年,这是我所能够找到的,父亲最早的一本创作笔记。我粗略地翻看了一下,这本创作选上的诗歌,拿现在的眼光来看,或许称它们为打油诗更为恰当。
而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每一首诗歌的后面,都写有诸于“作于誓师大会”、“作于打硪之后”、“作于心墙之上”、“作于夜战之下”、“刊登于碧水河工地报第*期”、“刊于大别山报第*期”之类的字样。
这些陌生的文字,静静地躺在父亲1973年的笔记本上,它们清晰而又模糊,真实而又虚幻,它们在那儿不动声色地引诱着我。而在我遥远记忆中,碧水河,早已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堤坝,以及一片汪洋的碧水湖面。可是,三十年前,我却出生在那儿,呼吸着碧水河氤氲的空气,在碧水河边悄然生长。
父亲第一本正式的诗集,是1977年出版的,而我正好也是在那一年出生,我不知道这之间,是否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我没有问父亲,我试图从父亲所保存下来的,这些奇特的文字中,去寻找那些不为我知的往事。
1977年出版的这本诗集叫《犁耙飘香》。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这样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九五三年隆冬的腊月,我出生在大别山下举水河畔的枫树湾,尚涉人生就饱尝了“放卫星”和“大跃进”的疾苦。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一个万木萧瑟的深秋,母亲在忙完一天的生计之后,见我面黄肌瘦,用竹筐挑着我去公社的卫生所。当母亲经过那道美丽的举水河堤时,紧系着生命的竹筐绳子,猝然对断。我从十几米高的举水河堤上,猛然滚落堤下。哭声刹时惊起几只飞鸟,惊落一片残阳。当母亲感到天地寒心的时候,我带着不可磨灭的创痕,依然微笑着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1987年,我十岁,父亲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太阳出山》,在这本书的后面,父亲又是这样写的: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当过农民、工人;当过办公室主任、乡镇长;当过科长局长、文联主席。灿烂的阳光虽然照耀不了周身的贫寒,一路的春风却把我引领到春的深处。咀嚼艰辛难忘的岁月,我不为当官,只为做人……
1997年,我二十岁,父亲推出了他的第三本诗歌集子《走向春天》。在后记中,父亲这样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谁不曾有过梦想,谁不曾有过希望?然而,面对大千世界,面对芸芸众生,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希望是什么?我的梦想是当个诗人,当个人们喜爱的诗人;我的希望是写好诗歌,写好中国诗歌。我还深信,尽管目前中国的诗歌被少数人折腾得不成样子,但它一直在人们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它永远是一门年轻而正在成长中的新型艺术。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首新时期文学,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诗歌作品的时候,都不能不陷入久久的深思……
在大别山秋天的那些日暮晨曦,每当我读到父亲写下的这些文字,我都会怅然若失。我常常在一些清晨醒来,为父亲是个诗人而惊奇不已。在一个个深夜里,我又会为父亲诗章中,那些闪耀着奇异光芒的诗句惊喜万分。
我想,对于我的父亲景远林来说,他这既平凡又富有浪漫色彩的一生,终将化作茫茫大别山上那一株株映山红,映红大别山上,那片依旧辽远的天空;映红大别山下,我们风风雨雨数百年的整个景氏家族……
关于父亲景远林的所有故事,我想得从1972年的那个秋天开始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