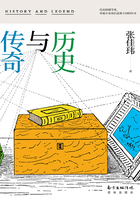其实骆秉章在这里实实在在做了一回冤大头,他在任上兢兢业业,没想到最后还是以赔款了事,成了皇帝眼中的黑乌鸦,可见银库的这汪水有多深。在这里我们可以来大致了解一下,银库究竟水深几许,能够让一个秉公执法的清官成为冤大头。
银库,从性质上来说,它就是一座仓库。不同的是仓库前面多了一个“银”字,就和钱打上了交道。当权力成为打开这扇仓库的钥匙,那么监守自盗的事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对于这一点,像骆秉章这样的监察官员也是心知肚明的。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洁身自好者也无法摆脱灰章程带来的束缚。
为了防止库银被盗,朝廷对那些在银库服役的库丁也是防之又防。库丁在银库工作期间,无论冬夏一律要求裸体入库。他们在进入库房时,要排着队从堂官公案前鱼贯而入,进去以后可以换工作服。如果干活干累了,库丁可以出去稍微休息一会儿,但出来时依然要裸体走到公案前,两臂平张,露出两胁,胯部也要抖一抖,还要张嘴像鹅一样大叫。虽然监管如此严密,可那些要钱不要命的库丁们仍然有漏洞可钻。
坊间有传言,这些库兵基本上都是子承父业,从小就是在家长的要求下按照一个职业库兵的标准来修炼自己的。他们那套高超的职业技巧,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就拿肛门夹物这门绝活来说,没有十年功夫是练不出来的。修炼者先练习夹鸡蛋,然后逐步升级,依次换成鸭蛋、鹅蛋,以至于铁蛋。修炼到最后,这些库丁每次能够夹圆锭十枚,足有一百两之多。等到他们进入银库服役,就可以作案了。每逢出入银库,库兵们就把银锭藏在肛门中,夹带而出。在各地的官银中,库丁最喜欢的是江西官银,外形光滑无棱,夹带方便,被称为“粉泼锭”。
我们可以大致推算一下,每个库丁平均每月轮班三四次,每次出入库多达七八次,少也有三四次,每次夹带以五十两计,四次也就有二百两了。这也难怪,库丁这个职业在当时会如此受到大众的青睐。
对于一个苦役库丁来说,虽然无品无级,可是他的实际权力的含金量却非一般官吏可比,库丁盗银已经没有秘密可言,《清代野记》的作者张祖翼曾经去户部转饷。他在文中记录下了这一幕:在银库的门前有一茅厕,裱糊得密不透风,库兵到此后就会将赃银卸出,然后埋起来。有时为了能够多偷银锭,库丁在搬运官银时会借口劳累休息,然后多次夹带银锭到茅厕。等到茅厕中的银锭积累到一定数量,库兵就会用水桶将其运走。水桶通常是库兵入库时带来的,因为每次入库前都要用清水洒尘,所以库兵们会把水桶改装成夹底的两层,以便作为作案工具。等到堂官走了以后,库兵们就会若无其事地挑着装着库银的桶走出来。
库丁的法定权力就是搬运官银,出的是体力活。在这一点上,他与普通服役人员并无二致,怎一个累字了得。对世人来说,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库丁的实际权力,那就是贿赂官员,将其拖下水,然后将盗取官银半公开化。 库兵三年更替,等到役满的时候,一个人可余三四万金不等。他们的管理者银库郎中也同样是三年一任,任满,贪者可余二十万,就算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亦能余十万。
库兵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他们虽然能够通过超越人体极限的技术手段偷盗库银,但是与那些能捞会贪的库官大员们相比,毕竟是一桩小买卖。这些人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挪用公款,获取的利益要远远小于风险。户部银库自乾隆时期和珅当国后,就从来没有认真清查过。嘉庆年间,虽然朝廷也曾经派过专官盘查,但由于受到库吏的腐蚀,那些负责监督的官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走形式。
随着晚清吏治的腐败,银库的侵蚀现象愈发严重,就像当时有人写道:“子而孙,孙而子,据为家资六十余年矣”。银库官兵上下沆瀣一气,时间一久,不出大问题才是真的有问题。
嘉道时期,银库的制度已经形成一整套陋规体系。当皇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就会采取补救措施。这时候就会派御史驻点清查银库,御史也是人,骆秉章那样的清廉之士毕竟凤毛麟角。按照当时的陋规,库官会私下向御史奉上规银三千两,就连御史身边的仆从也能得到两三百两。
道光十年(1840年),御史周春祺经过一番调查取证后,获取了大量银库幕后交易的证据,他打算将调查结果上奏朝廷。他的姻亲、曾任户部尚书的汤金钊就劝阻他:“此案若发,必藉数十百家,杀数十百人,沽一人之直而发此大难,何为者?”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如果被揭发,将有很多家庭被抄没,很多官员被杀头,你不能因为只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沽名钓誉,兴此大难。
虽然周春祺听从了他的建议,没有将这件事捅出去,但是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千疮百孔还是会有糜烂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