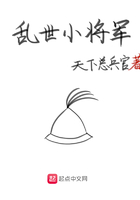道光、咸丰年间,漕运水手行帮组织再次发生重大转变,在这次转变中,青帮应运而生。
青帮的出现源于道光年间漕运体系的萎缩。道光二年(1822),朝廷开始着手整治走向末路的漕政,大量裁减漕运人员。对于裁减人员的安置,政府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旗丁,官府是以津贴的方式,予以安置;而对于水手等临时雇佣人员,就无法享受政府津贴。每人只补偿了二三千文的盘缠费,就将其打发回家务农。
对于那些长年漂泊在外的水手们而言,他们是有家难回,无业可置的无产阶级。尽管朝廷已经下了遣返令,但真正响应的人却没有几个。失业的水手依然留在漕运线上,毕竟这里还有行帮组织可以依赖。如果真让他们离开这里返回家乡,那真就成了无根浮萍,无所可依的游民。留在漕运码头还可以跟着行帮组织混口饭吃,起码不会饿死。
道光五年(1825),清廷开启海运。海运的出现对于整个漕运水手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失业人数越来越多,最后政府连最起码的二三千文的盘缠费也无力执行。
当时的社会形势异常严峻,失业后的水手们很难再找到生活的其他出路。为了应对这种转变,水手行帮只有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水上江湖向陆地江湖过渡。本来水手行帮只是漕运利益链上的一环,当这条利益链即将萎缩并走向断裂的时候,水手行帮就要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组织策略。他们不愿意放弃水上势力,但同时也向陆地的民间社会逐步渗透。
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全面实行海运。数以万计的水手、舵工、纤夫从漕运线上撤离流入民间社会。这支庞大的失业人群,主要流向了社会的三大血酬阶层。吴思先生为“血酬”下的定义,就是流血拼命所取得的报酬。我在这里将其引申,依靠流血拼命取得活命之资的阶层称为“血酬阶层”。罗教水手流向的三大血酬阶层,分别是起义军、政府军、青帮。而这时候起义军和政府军为了各自集团的利益,正拼得你死我活,也就是说这两大阶层的日子也是刀头舔血。比较下来,很多人觉得帮会生活反而相对稳定,这时候帮会的组织结构已经趋于严密。所以在海运取缔之后,大部分水手还是留在了帮会中,并没有脱离组织。
从漕运线上撤离下来的水手行帮开始向两淮盐场一带聚集,水手行帮有了一个新的称谓,青帮。行帮组织也由此拉开了暴力劫掠、贩卖私盐的黑色生涯。
青帮又称安清道友,史料记载:安清道友“号称潘门,亦曰潘安,又别称庆帮,俗讹为青帮。”与水手行帮尊奉罗祖不同,青帮尊奉的是潘祖,其帮派内的主要成员是水手行帮时期与老安对立的新安一派。从水手行帮向青帮过渡,帮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青帮依然遵守着水手行帮时期有着宗教色彩的帮规体系,比如说以师徒的名义私结党羽。青帮成员在运粮的过程中,依然会像过去那样打出龙凤旗,以官方自居。与水手行帮不同的是,青帮在官场与民间社会的灰色地带有着更为圆滑的变通度。青帮成员很多来自于漕运水手,水手的原身份虽然是民间社会的无业游民,但其职业身份却还是官方的从业人员。作为帮会内部大小首领级的人物,他们的身份等级比普通成员要高,在漕运权力体系中这些人是衔接水手与官府的桥梁,他们通常是有职有饷,两边拿好处。也就是说,这些具有职级的首领级人物与官场人物,尤其是清军中的中下级武官有着或深或浅的交情,相互勾连。所以青帮很多时候会受到官府的庇护。
道光以后的帮会组织已不再局限于漕运水手,而是扩展到两淮盐场及沿途各市镇、码头,其成分极其复杂,俨然一个庞杂而严密的社会集团。这时候的青帮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窝赃走私、敲诈勒索甚至是公开劫掠民财上。青帮的内部成分也开始发生变化,除了游民阶层还有其他行业的各色人等。
为了扩张势力范围,青帮甚至把运河沿线的捕快、衙役也吸收进来,官员入帮在当时成了社会风尚。在上海青帮“通草”里的《前人题名录》、《同道题名录》中就列举了几千名实力派人物,在这些人物中,有10%左右是守备、千总、武举、文牍之类的官员。
当帮会势力与执法者纠缠在一起,公权力就开始向民间社会势力慢慢渗透。这样就会形成以某个权力掌控者为主导,以寻租为驱动力的团伙形态。这种利益团伙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朝廷依靠正式权力很难控制,但它又附着在权力的肌体之上,在瓦解正式权力体系的同时,又将其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
清朝末年,在运河沿线有个叫做十八段的地方,方圆数十里之地,几乎全为帮会所控制。
这里聚集的帮会成员超过上万人,帮会首领叫做顾三五子。他手下的帮众有男有女,其中男帮众有数千人之多。帮众分居于各村庄各乡里。帮会按照帮众的居住地来划分地盘,每段都派驻男女帮徒上百户,分界居住。此处帮会组织的发展已经开始走向军事化,比如说在帮众聚居地的建造上,段的四周高筑土墙,厚达五六尺。城墙上面修筑有更楼和炮位。帮徒居于其中,不干黑帮营生的时候就男耕女织,像一个普通农民那样生活。如果有生意可做的时候,帮主一声令下,那些在地里忙活的农民就摇身一变成了杀人越货的土匪。此地加起来共有十八处,各段之间互为守望,攻防自如,并且帮会还备有当时最先进的枪械。这种有人有枪有地盘的黑帮组织,连官军拿他们都没有办法。
其实像“十八段”这样的地方性帮会组织的萌芽基本上都是由宗族势力发展而来,是以强大的宗族势力为基础的。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恶势力的发展壮大又会加强宗族势力的影响。许多流氓恶势力就是以宗族成员为核心,采取开山门、摆香堂、拜把子等形式,联合、招募一些臭味相投的族外分子参加而组成。
有的帮会组织就是宗族势力演变而来,是宗族势力的凝聚。而组织内部的秩序则成为宗族内部秩序的强化,组织的“老大”往往是宗族内的核心人员。因此,宗族势力越大就会促使这些恶势力越快增长,反过来,这些恶势力就会成为维护宗族利益的保护伞,促进宗族势力的对外扩展。
各段中的帮众的生活来源基本上是靠劫夺行人,抢掠商旅所得。时间久了,邻近各县的富户都将这个地方视为如同水泊梁山那样的盗匪出没之地,纷纷迁往他处。为了生存,帮会只好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向周边地区扩张,经常组织人员跑到其他县境抢劫,干起了土匪的营生。因为帮匪众多,如果他们每月分期分批出去抢掠,那么抢掠次数和抢掠所得也并不少。
邻近地方的官府衙门向上申报,要求朝廷出兵捉拿帮匪。知府调集了一千多人奔赴十八段,准备剿匪。谁知政府军来了之后,帮会不但没有被剿灭,反而发展的势头更猛了。打听之下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带兵的长官也是青帮的会徒。他与顾三五子见面之后,才知道按照青帮的辈分,两人算是师兄弟。师兄弟将朝廷的正式法规抛在脑后,从此恪守本帮帮规,官匪一家亲。最后,师兄弟二人居然立下盟约,此后不得在本州境内犯案。如果顾三五子要派段中兄弟外出“开武差”,首先要通知该长官,得到允许才可以“出差”。从此之后,周边十余个县在官匪勾结,共同治理下呈现出和平气象,而那位无所作为的长官连一根土匪的毛都没拔下,居然在当地赢得良好的口碑,并且受到官府的嘉奖。
其实在当时的运河沿岸的许多州县、码头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差役不过帮,饭碗端不长;帮会不通差,生意敲不成。这句话道出了帮会与官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
作为地方上的官差在破案时,必定会触及到帮会利益。在当时,很多地方性案件都和帮会势力有关。如果官差甩开帮会独立办案,根本就理不出任何头绪,而且即便理出头绪,也没办法实行抓捕。如果差役是帮会中人,则是另外一番情形。案发之后,只需略加查询,就可以知道此案为谁所犯了。正因为如此,帮会头目都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神通。
无论帮会的成因有多么复杂,权力黑洞和体制黑洞几乎就是黑帮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黑帮最为猖獗的地方,一定是地方官府最黑暗的地方。官府本应是黑帮的天敌,但很多时候却形成了一种互动机制。只要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能够产生利益,而这种利益又恰好满足了官员的需要,那么两者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相安无事的均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