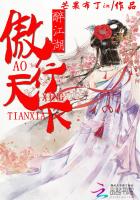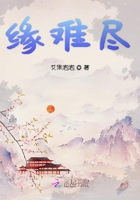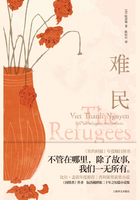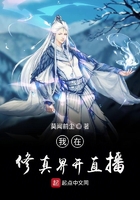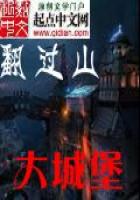旅游团来到愧园。
这座精致典雅的古代园林是小镇的骄傲。一进园门,那么一大片洁润可爱的荷花便使人赞不绝口。带团的是一位年轻的业余导游,他开始向游客们介绍愧园的来历:“古时候有个大官,什么朝代、做的什么官、他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清了,反正几十年官做下来,没犯什么错误,挺不容易的呢。在他年老退休以后——”一位游客忍不住纠正他:“应该是退职吧。”业余导游满不在乎:“我不是给古代人当导游,这样说你们容易听懂些,不是吗?——在那大官退休后,他准备安度晚年,就把自己的住宅装修得更舒服些,取名叫‘无愧园’。园里的池塘种上许多荷花,表示自己的一生像荷花的花瓣一样洁净极了。可这开心日子老头儿只过了三年。临去世前,他嘱咐儿子,把‘无愧园’的‘无’字去掉。”“哦。”众人恍然道。
“我又可以写一首诗了。”团里的一个男青年对两个女青年说。
女青年甲问女青年乙:“这一路上,他是第几次说这样的话?”女青年乙认真地回忆了一下:“第六十八次。”这么说,男青年至少可以写出六十八首诗。他已经在报纸上发表过作品,是个真正值得钦佩的诗人呢。
“可是,那个退休的大官到底为什么要去掉一个字?”向业余导游刨根问底的是个小男孩。他是业余导游的侄子,暑假里跟叔叔一起出来游山玩水。
当叔叔的被问得很不高兴:“我说小绿,这是旅游团,不是智力竞赛,哪来这么多‘为什么’?”他弯下身子警告,“你是要叔叔好看吗?”小绿不满意地咕哝了一句,不再做声了。
业余导游接着向大家宣布:大家自由活动,一小时后在园门口集合,坐班船前往另一个景点。
“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误点的自己负责!”于是大家分散开来,各自寻幽览胜,照相留念。
一个小时以后,旅游团的团员们很自觉地到了集合地点。
“看看少了谁没有?”“少了,那个导游没来!”这可是少不得的关键人物。大家等了一阵,仍不见踪影,只好分头去找。
园内庭院深深,曲径周折,找人很不容易。大家费尽周折终于在一座井边找到了那个导游,他正向井里探头探脑。
“导游,这儿很有趣吗?大家都在等你呢。”“可是,我的侄子……”“孩子掉井里了吗?!”“但愿没有……可是四处我都找过了……”其实小绿就在附近。
刚才,他是被一种奇妙的声音指引着,独自拐入后院,来到一座小楼跟前。
他看见一块木牌挂在门口,上写“愧园书画社”,再朝门里看,四壁挂满了字画。那奇妙的声音从一张古琴上发出,弹奏它的是一位相貌清奇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弹得十分入神,丝毫没有顾及走近他身边的男孩。
男孩也就静静地听着,直到曲终。
中年人缓缓收回双手,这才把脸转向他的听众,问他有什么感觉。
“嗯,好像……”小绿认真地回味着,“好像挺闷,挺重,要出什么事似的。”中年人点点头,说:“你倒有些灵气。我心情沉重,是因为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我已经历过九次,这是第十次了。多少年前的今天,愧园主人决定把‘无愧园’改成‘愧园’……”中年人将小绿领到他的画桌前,那上面有一幅刚完成的古装人物画。背景即是园中景物,画中一老者正向井中凝望。
小绿问:“这就是他吗?”“是的。”“可是,”小绿惊奇地注意到,“您怎么没给他画上眼睛?”中年人显得颇为不安,嗫嚅道:“眼睛么?今天不能画眼睛。”“为什么?”“今天……今天我怕眼睛。”小绿的心儿怦怦跳,等待着一个神秘莫测的故事。
沉吟有晌,中年人开始缓缓叙述——据说,愧园主人原先是做谏官。谏官的责任是向皇帝提出劝告。皇帝身边有九个谏官。皇帝规定每个谏官每天必须向他提出一条劝告,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这样皇帝就可以对大臣们说:“瞧,我每天要接受九条劝告,每年要接受三千二百八十五条劝告,像我这样从谏如流的皇帝太难找了。”愧园主人便得和其他谏官一样,每天仔细琢磨出一条皇帝能够接受的劝告。他们当然有经验,知道皇帝能够接受什么。他们提出的劝告一般是:“陛下,您龙袍上的龙须应该绣得再长两分,这样更神气些。”“陛下,您中午吃的一盘炒鸡蛋只用了五十五个鸡蛋,应该再加一个,双数吉祥些。”如此等等。所以,愧园主人顺利安全地干了几十年,一直到退职回家。他给自家庭园题了“无愧”二字,来概括他一生的成功。
就在题字的当天晚上,他到园中散步。走过井台旁,忽听井中有响动,像泉声幽咽,又像有人在叹气。他有点害怕,但又忍不住要去看。
黑夜里,井中却并不昏暗。可以看见井水显得紧张不安,微微起伏,像呼吸着的胸脯。井水浑了又清,清了又浑,如此三次。接着,变得很深的井底浮现出一对眼睛。这眼睛忽大忽小,时而像是很近,时而像是很远。
愧园主人觉得这眼睛很熟悉……他曾有过一个年轻的同僚——第十个谏官。这年轻人第一天见到皇帝就提了这么一条劝告:“陛下,最好能改改规矩,如果有比龙袍、鸡蛋什么的对您更有好处的劝告,每天听一百条也别嫌多;如果只有龙袍论、鸡蛋论,那么一条不听也不要紧。”皇帝听了,回答说:“我也给你一条劝告,如果你没有备用的脑袋,最好仔细些,要爱护它。”年轻人又说:“如果您确实知道一个人没有两个脑袋,那就不要随便砍别人的脑袋。”这已是他在一天内向皇帝提出的第二条劝告了,所以尽管皇帝明知他的脑袋并不多,还是给他砍掉了唯一的一个脑袋,要按规矩办……
这时,那第十个谏官的眼睛直直地、一眨不眨地盯着愧园主人……
这老人轻松安逸的心境被全部破坏了。他衰老得更快,终于病倒,终于最后决定在原来的园名上去掉一个字。
十年前,我住进了愧园。这是镇上见我的画有了些名气,就让我在这儿办了一家书画社。我很喜欢这里的环境。那是个多云的夏夜,星月朦胧,闪闪烁烁的萤火更显得耀眼。我想去看夜色中的白荷。路过那座井时,我看了它一眼,仿佛听见什么,顿时想起怪异的传说。于是不由自主地去井边窥望……啊,井水真的在微微涌动……变浑,又变清……
眼睛!我真的看见了井中的眼睛,很熟悉的,直直地盯着我。这是我的老师,指点我学画的老师呀。当他被人们当坏人看待时,我不敢说出他是我的老师,不敢去看他,甚至当后来冤案大白时,我还是不敢去看他,因为羞于以前的行为。老师不久前去世了,我只去看了他的墓碑……可此时,老师的眼睛从井中直直地盯着我!
十年来,井中的眼睛出现过九回。你瞧,我抖得厉害吧,这是预感,今晚又将是一回……
正说着,小绿终于听见叔叔的呼喊,便答应着跑了出去。
业余导游气得要命:“班船早就开走了,为了你,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浪费一夜了!”“怎么是浪费呢?”小绿不服气,“晚上可以看眼睛呀。”“什么,眼睛?”小绿便把听来的一切复述一遍。
没人相信他。
但晚上反正走不了了,不妨去看看愧园夜景,可以顺便到井边转一转。那井多少有些传奇色彩嘛。
旅游团便在愧园招待所留宿。
当天晚上,团员们在愧园里看到了萤火,看到了夜色中的白荷,居然也看到了——眼睛。
在同一个井口,各有所见:
医生见到的眼睛,属于被他误诊的病人;赌徒见到的眼睛,属于被他的赢钱导致跳楼的赌友;女青年甲在井中看到了女青年乙,女青年乙在井中看到了女青年甲,因为她们虽然常在一起,形同手足,但在背地里都说过对方的坏话;那“诗人”见到的是外国眼睛,他心里清楚,那是普希金,因为他唯一得以发表的作品是从《普希金抒情诗选》中抄来的……
另外一些颇有自知之明的团员再不敢去井口张望了。
但回到招待所以后,在他们的脸盆里、茶杯里,甚至痰盂里,都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他们所熟悉的眼睛。
只有小绿,没有看到眼睛。他还是个孩子,还没有对不起人的经历。
神秘的愧园门口,有一副由那位中年书画家撰写的对联:
似镜双睛清井底如烟一梦白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