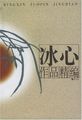Odysseas Elytis(1911-1996)
1979年获奖作家
——流着汗使劲从有时没过膝盖的泥浆里拔腿而行。因为一路之上总是下着毛毛细雨,就像我们身体内部那样。很少几次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大家也一言不发,全都那样严肃沉默,在燃着的一支松明火光下一个个分享着葡萄干。或者有时碰到机会,我们扯开军装狠狠搔着自己的身体,直到搔出血来方罢。因为我们浑身是虱子,而那是比疲劳更不好受的。终于,黑暗中传过来一声哨响,号令我们开始行动,我们便又像驮载的牲口那样努力前行,要赶在天亮之前取得进展,天一亮我们就会成为飞机的明显目标了。由于上帝并不知道目标一类的事,所以他仍坚持自已的习惯,让日光在每天同一时刻降临呢。
然后,我们隐蔽在深谷中。把脑袋朝沉重的那一侧放倒,使它不致做出梦来。但鸟类会对我们恼火得很,觉得我们根本不重视它们的谈话——也许还因为我们在无缘无故地损害大自然吧。我们的确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农人。携带着一种不同的铁镐和工具,讨厌极了。
撤回到乡下的那十二个整天,我们时常接连几个钟头地凝视着镜子中我们的面容。正当我们的眼睛渐渐地习惯了以往那些熟悉的特征,正当我们开始小心地领略那光溜溜的上唇或睡得丰满了的面颊的意义时,他们便通知我们出发,以致第二天晚上我们即开始感到我们又在变样,第三天更加,到了最后一天即第四天,就很清楚我们已不一样了。此外,我们仿佛是由年龄不同的几代人组成的一伙在沿路行进,有的来自现今,有的来自古代,由于胡子过多而变白了。头上扎着带子、愁眉苦脸的山地酋长,能吃苦耐劳的牧师,经历过几次战役的军士,表情严肃地挥着斧子的开路先锋,沾满了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的鲜血、手中拿着钉头锤和盾牌的拜占庭边疆卫士,大家在一起,谁也不说话,肩并肩地哼哼着永远前进,越过山脊和中间的峡谷,从不去想别的事情。因为正如那些一再走厄运的人习惯了祸害并最后归咎于命运或天数那样,我们始终一往直前,迎着我们所谓的瘟疫,像我们讨厌暗雾或乌云时说的那样——流着汗使劲从有时深过膝盖的泥浆里拔腿而行。因为一路之上外面总是在下着毛毛细雨,就像我们身体内部那样。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已很接近那分不清工作日或假日、病人或健康人、穷人或富人的地方了。因为前头的吼声,犹如群山那边的风暴,在不断增大,以致到最后我们能清楚地分辨出那迟钝而沉重的大炮声和单调而急速的机枪声了。还因为,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碰到了那些朝另一方向缓缓行进的伤兵。而那些戴红十字臂章的医务人员会把担架放下,向手心吐几口唾沫,眼中流露着渴望得到香烟的狂热目光。当他们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时,他们会摇头诉说他们的血腥可怖的故事。可是我们听到的只是黑暗中传来的其他声响,它们由于那深渊中的火焰和硫磺而仍在发烫。有时候,但不那么常见,有一种闷住的呼吸声,像打鼾似的,那些熟悉的人知道那是死亡的格格声响。
有时他们一路拖着那些几小时之前才被我们的巡逻兵在突袭中抓到的俘虏。他们的呼吸带有酒臭味,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罐头或巧克力糖。可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背后的那些桥梁被切断了,我们的骡子已毫无办法,陷在冰雪和滑溜的污泥中。
终于,时刻到了,我们看到了远处这里那里升起的黑雾,以及沿着地平线最先出现熠熠闪耀的红光。
(李野光译)
骡夫
在那些日子里,终于过了整整三个星期之后,第一批骡夫进入了我们的国土。他们把一路经过的那些城镇如德尔维纳、萨兰达、科尔察的情况告诉我们。他们以尽快结束和一走了之的神气卸下了咸鱼和饼干。因为他们对这种来自山区的轰轰声很不习惯,总觉得害怕,对我们瘦脸上的黑胡子也是如此。
这时发现他们中有个人身上带着些旧报纸。于是我们全都以惊愕的心情阅读着——虽然我们已经听到过关于此事的谣传——人们怎样在首都举行庆祝以及将那些从普雷维萨和阿尔塔回来休假的战士们扛在肩上游行。那时钟声整天都在长鸣,晚上人们在戏院里唱歌,并在舞台上演出我们的生活情景让群众欣赏。
我们全都沉重地缄默着,因为我们的灵魂由于成年累月在旷野中待着已变得凶狠起来,而且即使不说,我们也都对剩下的年月感到紧张。事实上,满眼泪水的中士佐伊斯却无视那些登载世界新闻的纸片,只在上面留下了五个指头的痕迹。而我们其余的人一句话也没说,只不过用眼光表示了我们对他的某种感激之情。
那时列夫特里斯独自站在一旁悠闲地卷着一支纸烟,仿佛他把宇宙的困境都承担在自己肩上似的。他回过头来说道:“中士,什么事那么惹你生气呢?那些命定吃鲱鱼和饼干的人将永远回去吃鲱鱼和饼干。而那些做日常文书工作的也得同样这么办。那些安排过舒适生活的亦将如此,不过他们是无法掌握生活的。但是请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吧:只有那种与自己内心的黑暗搏斗的人才能终于找到自己在阳光下的位置。”这时佐伊斯说:“那么你认为我就没有自己的老婆、田地和麻烦事儿,得老坐在这旷野里守着啦?”列夫特里斯回答道:“中士,一个人不喜欢的东西才是可怕的,因为它们已经丧失了,无论你怎样努力要抓住它们也是白费。可是你不会丢失感情上的东西,不用担心,而那就是在这荒野尽力而为的目的。或迟或早,那些命定要寻找它们的人必然会找到。”这时佐伊斯又问道:“那么你觉得谁会找到它们呢?”于是列夫特里斯不慌不忙伸出一个指头说道:“你和我,兄弟,以及任何一个被正在倾听着我们的现今所选中的人。”
恰好这时我们听到了夜空里尖啸着向我们飞来的炮弹。于是我们迅速地脸朝下卧倒在荆棘上,因为如今我们凭感觉认识了那些看不见的标志,而我们的耳朵能够预先准确地断定炮弹将在哪里落地开花。炮火并不曾伤害什么,只是少数几匹骡子用后腿直立起来,而另一些则吓得四散跑开了。当浓烟消散时,你能看到那些辛苦地带领骡队的人正在大声吆喝着追逐他们的牲口。他们以惊惶的神情继续卸着鲱鱼和饼干,企图尽快结束并一走了事。因为他们对这种来自山区的轰轰声很不习惯,总觉得害怕。对我们瘦脸上的黑胡子也是如此。
(李野光译)
美人与文盲
时常,在暮色休息之处,她的灵魂呈现一些来自对面群山的光明,虽然日间过得很惨,而明天又未卜吉凶。
不过,当黑夜降临和牧师的手在死者陵园的上空出现,她,孤单地,正直地,同那几个熟识的夜伴——迷迭香的微风和从烟囱来的烟雾——清醒地躺在海的门口。
分外的美丽。
一半由海浪形成或一半从沙沙声中猜到的话语,以及另一些似乎属于死者在柏树丛中惊起的话语,就像那盘绕于她头上的奇异光环,突然给她以启迪。于是,一种难以相信的彻悟让真实的风景呈现在她最深的心底,那儿,黑人们在河边同天使搏斗,显示着美人曾经怎样诞生。
或者是,换一种说法,我们称为眼泪的东西。
而且,只要她的思想还要持续,你会觉得它洋溢在她那闪光的脸上,而眼睛和颧骨饱含痛苦——像一个古庙看守人的眼睛和颧骨似的——那么深邃。
从大犬星座之巅一直延伸到处女座的顶部。
“而我,远离城市的瘟疫,梦想她身边的一片荒漠,那儿眼泪已毫无意义,唯一的亮光来自那吞没我的全部所有物的火焰。
“我们俩并肩地撑持着未来的重荷,发誓要服从星界的共同管理,彻底保持缄默。
“仿佛我真不知道,尽管是文盲,正好在那里,在彻底的沉默中,能听到最骇人听闻的喧声。
“而那孤独,从它变得为人类所难以忍受的时候起,就散布和播种了星星!”
(李野光译)
勇士的睡眠
一
他们还在散发乳香味,而面貌已经焦枯,由于通过了阴间冥府。
在那里,在无情者突然摔开他们之处
俯伏着,在那块地上,连最小的海葵也能使地狱的空气发苦。
(一只手伸开,像要努力把未来抓住,另一只手垫着蓬乱歪倒的头颅,
仿佛在一匹挖掉了内脏的骏马的眼中,它最后一次瞧着成堆冒烟的废墟)——
在那里时间解放了他们。一只翅膀最红,它遮盖着世界,而另一只已经轻柔地在远处扇动。
没有一丝皱纹或悔恨的悲痛,但是最深处那古老得无从追忆的血已艰难地开始发红,在一片墨黑的天空。
一个新的太阳,还没有成熟,
没有强盛到足以融解活的三叶草上那茸茸的白霜,但已在消除黑夜的宣布神谕的权势,使荆棘不得生长……
从一开始,岩谷,群山,树林,河流,
一个由复仇后的感情所构成的宇宙开始发光,与原来相同但被颠倒,如今勇士们可从中穿过,而刽子手在其中被立地杀掉。
悠悠苍天的耕种者们啊!
无论是深渊中正午的钟响,或者从高处飞降的极地之声,都不曾使他们的足音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