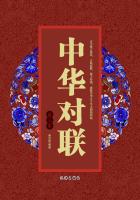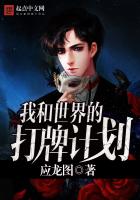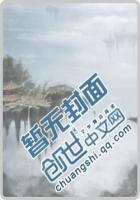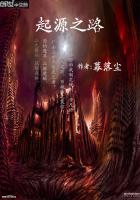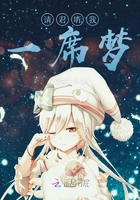没有文凭的导师
1919年,陈寅恪与吴宓在哈佛读书时,对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胡适与陈独秀深恶痛绝,陈寅恪对吴宓说:“今之盛倡白话之文学者,其流毒之大,而其实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陈寅恪对胡适的痛恨,在这短短几句话里表露无遗。其实当时痛恨胡适的大有人在,吴宓后来对朋友说:“当时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而陈寅恪又是其中最过激的一位,他完全站在胡适的对立面,一棍子将胡适打死。
1919年以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影响越来越大,来美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陈寅恪又接触了傅斯年、毛子水、赵元任、杨步伟等人。傅斯年和毛子水都是胡适的得意门生与忠实信徒;而赵元任又是胡适早年在美国的同学,情同手足,杨步伟又是赵元任的太太。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如此受到追捧,陈寅恪对胡适也慢慢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陈寅恪得知,他求教过梵文的钢和泰先生,竟然也是胡适的老师,如此说来,陈寅恪与胡适是同门师兄,如此他对胡适的认同又增加了一成。
当时陈寅恪在国外留学,生活非常艰苦,有时连饭也吃不上,但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攻读学业,熟读了藏、蒙、满、俄、朝鲜等文字,连古梵文、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吐火罗文、巴利文、印地文、希伯来文也不放过;同时潜心研究中亚史地、摩尼教、耆那教、佛教经典,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学术研究上都有独到的见解。1926年,没有学位、没有文凭、没有著作,却有着满腹经纶的陈寅恪回国,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他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曹云祥当时还不太信任陈寅恪,问:“这陈寅恪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云祥闻听吃了一惊:“我们国学院可从来没聘用过无文凭的导师,那他有没有什么著作?”梁启超答:“他也没有什么著作。”曹云祥犯难了:“既非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一听有点生气:“曹校长,您还不相信我推荐的人?实话告诉您,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却远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列举了世界名校几位著名教授对陈寅恪的评价和赞誉,曹校长听了点点头,二话没说,当场就给陈寅恪发出聘书。
时间到了1928年5月,此时的胡适早已如日中天,“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京城文化人的口头禅。陈寅恪偶然间得知胡适正在撰写《白话文学史》,将有专章论述“佛教的翻译文学”,他心有所动,“入史”的念头让他不能小看这件事,他主动去信给胡适,将新作《童受“喻论”梵文残本跋》寄给了胡适。胡适果然在书的“附记”里给予陈寅恪很高的评价,友谊第一次在两人之间建立。次年1月,胡适来北平参加梁任公遗体告别仪式,与陈寅恪第一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一番深谈后发现,两个人不但是同门师兄,祖上竟然还是世交。
祖辈传承的友谊
进入胡适的交际圈之后,陈寅恪很快和胡适结成最知心的朋友,对于胡适的盛名,他既羡慕又有几分嫉妒,曾经无伤大雅地捉弄了胡适一回。
那是1932年初夏,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出试题,他正好在《晨报》上看到胡适的新闻图片,一时灵感一闪,就在国文试题中出了个对对子的小题目,对子题为“孙行者”,要求对出对句。开考之后这道题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到了改试卷时,陈寅恪发现,参考的考生中,只有一人完全答对,对句为“胡适之”。陈寅恪不禁大为赞叹,连胡适也十分震惊,胡适说:“不管这名考生其他考卷考得如何,仅凭之一对句,也是可以被清华录取的。”当年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有专文论及陈寅恪命题的深意,“欲借此以发现聪明博闻的特殊人才”。答对题的这个学生叫周祖谟,后来成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特殊人才”。
1931年12月,受陈寅恪之邀,胡适为陈寅恪太太的祖父题写《唐景崧遗墨》,两家祖辈的世交这才牵连而出——陈寅恪太太唐的祖父叫唐景崧,曾任台湾巡抚。在任上,胡适的父亲胡传也在台湾任职,时间在1893至1895年间。胡传与唐景崧因职务关系结识,结成亲密无间的好朋友。虽说两人是上下级关系,但平日里就像兄弟一样。唐景崧对胡传颇为器重,曾委派胡传代理直隶州知州,及至兼任台东后山军务。后来两人出生入死,共同抵抗外敌入侵,鲜血凝成的祖辈友谊影响了胡适与陈寅恪之间的关系。
陈寅恪收到胡适的墨迹之后,专门去信给胡适,向他表示感谢:
“昨归自清华,读赐题唐公墨迹诗,感谢!感谢!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不抵抗主义’,诵尊作即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得到清华导师陈寅恪的尊重,胡适当然也格外珍视,他在日记中高度评价了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只要有机会,胡适就举荐陈寅恪。1940年蔡元培病逝后,陈寅恪认为胡适是文科中最有能力担任院长的人选,他向傅斯年进言,为了给胡适投上一票,他特地到重庆参加评选。
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陈寅恪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他对朋友说:“跟胡适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但他与胡适也只走到南京,并未去成台湾。虽然陈寅恪留在了大陆,但在他的心目中,胡适仍位居第一。
1950年代大陆开始批判胡适,陈寅恪公开表示拒绝参加,而且认为是“一犬吠影,十犬吠声”。尽管远离政治,陈寅恪最终也没能逃脱“****”之祸。1969年10月,被称为“司马光之后最伟大的史学家”的陈寅恪,在广州含恨辞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这样评价他说:“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