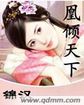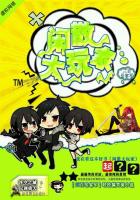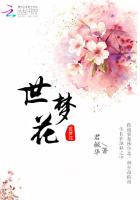爱吵架的安徽佬
陈独秀与胡适是安徽同乡,与胡适一样,他很早就离开老家怀宁,外出求学,后来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1915年秋天,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请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郊约胡适撰稿。汪孟郊与胡适同为绩溪人,同乡加同好,胡适当然没有理由拒绝。
与陈独秀结交是胡适人生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他早期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那些发轫之作,都是在陈独秀的敦促下写成的,两个人也由此结下深情厚谊。虽说志同道合,但由于各人个性不同,反应在为人处世上便有了很大的差异。
胡适引起轰动的是那篇《文学改良刍议》,文章最初在他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陈独秀得知后一再索稿,他只得一稿两投。这篇文章在《新青年》发表后立即哄传全国,使胡适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正因为这样的提携,胡适后来十分珍惜他与陈独秀的友谊,彼此之间无论分歧有多大,他总是把陈独秀当作他的朋友,称陈独秀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胡适为人温文尔雅,他有一句名言:“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而陈独秀则性情古怪,说话直爽不怕得罪人,他几乎一见胡适就谈他的主张,谈不拢就辩,辩不过就吵。胡适实在受不了时,也不和他吵,就用脚跺地板,表示自己已经很生气了,你不用再说了。陈独秀知道他的习惯,这才默不作声。
1933年10月,胡适从国外回来路过南京,可能因为事多,就没有去看望陈独秀。一直到了北平,他才写信给陈独秀解释:“我此次匆匆回国,未去看你,请原谅。两个月后有事还要去南京,届时一定去看你。”陈独秀收到信后忍不住破口大骂:“什么东西,出大名了,成人物了,有时间同达官贵人周旋,独没有时间看望老朋友,什么东西。”当即修书一封给胡适,声明与他绝交。胡适看后一笑了之,他知道这个老朋友的火暴脾气,一点小事就常常搞得一惊一乍的,仿佛是塌了天的大事,胡适对此并不太当回事。两个月后他来到南京,装作没事人一样去看望陈独秀。果然,陈独秀火气早已经散了,还像往常一样坐下来与他对谈,谈不拢就吵。据说有一次陈独秀与胡适吵得很凶,那时候陈独秀是****领袖,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两个人争执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群众运动。陈独秀认为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帝国主义的压迫。胡适则根本不承认中国的问题有什么简单的解决方案,反对“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头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平时极具绅士风度的胡适这次也受不了,最后拂袖而去。
1925年12月,北京发生了晨报报馆被焚事件,业已成为“新青年领袖”的陈独秀对此的回答竟是一个字:该。这个态度又让胡适寝食难安,他给陈独秀写信说:“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四次施以援手
激进的姿态、自由的心灵、远大的目光与火暴的脾气,总是给陈独秀带来牢狱之灾,他一生先后四次被逮捕,每一次胡适都参与营救。
第一次发生在1919年6月。面对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陈独秀十分气愤,与李大钊等人协商,亲拟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对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五条“最低之要求”。这份《北京市民宣言》写好后,交胡适译成英文,以英汉两种文体排版印刷,然后作为传单在北京的娱乐场所散发。胡适也外出散发传单,半夜回到家时,便得到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他动用安徽老乡和媒体的力量来营救陈独秀,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陈独秀最终被释放。
两年后的秋天,陈独秀在法租界被逮捕,理由是“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同时被捕的还有包惠僧、柯庆施、杨明斋和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案情发生后,各大报纸一片哗然。胡适于当晚得到消息,立即打电话给蔡元培先生,请他向法使馆交涉。蔡元培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晨,为陈独秀被捕事,访石曾,访铎尔孟。”过了三天,法国人请胡适吃饭,同席作陪的有法文《政闻报》主笔。胡适趁机向这位主笔提起陈独秀被捕一事,务必请他过问。虽说此时胡适与陈独秀在政治上已有了较大的分歧,但他以友情为重,设法营救陈独秀。最终在刘海粟、孙中山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陈独秀被释放,以“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作了了结。
第三次被捕是在上海,据说是有人造谣中伤,法租界捕房为了敲竹杠,将陈独秀投入监狱。次日晚上胡适在北京得到消息后,马上给当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写信,请他与法国驻华公使直接洽谈,无条件释放陈独秀。这封信确实有效果,在1922年8月19的日记中,胡适这样记道:“今天顾少川(顾维钧)的秘书刘打电话来,说顾君得我信后,即派他打到法使馆,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法公使即发去上海,今天已得回电,说独秀罚洋400元了案了,也没有逐出租界的事,我写信去谢谢少川。”一个月后,陈独秀突然出现在胡适面前,胡适惊喜万分,两个人谈了很久。
最后一次入狱是在1932年10月,******逮捕陈独秀的理由是后者“专事****”,决定“迅予处决”。千钧一发之际,胡适联合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学者名流急电******,反对草率处决,要求交由司法部门作谨慎处理。同时,胡适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亲自出马作《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学术报告,争取各界同情与支持。迫于舆论压力,“迅予处决”的说法被收回,陈独秀后来仅被判处13年徒刑。虽然挽救了陈独秀的性命,胡适仍不罢休。1937年8月,******派他到美国去进行外交活动,胡适利用这一特殊身份,给当时大权在握的汪精卫写信,请汪与******商谈,提前释放陈独秀。8月23日,陈独秀果然出狱了,他辗转幽居江津。多年后胡适“请他(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以“烦见生人”为由婉拒了胡适的好意,最终在江津寂寞地作别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