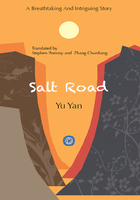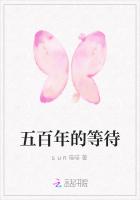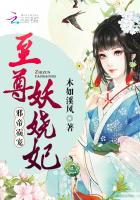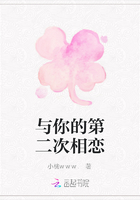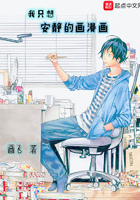陶方宣
《胡适评传》的作者、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说:“在时代的潮水中,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侵蚀。个人的生命是时代的生命,个人的消逝是时代的死亡——至少部分是这样。”这句话用在胡适身上,是多么贴切。
经常有人用“高处不胜寒”来形容胡适这样的大家,可我从来不觉得大家是孤立在高处,胡适当然也不例外。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孤立的人,从文化角度来说,人更不可能孤立。事实上所有的人类都受着文化的制约,个人永远都跻身在时代之内,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密不可分,他就是时代的一部分。胡适是这样,鲁迅也是如此;凡高是如此,贝多芬也是这样,古今中外的文化大家、艺术大师无一能幸免——大师只是那个时代某个领域最突出的代表,一片森林中,不会只有它这一棵高高耸立的苍天大树;芬芳满园的花圃里,不会只有它这一朵娇艳鲜花。林木葱茏,才会显得生机一片;群芳争艳,才会让人赏心悦目,杰出人才的孕育也是如此。在诗歌鼎盛时代,李白的出现像彩虹横天,但是他在那个时代出现一点也不偶然,在李白的周围,有无数诗歌星座在闪闪发光:杜甫、王维、岑参、杜牧、孟浩然、白居易、王昌龄、陈子昂、刘禹锡……是他们组合成浪漫而瑰丽的盛唐气象,就像凡高身旁有莫奈、塞尚、高更一样,就像贝多芬身旁有海顿、马勒、莫扎特、舒伯特、布鲁克纳、约翰·施特劳斯一样,就像莎士比亚身旁有福特、马洛、本·琼生、韦伯斯瑞一样——巨人从来不会单个地孤立地出现,大师只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是森林中最高大的一棵,是花园里最鲜艳的一朵,而不会只是其中唯一的一棵、一朵。大师其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高,他的出现预示着一个群体的崛起、一个时代的崛起。
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写胡适的。这一年间除了本职工作外,业余时间一直埋首在大师胡适的气场中,我认识了他和他身边无数布衣文人和清贫书生,同时也认识了那个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口头禅:我的朋友胡适之——从我这个角度看,朋友胡适和胡适的朋友们,每一个人都那么可爱、丰富而富有质感,饱含意蕴,就像他们已载入史册的名字:邵洵美、苏雪林、蒋梦麟、辜鸿铭、陈寅恪、徐志摩,还有陈独秀、蔡元培、章士钊、沈从文、汪静之、陈衡哲……实在太多了,无法一一罗列,我只能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他们的交往、他们的故事,让我有机会潜入历史内部,号准了时代的脉搏——所有的记录都在这本《胡适的圈子》里,这个“圈子”群星璀璨,熠熠生辉,映照出时代清晰的容颜,我们可以对比着认清自己跻身的时代。这句话其实也可反过来说,我们置身的这个年代也可以映衬出胡适那个时代,那是新旧交替的民国时代,一方面八股文盛行不衰,一方面新文化运动风云激荡;大都市有飞机、电影,有与欧美同步的现代文明,也有四世同堂、妻妾成群和千年不变的古老生活——生活表面的色彩缤纷源于社会内部的巨大蜕变,它当然会投射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特别是那些领风气之先的文化人。比如胡适,他首倡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第一次文化大碰撞,如同吴刚遇到嫦娥、天雷勾动地火。当然,仅仅是胡适一人显然反映不出时代的全部,我将他当成一个纲,与他交往的人都是目,纲举目张,每一个人都显露出鲜活生动的一面,他们的人生侧面、命运走向、性格形成、思想脉络以及生活中的趣味细节、花絮点滴,全都不是偶然的,你都能在这些有趣的人生小故事中,看出一个大时代的鲜活容颜和有力心跳。如果说纲与目结成的是一张细密的网的话,那我希望这张世情之网所打捞的,是对时代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探寻——表面看来,我写的只是一些人物片断,但是人生就是由一些片断组成。每一个人生,事实上都是处于时代与历史的坐标之上,都是时代或历史的一部分。
李敖说“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他说得没错,但是在我看来,人物就是露出时代海面的“孤岛”,所有的人物组合在一起,就是浮出海面的“珊瑚群岛”。而胡适就是一座山峰,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也绝对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山峰,在它的周围,有一片奇峰耸立、绵延不绝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有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冈底斯山脉,正是这条条山脉、座座奇峰,组成了让人仰望也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