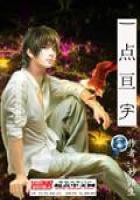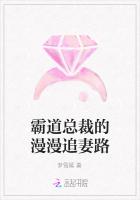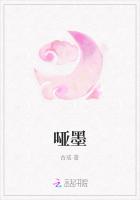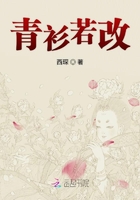戴安娜从一个不谙世故的纯洁少女,到众人瞩目的王妃,最后公然与王室决裂,同查尔斯王子离婚,这一非凡的经历充分说明她性格的鲜明性。人们过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于她的柔美、妩媚、温顺的女性性格上,而忽视了她的性格叛逆的另一面。叛逆和柔美似乎有水火难容的矛盾,却又鲜明地集中在戴安娜身上,构成了她短暂一生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两种性格的融合,才造就了戴安娜的辉煌与不幸。假如她是一个“丑小鸭”、“灰姑娘”,那肯定成不了王妃,也就避免了许许多多的人生不幸和失败。作为王妃,戴安娜的确享受到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荣华富贵,但她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常人无法想像的。假如她没有叛逆的性格,屈从于王室的清规戒律,逆来顺受,不同命运和现实抗争,那么即使她仍然是举世瞩目的人物,人们对她的认识与评价,可能不会是今天这样。
戴安娜小时候的性格是柔弱的。在她幼年时代,父母离异给她造成了巨大心灵创伤。当时,戴安娜年仅6岁。
在庄园里,戴安娜和弟弟由父亲抚养。她常常和弟弟一起度过漆黑的夜晚,也学会了体贴照顾弟弟、照顾别人。这段痛苦的记忆给戴安娜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她曾对保姆说,她长大以后决不离婚,不让自己的孩子遭受离异的痛苦。事与愿违,她长大之后也与自己的丈夫离婚,把自己幼年时代的痛苦经历留给两个亲生骨肉。所以说,幼年时代的戴安娜并不是日后那种强烈的叛逆性格,相反她是柔弱性格。
戴安娜品质良好,在校期间乐于助人的行为品性也为她赢得了荣誉,多次受到校方的表扬。父亲见戴安娜学习成绩一般,便把她和姐姐送到瑞士一家礼仪学校学习,但戴安娜在那里只呆了两个星期,所学到的惟一一项技能是滑雪。
离开学校的戴安娜,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待业青年”。她说服了父母,独自一人到伦敦谋生。戴安娜能够把握住自己,不吸烟、不喝酒,也没有其他不良生活习惯和嗜好。戴安娜生活上洁身自爱,在与查尔斯王子接触前,她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男朋友,更不懂什么是性生活。
这时的她还是一个纯洁的无忧无虑的女孩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子邂逅,王子便在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同时,19岁的戴安娜也赢得了查尔斯王子的好感。
1981年7月29日,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举行了异常隆重,耗资近10亿英镑的“世纪婚礼”。婚后,戴安娜正式成为王室的一员。一个普通的少女成为了王妃,不仅是身份上的改变,还意味着她的一举一动都不是个人的事,而是王室的形象。戴安娜在英国王室女性成员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除了伊丽莎白女王和王太后之外,她作为王妃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她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个人行为,都要注意形象,因为她的一举一动都代表英国王室的形象。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突然间受到王室种种清规戒律的约束,而且要毫无差错地遵守各种她非常陌生的“清规戒律”是非常困难的。戴安娜有美貌,有气质,也有自己的个性,她不遵守王室的规矩必然要同王室发生矛盾。在她面前有两种选择:要么“戒掉”自己与生俱来的个性与从前的生活习惯,服从王室的规矩,做一个逆来顺受的、合格的王妃;要么保持自己的个性,追求一个真实的自我,充当叛逆王妃。
起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戴安娜选择了对王室的适应,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改变自己的性格,朝着王室期待的那种合格王妃的方向努力。然而她成为王妃后,一下子成为了举世皆知的明星。各种新闻媒体对她的关注热情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她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脱媒体的视线,这种生活令她感到窒息。
在戴安娜成为王妃前,在她的心目中,查尔斯不仅潇洒英俊,更具有神圣感和神秘感,她所向往的婚姻是一种童话王国里的婚姻。然而,婚后令她仰慕的王子变成了普通的男人,缺点也逐一显露,婚姻的目的更使她心寒意冷,所以,婚后的戴安娜很快便发现家庭和宫廷是一样的,没有她希望的那种温暖。尤其是她寄予无限希望的、年龄比她大许多的王子对她的爱并不像她期望的那样深沉和热烈。
虽然如此,戴安娜还是努力去适应王室的种种规矩,认真出席各种社交活动,然而她总是甩不掉自己的想法和做事方式。
事实证明戴安娜的做法并没有错误,她能够在公众面前获得其他王室成员从未获得的成功,这说明了她与王室所规定的那套做法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她对王室的种种“不适应”,以及“蔑视”王室规矩的举止言谈,不仅使王室成员“大失所望”,就连一些在宫廷服务的工作人员也议论纷纷。除非她能够认同王室的一切,否则孤立和遭到指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以她叛逆的性格,她决不会违心地顺从王室的清规。
对戴安娜的脾气和个性失望最大的人非查尔斯莫属,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和王子的关系已达到无可调和的地步。戴安娜不得不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在宫廷中,所有的一切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可谓身不由己。戴安娜犹如笼中的“金丝雀”一样,高贵,但缺少自由。而在宫廷之外,她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耀眼的明星,尤其在衣着打扮和发式上,她几乎牵动着全世界所有爱美的年轻女士们的神经。仿佛戴安娜就是时尚、就是潮流。
戴安娜的种种举措,越来越与王室的种种规矩格格不入。在以保守闻名的英国王室中,她眼里最为普通正常的行为,也得不到理解。比如,在她的孩子参加体育比赛时,她也会像普通的母亲一样,光着脚冲向终点;她亲自到服装店里为孩子挑选衣服。她让孩子接受一种王室从来没有过的教育方式,目的是想使孩子真正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所有这一切,都与王室的传统和规矩背道而驰。王妃怎么能和普通人一样呢?王室不理解,更不能容忍。王室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叛逆性格突出的王妃,而向往自由的戴安娜,自然也无法接受王室的种种戒条。当这些戒条在戴安娜身上最终失去效用时,她自然会离开对她来说是“冷宫”式的宫廷。
戴安娜的叛逆性格在宫廷中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服饰。戴安娜早就“破除”了宫廷对于女性成员着装的不成文的规定。她的服饰五颜六色,式样多种多样,从鞋子提包到帽子服装,从头到脚,都独具特色。从服装样式上看,王室的各种规矩已被她彻底抛弃,她不仅有雍容华贵的礼服,也有许多新颖别致的服装,一些王室女性成员不敢或不能问津的性感服装,戴安娜也来者不拒,身着三点式的各种照片已屡见不鲜。戴安娜着装上的开放性,鲜明地表现了她的叛逆性格,这已不是英国王室王妃形象了。尤其是那些大胆、暴露的服装,显然不是英国王室成员所能接受的。在戴安娜的服装中,类似的服装绝不止一两件。她在以自己的叛逆性格、以叛逆的实际行动向传统发出了挑战,向王室发出了挑战。戴安娜在穿着上展示了自己的柔美,同时也反映了自己的叛逆个性。在选择实现自我和女性天性时,戴安娜把王室的约束置之度外。在权利和义务上,她也是最终选择了自我,叛逆的个性,使她与王室走得越来越远。
1996年2月28日,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子正式离婚。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世纪婚礼,以有着同样巨大轰动效应的离婚而告终。离婚后的戴安娜依然是那么迷人,魅力不减当年,媒体效应丝毫未减,各种媒体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戴安娜离开了宫廷,实现自我价值,可以自由地支配自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中。离婚前,戴安娜不仅是“国际服装大使”,更是一位出名的“亲善大使”,曾在100多家慈善机构兼职,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副会长职务达13年之久。世界上许多地方留下过她的足迹。
1989年,戴安娜访问美国期间,在一家医院,将一名年仅7岁的爱滋病患者紧紧搂在怀里。所有在场人无不为之感动。离婚后,她代表国际红十字会来到饱受战争折磨的安哥拉,步行深入到已有7万人死于地雷的地区慰问。
戴安娜的这一勇敢行为再次引起轰动,得到了各方面的褒奖,无怪乎诺贝尔委员会提名她为当年度和平奖候选人。
以上种种所为哪能是王室王妃所为?而且更不是那些保守的王室王妃所能做到的。
假如说,戴安娜的叛逆表现在他同王室的公然决裂上的话,那么她那特有的女性柔美,则集中表现在她的爱心、善良等方面。她始终以美丽、真诚的微笑面对公众,把自己的爱心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戴安娜曾帮助过一位身患绝症的女孩。一次,女孩和母亲到医院体检时,母亲忘记带内衣。戴安娜马上将自己的内衣借给这位母亲,并吩咐人把这位母亲换下来的衣服带回她的住处洗涤。1997年,她把自己79套豪华晚装拍卖,所得320万美元全部捐赠给了抗爱滋病协会和抗癌协会。类似行动,不胜枚举,如此人称戴安娜是“人民王妃”应是她成功的体现。从“叛逆王妃”到“人民王妃”,看似简单的称谓变化,实际上揭示了一个内涵非常深刻的问题;人民是人民,王室是王室,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称呼的转变从侧面反映了戴安娜的性格。
戴安娜永远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她自己也左右不了的。美貌的戴安娜还和年轻时候一样,有众多的追求者。但她与异性交往麻烦太多,当戴安娜和亿万富翁的儿子多迪·法耶兹相恋后,一些以搜集花边新闻、名人绯闻的记者们对这对恋人围追堵截,戴安娜几乎是走投无路,插翅难逃。
1997年8月31日,为躲避这些记者们的骚扰,戴安娜和多迪的汽车高速行驶,结果发生车祸,戴安娜不幸身亡。
戴安娜由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变成王室王妃。但叛逆的个性注定她不是王室合格的王妃,而是人民王妃,也是叛逆的个性让她过早地走完了人生之旅,但她的一生是伟大而又完满的一生。
“怪人”并不怪,实话决不顾情面
一提起辜鸿铭,人们的脑海里总是想到这样一个形象: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在五四新文化的氛围里拖着一条大辫子,穿着长袍马褂走在路上的人。辜鸿铭一直是中学课本里“保守”、“反对新文化”等名词的代言人。但实际上他学贯中西,有自己的想法,并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正是他性格叛逆、坚持的一面。
“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是文化界、教育界最活跃的一块领地,中西方的各种学术在这里都异常活跃,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他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来者不拒。当时各路人马纷至沓来,有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这些新派人物执教,也有坚守中国国粹的复古主义,如刘师培、辜鸿铭等人。
而当时的情况,无疑是新派力量占据上风,而辜鸿铭不为所惧,依然故我,即使群起而攻之也岿然不动,与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
辜鸿铭以他的怪癖成为20世纪20年代轰动京城的一位争议极大的人物。他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对于西方世界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有名的”,勃兰兑斯说他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
1856年,辜鸿铭出生在槟榔屿的一个贫苦的华侨家庭。在他八九岁时随一位牧师到英国读书,后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那一年他23岁。之后,他陆续去过德、法、意、奥进修,获得过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达13种之多,在众多博学多才的中国学者中是极为罕见的。他对英、法、德、意、日、俄、希腊以及拉丁文,无不通晓。他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已达到很深的造诣。
他不仅是语言天才,更是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他在东交民巷的六民饭店作英文讲演,题目是《中国人的精神》,凭票入场,每张门票售价二元,打破以前学者演讲无卖票之说的旧习俗。辜鸿铭的演讲在北京的外国人很多都到场了,座无虚席。
他在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他在讲授英国诗时,所举诗人的作品,脱口而出,不假思索,与诗集对照,分毫不差。对于他惊人的记忆力令很多人,包括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据女作家凌叔华回忆,辜鸿铭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差地当众背出千行弥尔顿的《失乐园》,证明他确是具有非凡的才华。
在课堂上,他挥洒自如,海阔天空,旁征博引,充满了幽默诙谐,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用中文来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来回答中文问题,中间又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阅历之广泛、见解之独到、议论之锋锐令所有人瞠目结舌。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他又是怪诞的。提起辜鸿铭,首先想到的民国以后他的那根在北平知识界堪称一绝的辫子。在民国时代,他坚持保皇。在北大校园里,他戴瓜皮帽,穿方马褂,顶红缨辫,穿双脸鞋。这样的打扮讲授英国文学总不免滑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疑是另类的,前卫的,也让人佩服不已。
有一次,一位新应聘而来北京大学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里,看见一位穿着长袍马褂的老古董,拄着根手杖,坐在沙发上运气。这位英国人向教员室的侍役打听,这个拖着一根被英国人蔑视为“pig tail”(猪尾巴)的老头是什么人?
辜鸿铭就与他交谈起来,听说他是教英国文学的,便用拉丁文与他交谈。这位教授颇为尴尬,因为他实在回答不上,辜鸿铭感叹道:“连拉丁文都说不出来,怎么去教英国文学?”不顾这位教授的情面,拂袖而去。
他的种种观点与当时提畅的新文化背道而驰,所以一向被人认为“怪”。一位外国太太反对他所认同的纳妾的主张,直问他,既然你认为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那么,一个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个丈夫呢?辜鸿铭对她说:“尊敬的夫人,只有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没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道理。”
他曾经说过蔡元培作了前清的翰林之后,就革命,一直到民国成立,到今天,还在革命,很了不起。他说他自己,从给张之洞做幕僚之后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现在,还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因此,他说在中国只有他们两个堪称表率。
辜鸿铭的一生总是在逆反中度过的。大家认可的,他要反对;大家喜欢的,他不喜欢;被崇拜的事物,他藐视;人人不屑的,他要尝试,追求与众不同,成为他的快乐和骄傲。
慈禧过寿,万民共祝,他却公开指责“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他有着自己鲜明的善恶标准,但他又是彻彻底底的保皇党,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堪称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