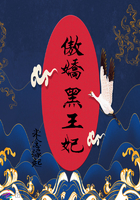在这本诗集里面,我们看到了相当多的几乎是非常古老的诗歌形式,最为简洁的文字。它们有着古代谣曲的风味,但它传达的依然是现代人的感情。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诗歌的时候,不会拘泥于它基本词汇的古老,而是会感觉到古老诗歌在诗人内心血脉中的崭新延续。如果说在日常对于诗人古马的阅读中他的“古老”意味还不够鲜明的话,那么,在这本集子里面我们看到了古马的全然面貌。古马甚至是在相对冒险的形式,无畏地以许多诗人放弃的形式,重新点燃了古老的诗歌火花,而那些古老的火花,在古马的妙手之下“回春”一样在一个迥然不同的年代重新绽开。这些诗歌在和许多诗歌语言非常现代化的诗人的作品相比之下,这样诗歌是停下来的,时间是停留了下来,人是停留了下来,但是我们在这样的停留之下,感受到了更具恒久性的命运般的诗意延伸。这样的诗歌似乎是多么古老,但在这一麻间,它们年轻得可怕,直接就渗透了我们的脆弱。我们恍惚是在某些不能确定的年代,我们是在古代,也是在现代,而时间瞬间穿过了我们。
古马的冒险,不仅是在将古代诗意地横移,而将时间打破。古马甚至会尝试着将民间流传甚久的传说、禁忌,以至于某些咒语一样的东西引人他的诗歌,以便呈现诗歌(文本)的原初化。在古马长达十三节、一百多行的诗《西凉谣辞》中,诗人将人类生活中更为古老甚至是神秘的成分,通过古老的词汇加以呈现:“新鬼殷勤,头上顶着沙葱”,“夜半鬼捣地//无他,无他//屋后萧萧白杨/鸱枭哭”,“野鼠窥星宿//莫睡,莫睡//银簪子挑灯人等人”。
这样的诗歌,它内在的东西本身就有着和谐与不和谐的矛盾,有着笼罩着人气的巫气和鬼气,但是我们从这样的场景中感受到了我们日常所感受不到的,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始终不给我们所真正感知真正可以确定的世界。诗人对这样诗歌的处理是宁静的,他的耳朵和眼睛在这样宁静中,无限地感受着,而就在这样无限的感受中,世界也变得无限了。一切都是在一起的,没有时间和空间,没有虚和实,没有生死,只是一种“在场”。
但在这样背景下的古马的诗歌并非没有现代诗歌的强韧肌理:“火车奔向落日/谁在用一根线穿针”(《无题》)。“当一只羊死去的时候/它会看见:/流星/把一粒青稞/种在来年春天的山冈”(《秘密的时辰》)。“雪山围拢着牛羊/水围拢着火/一朵燃烧的白色的花/一只溺水的女人的手/在黑暗的旋涡中世界,我要为你生育”(《生命》)。
这样借助了大量古老词汇的诗歌,它所呈现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必须用现代诗歌的感受来处理了。其中,甚至有一些展现了相当“艰难”的意义,比如“世界,我要为你生育”这样的句子,解释起来是要用相当笔墨的,甚至是需要用许多艰涩的哲学语汇的。它所带来的现代意义上的深度,不是简单可以界定的。而在这样的诗歌里,我们看见了更为“中国”的东西。
在《车轮》里面,诗人从“薄雾漂流,寒烟四起。/落日,少妇的紫皮独头蒜及时成熟。及时成熟的当然被及时运走”写起,到“——生死总是血脉相通,岂止生死才是血脉相通啊”!这样韧性十足的诗句,有力地抵达了现代诗歌的最深层。这样的诗歌,抓住了永恒,也使我们对老的词语可以再度景仰。
七
2004年1月,《中国诗人》在“开卷诗人”栏目发表《古马诗十七首》及我的评论《沉静与锋利:读古马诗以及对诗歌的若干思考》,同时配发了诗人的多帧生活照。
《古马诗十七首》是古马2000年以来最为重要的部分诗作。
作为诗歌的阅读,是几乎没有什么责任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谈论诗歌都是危险的。美国学者奚密(英文名MichelleYeh)在谈到诗歌的阅读时说:“我个人读诗的心得是,越丰富尤其是有些‘异常’的诗歌,诗歌内部,尤其是杰出的作品,其内部都有难以言喻和勘破的东西。可以阅读,但是你似乎要说出来一些什么的时候,就艰难了。仅仅具有单一层面的内涵,只能允许单一切入点的作品,很可能不是一首好诗,因为它太狭溢、太平面化。一首好诗给人的阅读经验应是立体的、多向度的。”那些杰出的作品,也许只是诗人内心的一道裂纹,那道裂纹上微妙的光照。面对这样的作品,评论家只是在冒险。尤其在好的评论家极其罕见的时代,更是让太多的评论“无奈”。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尊重少数一些评论家,比如陈晓明,他对孙甘露的评论,就让我看到了他无比犀利的眼力,这样的评论家甚至比作者更加深人地解析了作品,在那样的评论过程中,他们的忧喜,已经完全渗透了语言进展的每一刻。谈论古马的诗歌,同样面临这样的危险。我不是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好的诗歌,我只是说,首先,他有相当数量的好诗;其二,他的诗在不断的推进过程中,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需要了解这种“变数”。
但是,这些诗歌,是我们面对的时候,必须要谈论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古马是一个抒情诗人,这一点古马自己也并不否认,坚持纯诗写作,这是他的诗歌倾向。
对于这组诗歌,让我们尝试着做以下细读:
我一直以为,纯粹的诗,可能更加需要在形式上“挤住”。好的诗歌,无疑需要更为紧凑。古马的诗歌,甚至在三四十行这样篇幅的纯粹的抒情诗,也同样能将情绪和感受“挤住”。《夜雨》就是这样。这是一首诗人纪念去世的祖母的诗歌。前面两节:
荆棘是冰凉的
头戴紫荆冠的亡魂
带来野径上的黑云
和陈年的蘑菇
三十七口井的村庄
一座白杨树环绕的庭院里
西红柿和庙子在暗中
竞相生长
这样的描写,在其他许多诗人的笔下都会出现,但是他们不会这样深人地“挤住”。一切都是生命,陈年的蘑菇和新鲜的在暗中生长的西红柿和茄子,都是物竞天择的生命。生命是以黯淡的方式生长的。这固然是由于悼念的缘故,但更多的是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这样独特的开头,接下来才是“堂屋里的灯光/夜里深坐着的亲人们/还在说着远行的人吗”那样的接近传统抒情诗的调子。但它的重要在于开头那样一种调子。那不是所有诗人甚至是好的诗人都会写的调子。虽然我还要说的是,我在阅读的开头就希望诗人写成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形式,只是这么去写,不着一个字的祖母,而尽得“满目凄凉”。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古马亦十分欣赏乔治·塞菲里斯在《安东尼奥》里对诗的理解:“在某个煤窑的最深处,最后往往会有一匹白马,而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便是不惜一切代价把那匹白马找出来。”也因之他的诗歌里面会有一些有意识的“拼贴”或日是将很难共处的“并置”在一起的东西。这不是“黔驴技穷”,而恰恰是古马为诗歌技艺的“殚精竭虑”。比如《给秋月的四支短歌》,里面就有这样一节:“哦/你若说出‘爱’/月光就像飞速打开的绷带/而世界则像一个病人/被幸福缠绕”。这不是寻常的手法,从爱、月光、绷带、世界、病人、缠绕,这是异常的,但将这些词语并置在一起,迅速推动,可能这样才能更深入地表达内心。这无疑是更深一层的东西。这样的诗已经是他的创竖,语言节制而流转,抽去了多余的语言,只是一些浓烈散发着生命味道的词汇,让人再次触及了生命的原初和苍凉。
但古马重要的诗歌,也许还有一些,是那种将自然和人类情绪密密挤压在一起的诗歌:“坐在暴风雪中心给你写诗/最后十行/冻僵的十指围拢着马灯/是肋骨,也是圈不住火的马厩”(《马灯》)。
这些诗歌在你阅读的过程中瞬间就打开了,蔓延,浸透了你,让人难以喘息。
古马亦有偶然出格的那样一些作品,如他的《忘记·:“……但所有‘一’让我忘记的并不都等于零/瞧,我描画的一棵洋葱/它能够说出你栽种在地球以外的水仙的品性”。
诗人里面,古马是少有的好记性。这样的“记性”,也势必会影响到他的创作;这样的记性让他在阅读时,不断地对所读作品发生记忆,这种记忆久而久之,就会发生“横”的影响。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记忆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
古马有这样的句子:“森林藏好野兽/木头藏好火/粮食藏好力气(《大雨》)。羊的圈草去修/草的家水来当”(《银手镯》)。颇具创新意味的音乐家谭盾,在有些人眼力是音乐的叛徒,但那些在舞台上的水的声音、纸的声音,一些更具物质本身的材料发出的声音,很早就是原始人的音乐了。音乐在恢复它的本真,人们已经厌恶了虚饰,需要锋利地透过虚饰,进人神秘的生命和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诗歌亦然。
古马的这一组诗歌里面,在形式上借鉴于《诗经》的作品就有数十首之多。甚至一些诗歌干脆就借用《诗经》里诗篇的篇名。借用这样一种形式,虽然在客观上可以给人一种新的感觉,但古马恐怕考虑的不仅仅如此。我们可以试着做以下比较;首先是在形式上,《诗经》的表达形式,主要是采用四字句和隔句用韵,间或有三字、五字、六字、七字的。在篇章结构上,多采用重复回旋以加强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在内容上,无疑古马更多的是研习了《国风》和其他一些民歌、谣曲里的原始(不假修饰)风味的部分。这更本质的东西,对于现代诗歌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感受力在现代生活里,不断受到磨损。沉到底,也是一种可能。重新去研究原始的比较原始的艺术,以便从根本上再次恢复我们的艺术创造力,毕加索就是一个例子。没有原始人发自大地和生命的艺术爆发力,他的艺术会“精巧”得多,而创造力则会少很多。那样的艺术是朴实的,可以浓郁地散发自身气味的。在艺术家无能为力的时代,重新学习更为古老的技艺,无疑是正确的。虽然,这只是古马艺术的一个分岔。我的意思是说,古马不会极其认真地把自己放置于这样一条道路,这样一条道路虽然也会成就一位诗人。它只是诗人尝试的一种可能,是他的一种“情变”。
古马不止研究过一种民歌,他研究各种各样的民歌,尤其是现在还在民间流传的歌曲。那些民歌是和它的曲子一起流传着的。古马唱得最好的是那种野地里的臊人的带着地方口音的武威民歌。奇怪的是,那些有些酸甚至是色情意味的句子,古马唱起来却十分痛苦。那些句子也真是好:“大路的边边,凉州的哥哥,你回去了不要给我的娘家人说,一晚上红柳的叶儿往下落,红绸的裤裤儿(嘛)往下脱。”这样的情歌,每每会叫古马落下泪来。当然,这些借鉴也存在许多问题。如果说现代小说与古典白话文之间的关系,要比现代汉语诗歌与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密切得多,也就可以说前者是继承关系,而后者则更多的是断裂的关系。古马的这些诗歌,并不是旧瓶装新酒,而是“永恒”装“永恒”,是一种不新亦不旧的诗歌。处理得好的,滋味独特;处理不大好的,需要解决一个“硬”和“生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