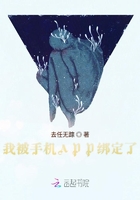唐娴连续好几天站在路旁,等着向见过世面的人打听存单的兑现地,奇怪,自那天以后,没有司机对她的招呼有反应,这等于又一次陷入了像从前一样的苦境。虽然,她并不甘心认可,但这么被冷落在公路边上除了陡增失落还能得到什么。
晚上,女儿问她是否找到了父亲的地址和兑换存单的地方,她开始失望地摇头。安琪儿照例伏在桌子上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唐娴在脑海里不断地寻找能够完成任务的办法,她想起了胡福,只有他能够知道人们的去处。“是啊,他有多年不见了,要是能够碰见他就好了。”她自己独自叨唠着。
女儿问她:“你说的是谁?”
“胡福,你见过他吗?”唐娴激动地问。
“看你神经的,我好像见过,不过我忘了。”女儿回答。
“过去他总是那么勤勉,能够及时地带领现世的人迈过那道门槛。他的确知道人的归宿,可是现在人死了只是自己剪些纸钱,根本不管用。”母亲埋怨着胡福。
“那么人死后有什么区别吗?”女儿问。
唐娴坚定地回答:“只有胡福能够打通未来之路,由他的钱铺路,才能够找到通向那个世界的道路,大门才能够打开。所以,死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小睡一会,如果像现在这样,自己剪些纸钱铺路,死人到达的只有墓地,真的死了。”
唐安琪像听故事那样听得津津有味儿:“你是说爸爸他已经死了。”
母亲思考了一下,显然,依然在世和死亡是有区别的,她得要先解决这问题再回答女儿的问话:“我看,如果人不死,也就说不上是死,亲人暂时离开你的这个时间无法确定,所以,只要那个人不在你身边,他就是离开了你,胡福就是知道他的下落。没有胡福撒钱送行的离去,你看到将人埋入墓的,最后人就化成尘土啦。这与胡福没有关系。”
看来这只是唐娴自己的解释。她向女儿表示:如果有机会见到胡福,一定要向他讨教这个问题。
“那我们都等着胡福为我们送行,这样,我们全家还是有机会在一起的。你不是说爷爷、奶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吗?胡福也知道吗?”安琪儿天真地联想起来。
翌日,唐娴依然到公路上去碰运气,她这次倒不指望能够有人知道到哪里兑换存单而是去寻找胡福的踪迹。看来胡福也是一个希望所在了,不是吗?原来他经常出现在村民们的眼前,村民们只认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谁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现在连这个能够阐述未来的家伙也消失了。至少村民们一直这样认为,生活在“楚乐庄园”的人们在需要他的时候深感无奈。庄园上一个叫玲竹的老妇像唐娴一样,早年丈夫外出未归,并没有留下后代,只身寡居,人世凄凉,由于自己年事渐高愈加地希望能够见到胡福,能够在末期时为她送行,以期找到离去多年的丈夫。
唐娴才到公路的边上,发现百米之外站着的玲竹,于是,便赶过去问他等谁,当听说老人家也在等胡福时,唐娴顿时觉得心里有了安慰:“看来,有那么多人在等着胡福作出回答,他是不是欠我们的账。”
“人家欠我们什么账,‘楚乐庄园’的人不是都快忘记他了吗,尤其年轻人都忘了祖了,他们想得开,甚至丈夫失踪了,媳妇丢了,几天就忘了,要不就换一个。嗨!还是他们想得开。也不顾虑一下这辈子快完了时候的出路。”玲竹回答。她们向道路的尽头望了一眼,就相互交谈起来,有了能够倾诉的伙伴,失落感就少多了,对于胡福的到来,唐娴认为:“只要心诚,他自然知道的。”玲竹老婆婆也同意她的看法。
两人结伴,有说有笑,等了三天,要说的内容也说完了,除了飞驰而过的车辆,连胡福的影子也没有发现,老婆婆有些慌张起来:“那个熟悉的胡福不会真的永远就没了吧?”
“你老怎么会问出这样的话来,我不是告诉你心诚则灵吗。”唐娴尽管也怀疑胡福是否消失了,但意志不愿意这样承认,她知道胡福要是真的消失掉,她就没有什么指望了。说来,像唐娴这样的女人靠希望活着还是值得自豪的,庄上更多的女人都指责她过于痴情,女邻居们也多了一些消遣的内容,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像说戏那样打发时间。
尤其那个长得像个黑熊一样的胖娘儿们,两只小笑眼总是让人觉得肚子里有装不下的坏水,说到高兴的时候一对肥硕的乳房跟着一起跳跃:“这唐妹妹也真是够专心的,人都走了那么多年,就是回来,恐怕她也不认识了,把青春都给耽误了,男人不在身边还有什么快乐,希望解不了渴。要是轮上我早就换他几个了。你们想想,这整天往公路上一站,多饥渴呀!”她一边打趣一边就咯咯地肆笑起来,然后,就东西不分的插着各自的观点。
她们是坐在能够远远望着依稀可见的公路,对着一个活生生的对象进行评论的,所以,这些娘们儿们自然很开心了。紧坐旁边石块上的黄脸婆又加着佐料:“这一阵子又多了一个玲老太太,恐怕她也梦着胡福能够带她到青春的年头上与老爷们欢一回。”
又是一阵开心地大笑。
这些女人的日子过得可谓舒坦,不像唐娴的日子总是在等待中充实。她毕竟是读书人的女儿,她把追求希望看得更重了些,然而,希望如果迟迟地得不到回报,她不能不在心灵的深处怀疑希望值不值得留恋,她甚至不再清楚回答希望的内容。每每面对那些女人们尖酸语言的挑衅,她只能默默地坚持着。好在玲老婆婆还能成为倾吐对象,面对那些女人们的奚落,她也有自己的回答:“竹婆婆,你说,人要是没有希望,不就更像一头活着的猪吗?”
老婆婆看了她一眼,没有回答。那是她最后给她留下的一个印象。
这一天玲竹没有到公路上陪伴她。她正充满疑惑,有两辆卡车嘟嘟地开过来,又是向她打听道路:“大姐,这里是‘楚乐庄园’吗?”
没待唐娴回答,一股恶臭从车里涌出来,硬是给她堵了回去。她只是点点头就表示出了满意的心情,这是她第二次听到外面的人寻找“楚乐庄园”。
那两辆卡车的司机光着膀子,一口扣着锅样的肚皮使他从驾驶室出来很费劲,他才挤出半个身子就被车门框卡住了,索性又退回了驾驶室。他用一双挂满油脂的脏手挠着浓密的胸毛问是不是从她眼下的路口下道。得到肯定后,就信心十足地“砰”地关上了车门,随着一股浓浓的油烟从车后卷起,卡车摇摇晃晃地向“楚乐庄园”开去。整个空气都弥漫着不散的恶臭,使唐娴几乎呕吐出来。
对于从公路上出现一些不速之客的事件渐渐增多,唐娴也有些适应了。她站在原地目送着两辆垃圾车,她发现司机在那些习惯坐在庄口石块上纳凉的娘们儿面前停下来,从驾驶室下来的那个长满胸毛的司机与叫“熊姐”的那个肥女人聊了有一刻钟的工夫,能够隐隐地听到娘们儿的笑声。之后,汽车的后箱盖就自动打开了,从上面卸下一堆黑乎乎的东西。那辆车也是这样。等那两辆车转过来继续从唐娴这里经过时,司机便主动隔着车窗与她搭讪:“唐女士要在这儿等胡福吧?他离这里不远,就在前面的城里,胡福早搬到城里住了。有机会到城里找他。”
说完司机一加油门,汽车“嗖”地一下就窜了出去。得到胡福的消息,本来挺高兴,想再向司机探讨也没有机会了。
其实,是那个胖娘们儿告诉司机的,司机才不知道胡福在哪儿。在唐娴悻悻而归后才清楚他们卸下的东西,那些垃圾几乎什么都有:有铁片、塑料、瓶子、烂纸、腐烂的食物等。她根本没有见过这些东西。这些垃圾就堵在道路的中央,她只好绕过垃圾行走。那些娘们儿带着筐将从垃圾里翻到的有兴趣的东西放进筐里。周围很快就引来一群群的绿头大苍蝇。唐娴不觉从胃里涌上一口胃液,只顾皱着眉头赶回家。她没有听到垃圾旁女人们的嬉笑。
这一天虽然唐娴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快,但在回家后,还是得到一个很大的斩获:门上钉着一个无名信封,里面装着一个男人的照片。她茫然地沿门前的小路望去,见一辆与上次送存单一样的绿色邮车正背她而去,她不知道这辆邮车与这张照片是否有关系,因而,没有急于要追上那辆邮车,但她还是疑惑地认为,这张照片就是那辆神秘的邮车带来的。她仔细地端详照片上的男人,认定这就是钱记。其时,出了门心的胎记作为认证的标记,一个少小离家成年男人的形象早不是固定的那个样子。不管怎么说,虽说那张大额的存单是一个无处兑现的希望加上这张钱记的近照足可验证希望总是现实的,总可以让她进一步踏实下来。她真的有些按耐不住再次唤起的激动,又急不可待地让女儿见识父亲的样子。原来,安琪儿只是靠母亲的描述在脑海里绘制一个不怎么清晰的父亲,现在看到父亲的照片她惊讶地说:“原来父亲就是这个样子。”那种亲切感和带着血缘关系的连蒂是世界上最真诚的感情之一,她简直爱不释手。
“下一次,你父亲就会亲自到了,你瞧瞧,思念多管用,希望的实现越来越近,先是一封信,接着又是一张照片,下一次还是什么呢?”母亲美好地想象。
“衣锦还乡!”唐安琪肯定地回答。她天真地接着续念:“我们老师告诉我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少小离家闯荡四海,老大后衣锦还乡。”
“让我们等着你父亲衣锦还乡的这一天吧!我要到王木匠那儿去一趟为他打造一个镜框。顺便看看玲奶奶,她也在等她多年前失去的亲人。”唐娴木讷的眼神儿一下子放出光来。
预定了境框,唐娴有意识来到玲竹老婆婆的家。她发现玲竹家的柴门前上着一把铁锁,从门缝看去,那里早冷了烟火,这时脚下的几篇纸钱提醒她主人的去处。她顺手捡起一片纸钱,脱口而出:“胡福来了!”
胡福的纸钱不是人们随意剪造的纸钱,对于虔诚地相信胡福的灵性的人,胡福的纸钱能够变成金色,就像唐娴现在捏在手里的一样泛溢着金色的光芒。
“玲婆婆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归宿。”她自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