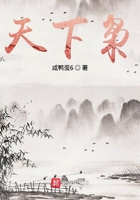“姑娘,你真行。老夫有眼无珠啊。”
分别的时候,崔老爷握着义妁的手迟迟不肯松开,两眼泪花,目光柔和而充满赞赏,义妁做到了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义妁是他这一辈子见过的最好的大夫。
除了诊金,崔老爷还馈赠了一匹绢和一对翡翠镯子给义妁,义妁推辞再三,蔡之仁却说崔老爷馈赠的礼物她没有权利处置,收不收应该回去禀告师父再作打算。崔老爷非常厌恶蔡之仁的嘴脸,这些日子在治疗夫人的病上,他没出一点力气,只在一旁指手画脚。崔老爷呵斥了蔡之仁,说这些礼物是专门给义妁的,给医馆的已经有足够的诊金。蔡之仁只好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盛情难却,义妁只得收下了礼物,回去后,她把镯子分给了采娟一只,采娟欢呼雀跃,搂着义妁团团转。那匹绢也分给了白大婶一半,白大婶抚摸着光滑的绢,爱不释手,直夸义妁的好心。
义妁治好了太医令丞母亲的中风,这事很快就在扶风传开了,义妁顿时声名鹊起,一时被誉为扶风的“女中扁鹊”。扶风县令也不请自来,为鼓励她,还亲自为她办理了医籍。也就是说,从今以后,义妁就是真正的大夫了,她有权利有资格给任何一个病患看诊、开处方了。这是义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经过她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修得正果了。义妁在父亲的坟前喜极而泣。这愈加坚定了义妁行医的决心。
所有的人都向义妁送去笑脸和祝福,唯有郑无空始终无所表示,义妁明白,师父总是在她最绝望的时候给她希望,在她最荣耀的时候给她提醒。郑无空希望义妁不要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她刚刚取得了医籍,她今后的道路还很漫长。
郑成议也来祝福她,依然在医馆后院的长亭,依然是谦和的笑容。
已经有些时日没有见到义妁了,郑成议有些激动,他总是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她忙碌的时候他克制自己的思念,尽量不去打扰她。
他含情脉脉地看着她,她总是羞涩地低着头,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她总是抬不起头来,虽然他英俊的面孔对她充满了诱惑力,但她却害怕他那能洞穿人心的目光。
“近来过得好吗?一定很忙吧?你要医治那么多的病人。”郑成议首先打破了沉默。
“还可以。”义妁小声地说道,时至小寒,天寒地冻,万物凋零,义妁的双手被冻得通红的,郑成议看了,好不心疼,真想用自己温暖的手去握住义妁小巧的手。郑成议曾经送过一双貂皮手套给义妁,义妁为了保持手的敏感度,一直不敢戴,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戴上。
“再忙也别累坏了身子。那些病患只管自己的身子,可不管大夫的身子。”郑成议有些开玩笑地嘱托道。
“不会的。”义妁笑笑,“谢谢公子的关心。”
“今后你可不可以不叫我公子?”
“那叫你什么?”
“成议。”
“这……有些不妥吧?”义妁心怦怦直跳,犹豫了一会儿,道,“还是叫你公子吧,这样比较顺口。”
“那随你吧。”郑成议有些失望,突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转移了话题,问道:“向姑娘请教一个问题。”
“公子请说。”
“冬天到了,该怎么养生呢?”
“内经说,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祛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疲厥,奉生者少。”
“什么意思呢?”
“冬天这三个月,生机潜伏,万物蛰藏,水寒成冰,大地龟裂,人应该早睡晚起,最好等到太阳出来再起床,不要轻易地扰动阳气。使意志伏藏,若有若无,躲避寒冷,不要让皮肤开泄。如果违反了这个道理,肾脏就会受伤,到了春天就会得痿厥病,供给春季养生的能力就差了。”
这时,杨怀三急匆匆地跑来,说有一个特别的病患要见义妁,义妁很纳闷,什么样特别的病患呢?
“那么,小女告辞了。”
说完,就跟杨怀三走了,只要一提到病患,义妁丝毫不敢怠慢。
郑成议有些失落,他怀藏着的那支步摇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来送给义妁呢。他发誓一定要把步摇戴在义妁美丽的发髻上。他梦里好几次都看见义妁戴着他送的步摇朝他走来,笑靥如花,一步一摇,美妙的姿态多么让人沉醉。
一个贼眉鼠眼、五短身材的男子出现在义妁的面前,这就是杨怀三所说的特别的病患。
“既然是特别的病患,那么应该有一间特别的病舍。”他请求义妁给他一间单独的病舍,他有重要事情跟义妁讲。义妁满脸狐疑,看他言行举止神神秘秘的,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既然是杨怀三介绍过来的,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于是就依了他,领他到了一间空置的病舍,这间病舍是为传染病人特别预留的。
“其实小人并非什么特别的病患,我不是来看病的。如果我不说是特别的病患,估计排上一天的队也见不到姑娘。”
“那么,你是?”义妁早就觉得有些蹊跷,又听他这么一说,不免有些生气。
“小人乃保和堂医馆的刘管家,我们医馆的鲍大夫请您过去一趟,有要紧的事情跟你说。”
原来,自义妁治好了王夫人的中风后,再加之郑氏医馆实行的义诊,来医馆看诊的病患越来越多,新增加的病患都是冲着义妁来的,他们说义妁给他们看诊的时候,目光柔和,让人看了舒心,不像郑无空,感觉凶巴巴的,令人害怕。
几家欢乐几家愁,郑氏医馆门庭若市,而与郑氏医馆仅一里之遥的保和堂却门可罗雀,本来保和堂的鲍大夫医德恶劣,唯利是图,对穷苦病人拒绝看诊,对富贵人家也想着法子盘剥,专门给开一些没有用的药方,没病也硬说人家有病。日久见人心,看得起病的、看不起病的,渐渐地,都不再光顾保和堂。
保和堂的鲍大夫终于急了,可不能这样喝西北风,得想个法子才行!他认为,造成保和堂惨淡经营的首要原因就是郑氏医馆,更确切地说是郑氏医馆里的郑无空和许义妁,是他们把扶风的病患全吸引过去了,尤以新崛起的义妁为甚。目前有一种新的流言在扶风传开,说义妁已经代替了郑无空成为扶风第一名医,还因为她是个女子,民间对她的传奇故事传得沸沸扬扬,就连说书人也不放过义妁,义妁治病救人的故事经过巧舌如簧的说书人一番天花乱坠的评说,往往赢得满堂喝彩,扶风的老百姓愈发觉得义妁不是人,而是神,神女下凡。
“如果把义妁挖过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保和堂鲍大夫打听到,义妁虽然已经是名医,但郑氏医馆开给她的工钱微乎其微,与她的名气相差甚远。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如果给她开出几倍甚至十倍的工钱,他就不相信义妁不动心。只要义妁成为保和堂的大夫,日进斗金就不再是白日做梦了。
鲍大夫的如意算盘打得顺溜溜的,很为自己能想出这样一条妙计而洋洋得意。义妁如今如此受欢迎,盯着她的不止鲍大夫一个,晚一步就有可能被别的医馆抢去了。于是,计谋一出,就立马派刘管家来郑氏医馆传话来了。
刘管家用散碎银子打发了杨怀三,杨怀三拿人手软,就把他引荐给了义妁。
可义妁一口回绝了刘管家,“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病患更重要。”
这让刘管家有些不知所措,无言以对。好在有杨怀三在一旁推波助澜,“义妁姑娘,你还是去一趟比较稳妥,说不定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比如你一直寻找的元尚会家人的下落。”
义妁有些动心,她费尽心思,四处打听元尚会家人的下落,至今毫无结果。找不到元尚会家人,她的身世之谜就无法揭开。
“去吧,去吧。”杨怀三催促着,他自己也不知道鲍大夫请义妁过去做什么,只要不是陷害义妁,去一趟有什么关系呢?
“请问是什么事呢?”
“这个小的也不知,鲍大夫没跟小的说,只让小的务必把姑娘请过去。”
义妁终于点了点头,“好吧,等我结束看诊就去。”
“那好!今晚酉时鲍大夫在醉风酒楼恭候义妁姑娘的大驾。”刘管家拱手道,“那么,小的不打扰了,后会有期。”
杨怀三送刘管家到医馆门口,死皮赖脸地说道:“再给点,再给点。”
刘管家先是一怔,随即马上明白过来,又掏出一串钱,皮笑肉不笑地说:“拿去,够你喝一顿花酒了。”
刘管家走远了,杨怀三在背后啐道:“你这家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爷这把年纪了喝什么花酒?!兔崽子,真是的……”
扶风最大最豪华最热闹的酒楼,醉风楼,醉在扶风。远远望去,醉风楼飞檐翘角在朦胧的灯光中若隐若现,整座楼流光溢彩,是扶风最醒目的建筑。进得门来,只见雕龙画凤,檀木桌子,碗筷都是铝质的。出入这里的都是达官贵人,要么就是富甲一方的商贾大鳄。店小二手脚麻利,穿梭在客官之间,忙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
义妁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场合,她一进去就引起不少花花公子的瞩目,她躲开这些目光快步来到二楼的雅间,鲍大夫已在里面等候多时了。
“幸会,幸会。”鲍大夫立马迎了上来,看他的样子,义妁还真怀疑他是不是大夫。
“姑娘请坐,请上座。”刘管家赔笑道。
“让二位久等了。”义妁行礼道。
鲍大夫打趣道:“像义妁姑娘这样的贵客,鲍某再等上一个时辰也是应该的。”
义妁笑了笑。
“姑娘不仅花容月貌,还医术超群,是世上不可多得的奇女子啊。”鲍大夫恭维道。
但这些浮言虚语义妁并不受用,她开门见山问道:“请问鲍大夫,找小女来有何事?”
“不急,不急,先吃菜。”
“小女并非为享受美味而来。”
鲍大夫眼珠子一转,向刘管家使了个眼色,刘管家立马拿出一个包裹,放在义妁的面前。
“这是鲍大夫送给姑娘的见面礼,请姑娘笑纳。”
不用想,也知道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定是黄白之物,义妁料想,这次鲍大夫找她来,与元尚会没有任何关系了,于是把包裹推向一边,正色道:“请鲍大夫说出请小女来的用意。”
“姑娘既然如此豪爽,我鲍某也就直说了,姑娘也知道,近日所有的病患都被郑氏医馆吸引过去了,弄得我们保和堂门庭冷落,但真正在郑氏医馆就诊的人能有多少呢?你们医馆就那么大,这些可怜的病患等了又等,甚至不惜贻误病情也要等义妁姑娘为他们看诊,结果还没轮到他们,病情就恶化了。作为大夫,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真是难过。”
鲍大夫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
“鲍大夫的意思是说想让我们医馆分给你们一些病患?”
鲍大夫提出的问题义妁也想到了,这也是义妁担忧的地方,义妁也曾数次提醒病患,如果是一些小病完全可以去其他的医馆看诊,没有必要在郑氏医馆苦苦等候,可这些病患非常固执,只相信郑氏医馆,只相信义妁,无论大病小病,只要义妁看诊,他们睡觉也踏实。
“姑娘若有这番好心鲍某不胜感激。但鲍某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
“姑娘你不觉得待在郑氏医馆太委屈了吗?以姑娘的医术完全可以另起炉灶或者另谋高就,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如果姑娘肯来保和堂,鲍某绝不会亏待你,酬劳要多少给多少,甚至我们可以给姑娘重新开一家医馆,名字就叫义妁医馆。姑娘意下如何?”
黄鼠狼给鸡拜年,鲍大夫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他肥胖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似乎胜券在握,在他看来,如此高昂的代价,没有人会不动心的。
可惜他找错了人,如果是蔡之仁,话就好说,可义妁不是蔡之仁,义妁站起来说道:“抱歉,小女从来没想过要离开郑氏医馆,没有师父,没有郑氏医馆,就没有小女的今天。告辞!”
说完,还没等鲍大夫做出反应,她就咚咚地跑下楼来。
鲍大夫气得吹胡子瞪眼,“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天底下竟然有这种愚蠢的人!”
第二日,杨怀三凑过来小声问义妁:“那个叫什么鲍大夫的,找你过去有何事呀?”
义妁笑了笑,“哦,没什么。”
“没什么是什么?你倒说说看。”
义妁见杨怀三那么性急,只好如实相告。杨怀三听了张大了嘴巴,“可恶的家伙,竟然打起你的主意来了!那么,你答应没有?”
“小女没有答应。”
杨怀三笑了,“呵呵。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的。义妁怎么会是那种人呢?那样的事情只有蔡师兄干得……”
话还没说完就用双手捂住了嘴巴,因为恰在这时蔡之仁迎面走了过来,似乎听到了什么,瞪了一眼杨怀三,愠怒道:“还不去干活,在这胡说什么?!”
“没,没,我正在和义妁讨论一个病患的情况呢。”说着,慌慌张张地跑开了。
“对了,义妁,你帮我告诉师父一声,我要出去一趟。”
“好的。”
蔡之仁脚底生风走出了医馆,义妁看着他的背影,心想,他这是去哪呢?这么着急。
蔡之仁要去的正是昨日鲍大夫宴请义妁的那家酒楼,醉风楼。
义妁拒绝了鲍大夫,鲍大夫好不气恼,把一桌美味全部掀翻在地,狠狠地骂道:“可恶的丫头,竟敢如此待我!既不能为我所用,就要被我所毁。”
鲍大夫精心给了义妁一杯敬酒,义妁不喝,鲍大夫决定再给她一杯罚酒,这罚酒喝不喝就由不得她了。
鲍大夫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想破了脑子,终于想出一条毒计。他要搞垮义妁的名声,名声建起来不容易,搞垮它就很简单了。只要把义妁的名声搞垮了,还有谁去郑氏医馆看诊呢?到那时,源源不断的病患就会流向保和堂。
但搞垮义妁的名声靠他一个人不行,还得需要一个帮凶,他立刻想到了在郑氏医馆郁郁不得志的蔡之仁,再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估计蔡之仁比鲍大夫更希望搞垮义妁的名声。鲍大夫算是看准了蔡之仁的心思,一山不容二虎,照这样发展下去,郑无空早晚要把医馆传给义妁,而不是蔡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