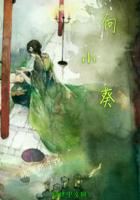叔叔的越南恋人
1962年,在辽东大山深处种地的叔叔光荣入伍。三年后,叔叔参加了抗美援越战争。
在一场遭遇战中,中方一名营长和北越游击队的一名负责人被俘。师部紧急命令,从全营选出10名战士组成小分队,执行营救任务。叔叔是其中之一。
小分队施展调虎离山之计,这边抽调5名战士配合游击队去打军车,吸引敌人,另一边实施救援。带路的一名姑娘主动要求加入小分队,因为她就是村里人,地形熟悉。女孩叫黎彩草,能说一口广西口音的汉语。
因解救行动成功,叔叔受到嘉奖,被批准回家探亲。
考虑到黎彩草家已被敌机炸毁,部队想让她到广西边境住下,等战争结束再送她回家。可是黎彩草不断打听叔叔的下落,引起营长的怀疑。团长明确指示:告诉她,她找的人已经退伍,立即把黎彩草交给越南方面;通知这小子归队听候审查。得知叔叔已经退伍,黎彩草只是一个人发呆,后来,在一个雨夜消失了。
叔叔归队后,受到严厉的审查:和黎彩草在4天里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是否泄露了军事机密?叔叔全用摇头作答。审查不了了之,不过,本来要被任命的班长职务泡汤了。
不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一次战斗结束后,部队返回途中,叔叔策动一位姓傅的战友与他结伴离队,在深夜摸进黎彩草所在的村庄。美军早已撤离,村子是一片废墟,他们攀上后面的高山。叔叔疯了似的朝山上喊:“阿草——阿草——”几十年后,傅叔叔告诉我:“真是奇迹啊,你叔叔真把阿草给喊出来了。原来,她和村子里幸存的人躲在山洞里。”在瓢泼大雨中,叔叔和阿草紧紧地抱在一起。阿草大声地说:“我晓得你会来的,你是中国男人。”
两人躲在一棵大树下,依偎着,谈了整整一夜,基本上是阿草说,叔叔听。言语一向很少的叔叔只重复着一句话:“打完仗,我就来娶你。”
天渐渐亮了,在傅叔叔的催促下,两人依依惜别。阿草送给叔叔一只红木雕的小猪。这只木雕陪伴了叔叔一生。
归途充满凶险,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他们和一群“越南人”不期而遇,当发出的暗号不被理会时,他们一下子警觉了,是敌人!战斗打响了,他们把集束手榴弹掷向敌人的卡车,两辆卡车发出天崩地裂的巨响,随即燃起冲天大火。两人随后从一道断崖溜下,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离队两天半后,两人重新归队,立即被秘密缴械关押。
通过对两人的审讯,加上游击队提供的情报,部队摸清了全部情况:叔叔离队的目的是去见黎彩草,战士傅某系受鼓动而随从;黎彩草,年方19岁,本人及家庭历史清白,父母、爷爷全部在敌机轰炸中丧生;归途中遭遇的是南越部队,他们从美军军火库中运回的两车地雷被全部炸毁,敌军死亡8人。
部队当即决定,上述情况,作为一级机密仅在小范围内通报,对外要统一口径:他们在执行秘密任务。叔叔和傅叔叔退役,叔叔暂不安排工作,听候进一步处理。
1966年年底,叔叔退伍回家,享受的待遇十分古怪:未分配单位,却每月能到邮局领15元钱。叔叔每天下地干活,有时十天半月也不说一句话。
次年秋天,叔叔说,他要外出一趟,这一去,近三个月才回来,人瘦瘦的,精神极差。四十年后,我通过叔叔夹在《******选集》中的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找到了黎彩草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的姑妈家。老人早已去世,她的儿子也已是白发苍苍:“哦,你问阿草的事啊?苦命啊,和一个当兵的好上了,听说解放军往回撤,就来找那当兵的,路上让地雷炸死了。那当兵的后来找到我家,晓得这事后,在院子里坐着,好几天不吃不喝。一天晚上走了,我妈发现一张有阿草的合影照片不见了,肯定是他拿去了,痴啊!”
叔叔半年后成亲,婶婶是邻县的一个漂亮姑娘。
叔叔终其一生,都没有忘记黎彩草。奇怪的是,婶婶从来没有因此而有过不快。堂妹告诉我:“她从来不让我动爸爸那个锁着红木小猪的木箱,还说,一个死去多年的女人他还这么记挂着,啥叫男人?这就是男人。”
堂妹大学毕业后,婶婶硬拉着一家人到广西旅游。到了广西,婶婶找到旅行社,为叔叔一个人办了越南七日游。婶婶让堂妹把叔叔推上车,七天后叔叔归来,婶婶什么也没问,一如往常。
作家和他的老妻
年过半百的作家与老妻两地分居,一个城里,一个乡下。
上世纪六十年代,还不是作家的作家高中毕业了。爹娘看着骨瘦如柴的小个子儿子着实犯了愁:这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娃,以后靠什么生活呢?经过亲朋好友多方物色,再加上不惜血本“重金”投入,小鸡子似的作家终于娶到了邻村膀大腰圆、力大如牛,长作家5岁的二嫚,也就是今日的乡下老妻。
在生产队,二嫚挣整劳力的工分,而作家连半劳力工分都挣不到;在家里,作家不问柴米油盐,一根筋看书写字,不着调,而二嫚补衣做饭带孩子,上上下下一把手。累极了的二嫚每每说,俺的亲娘来,这哪里是给俺找的男人,分明是俺永远养不大的幺儿子!
队里不指望,家里指望不上,闲人作家就有了充足的时间看闲书,什么《古文观止》、《唐诗宋词》……当他痴迷于四大名著时,满心窝子就有了好些话,当他阅读了大量作家的文集时,手就发痒,不写不行了。
儿子在院子里玩泥巴,作家在屋里飞笔游走,在二嫚眼里,这俩男人一样:图个乐子。
让二嫚对作家刮目相看是在一个午后,大队长送来一摞报纸,说让作家去公社上班。天,连只鸡都抓不住的男人还有用处?
后来二嫚才知道,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好些文章,公社要他去耍笔杆子。
在公社大院的作家,一如既往地勤于笔耕;生产队的二嫚,养老育幼依然牛一样出力。
文革结束后,面对革故鼎新的时局,作家激情澎湃,创作了大量富有时代活力的文学作品,且这些作品频频露面于省和国家级报刊。而后,作家被调到市作协,成了一名真正的作家。
做了作家妻子的二嫚还在家里侍弄那二亩责任田,虽然老人已离去,孩子们也像他爹一样有了出息进了城。
孩子们劝她到城里去,她说:俺是老黄牛的命,离开庄稼地,没地方拉犁拖车,心里空。
已名噪文坛的作家忽然封笔,潜心研读起“四书五经”“诸子文献”来。他说,我那点涂鸦与前人大作相比,太稚嫩,太拙不可观了。不写了,抓紧时间拜读圣贤文章吧!
当读到古代圣贤写的“贞洁烈女”时,作家忽然想起了家中老妻。
先前,作家一直认为,自己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二嫚的婚姻简直是一场悲剧;任劳任怨的二嫚似乎更像一位寄居家中多年的房客,再拙劣一点说更像一件“传宗接代”的工具……作家从来没有过什么婚外情,不是不想,而是没时间,毕竟对文学的痴迷远远大过任何女人。
今天,恭读圣贤的文章,作家觉得这里似乎有老妻的影子:相夫教子,赡养老人,抚育孩子……
时间已是初冬,作家拨通了乡下的电话。当老妻听说工作繁忙的作家不年不节竟然来看自己时,激动得一夜没合眼。
老妻一大早便撑船去了小河对岸,因为她不愿让作家多走十多里地经过大桥绕到村子里来。
初冬的风有些刺骨,不再健壮的老妻用力系了一下头上的围巾,眼睛极力注视着远方。来了,她矮瘦的作家男人终于来了。
没有拥抱,没有寒暄,甚至没有多余的招呼。解开船绳,上船,拨篙,小船轻轻离了岸。
澄碧的河水缓缓流着。这时,作家想到了柔情似水,想到了水的无声与飘逸,想到了厚德载物,想到了无私奉献,想到了老妻……他靠近船舷,想捧些河水亲吻。
重心旁移,小船陡然倾斜,作家犹如一片树叶轻飘飘落入水中。
见此景,老妻猛地伸出那双大手,虽慢了些,可还是抓住了作家的一个脚脖。稳住自己,平衡住船身,老妻用力把已吓得脸色灰黄的作家拽上船来。
把湿衣服脱下,老妻再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作家穿上。口里不停地宽慰道:莫怕,莫怕!这小河沟里,莫说你,就是千斤大牛俺也能把它捞上来……
躺在老妻的怀里,作家的老泪流了很久。
不久,一篇名为《老妻似水》的新作再次打动了读者,这是作家封笔五年后的第一篇作品。
遍地老虎
小贞蜷缩在床头,肩臂上裸露着一截红色胸罩带。
王金虎倚着门框,眉毛倒竖。
孙青云掀开被子,打量自己,一丝不挂,不觉毛骨悚然。不能断定做过什么,黄泥巴掉进裤裆,不是屎也是屎。
小贞是一个老乡介绍来的保姆,后来知道也是自己的同乡。
孙青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头脑一锅粥。小贞说哥哥王金虎来看她,孙青云吩咐多做两个菜……孙青云早就戒了酒,不知怎么竟然喝多了。
酒,一想到酒,他就不寒而栗。
孙青云曾是李副县长钦点的秘书,李副县长分管文教卫生,后是常务副县长,就要当县长了,孙青云也是某办主任人选,在这个时候事情拐了个弯。
一次他代李副县长宴客,在楚天楼。楚天楼的奥妙,不在吃喝,孙青云懵懵懂懂进了包厢,暧昧的光线,飘渺的音乐,婀娜的少女……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根本回忆不起来。妈的,茅台酒是假的,要不怎么醉到那个程度,他一直耿耿于怀。是否另有玄机他没有多想。
警员找到他的时候才知道,那晚上的女子是暗娼“红玫瑰”。她要是待在楚天楼屁事没有,偏这山望那山高,在“云水阁”犯事了。据说“红玫瑰”身上的小本本上记有孙青云的名字电话。也有说他陷进官场争斗,谁让他是李副县长的人呢……
孙青云没升上主任,连秘书也做不成了,他的老婆立马走人。
孙青云与老婆章淑媛是校友,章淑媛这名字令人遐想,温馨悠扬。论长相,令男生过目不忘不无道理。个头小,板刷寸头,腰身粗壮,荸荠般的身段,流线圆弧替代了女人曲线,一副柿饼子脸凹凸不平,敷上一层****盖不住点缀其间的小疙瘩,半截扫帚眉下一双眯缝眼,总也没有睡足的样子,肥厚的嘴唇无法掩住一颗擅自出队的门牙,这副长相谁见了会忘记呢,想不记住都难。她的长相有些草率粗糙,却有个不可小觑的爸。
生怕重新回到穷乡僻壤的孙青云,中文系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县中。303室的室友们刮目相看,诧异之余大兴问罪之师,说你个龟孙子,比潜伏的敌特厉害。祖坟上长了一棵肥嘟嘟的蒿草,不露声色牙缝也不曾松过。说怪不得你这一个学期就像大侠,神出鬼没行踪飘忽。有讨伐的有赌咒的,说你个龟孙子不够哥们,让你一辈子娶不上老婆,娶上老婆也生不下儿子,生下儿子也是别人的。
就在毕业前夕,他与章淑媛悄悄领了结婚证。
事情并不如想象中复杂。简单的铺垫之后,暑假的某一日下午,他从老家来到县城,把章淑媛约到小饭店,两个人开了一瓶“洋河”……他把她一直送到闺房。章局长咳嗽一声推开女儿的房门时,孙青云吓得站起来,手却被章淑媛粘着……他和她同在一个县,她爸爸是县教育局长。那个时候师范生统配,哪里考来要回到哪里。
一次李副县长视察县中,孙青云初露锋芒,作了一个简短而精练的发言,恰到好处,给李副县长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立即吩咐调到身边。
王金虎问,怎么打算?孙青云望一眼小贞,小贞低着头,披肩长发盖住大半个脸。王金虎催促说,问你呐,装什么装!孙青云对小贞说,你哥哥……王金虎粗暴地打断他,什么哥哥妹妹,她是我女人……你睡了我女人!不容他开口分辩,又说,这把年纪了,****吧你,把我女人肚子搞大了,你还是人吗?
孙青云弄不明白自己是否对小贞无礼,一直诚惶诚恐,听说小贞怀孕,而且是他的,他忽然在心里笑了一下,如释重负。没事了,踏实了,悬在心头多日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他慨叹,人哪,内心那只大老虎总是张着血盆大口。他把求援的目光再次投向小贞,小贞,你告诉我,告诉他,你说,说我没有对你怎么样……快亲口说出来!
小贞低头不语。
王金虎算是小贞的男人。两个人住相邻村,王金虎从小就不安分,长得五大三粗,力气出奇的大,外号“大老虎”,长大了人见人怕,一个泼皮混混,没人敢惹,粘上你够喝一壶的。
十多年光阴,山不转水转,一切命中注定。有一天,他在车站偶遇她,一眼认出来,立马灵魂出窍两眼绿光,像影子一样纠缠……小贞饮了一小杯啤酒,就交出了自己的初夜,只好谈婚论嫁。恰在此时,一帮狐朋狗友追着他的屁股讨赌债,他自恃孔武有力,天不怕地不怕,凶神恶煞一般……被他殴伤的人送到医院没有救过来。他被戴上手铐,小贞哭天抹地,他却硬橛橛地梗着脖子撂下一句话:敢让别的男人上,小心脑袋……
一次章淑媛说漏了嘴,那天她根本没醉。
离婚简单顺利。章淑媛幽怨地望孙青云一眼,说,结婚以来,你从没把我放在眼里,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露出原形了吧!一肚子野种满世界飞扬……不怨章淑媛,结婚七八年居然没弄出个一男半女。
孙青云的心不在焉激怒了大老虎,他气急败坏地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闷屁都不放。要么把女人让给你,我拿钱走人;要么赔损失费……谁不知道你的钱多呀,小时候就听说你当了大官。小贞说你书房连瞧一眼都不能。
孙青云笑了,说,不就是钱吗?过几天来取。
****事件后,孙青云被安排在文化馆。
不用几天,那点劣迹就传遍了全馆。吴馆长还不错,闲暇邀他下下棋聊聊天,偶尔在小餐馆聚一下,孙青云不喝酒。吴馆长是画家,画虎名家,专画大老虎。孙青云受吴馆长影响,开始学画,画虎。
过了二年,孙青云去了艺术研究院,挂个副院长,据说是李副县长暗中关照的,还亲自撮合他的第二次婚姻,女方是县歌舞团青年舞蹈演员丁丽丽。
孙青云且喜且悲,有点疯疯癫癫。他也曾隔三岔五在章淑媛身上耕耘播种,颗粒无收。丁丽丽的身体仿佛恩赐一般只给过他几回,却种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丁丽丽,不枉男人一场,他在内心慨叹。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他一度以为生命遇到第二次小阳春。感谢李副县长。
一个周末的黄昏,丁丽丽演出归来,迫不及待提出离婚。孙青云呆若木鸡。问,儿子呢?丽丽说,你不用管了。秋季开学儿子上一年级。丽丽说到省城演出,带儿子见识见识,这一见识不打紧,孙青云父子从此天各一方。
孙青云想不明白,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吗?丽丽说,没有,我经常不在家,儿子多亏了你,我对不起你。那干嘛要离婚?他问。丽丽轻描淡写地说,需要理由吗?一句话把孙青云噎得翻白眼,他没好气地说,不在乎我也要为儿子着想呀。她说,正是为了儿子才要离婚。顺便告诉你,我已经调到省城,这次是去报到的。都安顿好了,儿子我必须带走,学校也联系好了。
……
几年后孙青云去省城,想拜见一下据说已是副厅的李副县长,费了许多周折才摸到府上,他揿下门铃,傻眼了。你怎么在这儿?丁丽丽愣了一下说,我的家呀……
孙青云对大老虎说,不用吓唬我,大牢里没位置,你要小心自己……看在小贞照顾我生活的份上,放你一马,下次再不能乱来。要不,我随时可以报警。
孙青云不是吓唬大老虎。